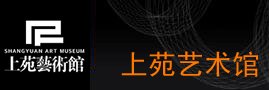行為藝術論
島 子
在當今,無論是藝術史的書寫,抑或藝術現狀的批評、討論,乃至身體社會學以及新興的文化研究范疇,都繞不開行為藝術所表征和被表征的客觀癥候。這不僅因為行為藝術的思想觀念刺激著當代藝術發生學的活力,產生了處于歷史密封倉情景的“粘魚效應”.同時對滿目問號的社會文化轉型,亦正在增補著人文意義的公分母內涵——在現代性烏托邦的終結點上,在以市場化為藝術品生產和知識生產軸心的法則之外,行為藝術家已經在扮演并將繼續扮演著疏離與介入的角色。相對與廟堂式美術館藝術和藝匠型的學院藝術,行為藝術作為一種建設性、生成性的新民間藝術,為社會文化結構提供了活性因子和精神樣式。正緣于此,在審美專制主義、歷史決定論、政治獨斷論相互摻雜的語境下,行為藝術就難免成為備受責難的領域和聚訟的焦點。本文試以文化研究的視閾和現象學的解釋方法,探討行為藝術復雜表征下所隱含的社會、文化及政治的真實境遇。
行為藝術的合法化問題
事實上,包括行為藝術在內的當代藝術.在本土面臨著合法化存在的雙重困境:一方面,在行為藝術與全權意識形態及其展覽機制之間,構成了壓制與疏離的現代性話語緊張:另一方面.關涉到行為藝術自身從策略到語言的自我完善問題。盡管我們并不能幻想或要求行為藝術能像京劇、芭蕾舞或唐詩、交響樂那樣,精湛、深邃.微妙而靈光地成為另一種經典藝術形態(那至少是下個世紀的光景了).而且任何所謂經典之原始的、結構性的整體都和創作個體的犧牲與眼淚、絞殺與饗宴、抗爭與內訌、信心與毀謗緊緊糾纏、連結在一起。
具有法學理論準備的批評家王南溟先生動議:合法化的前提至少應該在法律上保障“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本土當代藝術的不自由,不“合法化”,從根本上來說是這種藝術的自由還沒有得到憲法的有力保護……從中國憲法的“言論自由”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表達自由”發展,有助于“合法化”的法律制度建設,尤其是裝置、行為等前衛藝術樣式能否進入美術館及其公共空間,就是最起碼的自由權利。[1]批評家敢于向權力說法理,無疑表現出知識分子應有的道德勇氣。否則,藝術批評會成為在壞日子冬眠的殘次媒介。然而,在當代藝術的關聯閾,把法醫當成戀尸癖,把超前的思想和深刻的實驗視為精神病,或以道德、良知以及種種莫名其妙的“名義”侵害創作個體的權益:或與此相反,都已司空見慣或麻木不仁。然而,法律是意識形態的表征.任何道德或者社會律法,都傾向于以利斧切割人性.唯一缺欠的就是對個體的主體性的最終理解。與藝術相反.法律不是個性的認定者,盡管法律也假借藝術的方式把個人的形象編導成扮演某一角色的某類演員,而法院恰好會把個人安裝在法律符碼的布景和劇情之中。
話說回來,即使行為藝術真的已“合法化”,其概念性的本質還是否能稱之為行為藝術。在此.重溫烏托邦哲學家布洛赫(Emst Bloch)的論斷似有必要,他認為“藝術不單純是某個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更不是其統治俯首聽命的奴仆。如果將藝術當成時代的反映,對藝術作品進行所謂合理的經濟分析和加以社會學圖式的蒙蔽(即使以盧卡奇的文學理論形式),那么,就必然造成對偉大藝術作品的曲解和藝術意義的遮蔽。”[2]再則,合法化的前提還必須經由一個知識構型和價值論的認知整合過程。現代學術的科學性是建立在通過概念的分析來了解事物和世界的,每一事物的存在都有其自身的本質,本質的名稱即某一事物的名稱,而概念里的本質決不會既是此又是彼,也決不相反相生。”火決不能收容了冷還仍舊是火.而且同時又冷。”[3]行為藝術不僅具有自身概念的形式,也隨著自身概念排斥它的反面。惟有回到現象學本原,從學理上辨析其“不可言說”的疑義,方能澄清多重附會的迷津,抵制審美專制主義妖魔化和自我妖魔化傾向,改變“前衛企業”的零售小販身份,滌除媚俗傳媒施加的無聊噱頭影響。
國人向來有種根深蒂固的附會癖(“文字獄”在世界文學史和政治史上都是空前絕后的),它反映在行為藝術的認識論上,主要存在著兩種附會癥候。
首要的是極“左”主義政治美學,它慣常附麗于古典主義“真、善、美”之宏大敘事準則,進而執持為兼有法治、義理、道德、藝術相互混淆而曖昧的評判標準,而實質上中外邪教之教義莫不假借“真、善、美”行使對人類的精神控制。[4]人們不會忘記,假借“革命真理”,“文革“政治美學及其美術曾經何等殘酷地對人類普遍價值進行踐踏。單就美學道理而言.人類社會并不存在某種適用于一切藝術及藝術品的審美本質與共同性質,把“真、善、美”假定為評價一切藝術形式和觀念的“健康理性的客觀性”,不僅顯得虛假、空洞、貧乏,而且往往因為其錯誤的語言表達而受到審美專制主義的熱烈鼓勵和超級役使。無情壓制審美多元化,絕不承認美包含并存在于美的對立面,最終危及藝術表達的自由。例如,行為藝術中的裸體問題.時常被貶斥為”淫穢“,敢問何謂“淫穢”7或日:引發性交欲望者也。如此斷定,問題就簡單得荒謬了一一這里就孤立地只剩下兩種人裸露癖(行為藝術家)/窺淫癖(觀眾)。問題是,在這種弗洛伊德式俗念之外,還應當隱存著各種不同的盲域,由于每個人對于性感的對象,性趨向的環境因素反應并不一樣,其中包括年齡、經驗、原欲、性別、民族、種姓、階級、信仰、道德價值觀等等,對于某人是淫穢或色情,對另一些人卻有可能是美麗、愛欲、活力甚至自由,如同巴特所言“盲域的存在使得愛欲影象不同于淫穢色情影像。……相反,愛欲影像不以性器為焦點.甚至根本不用亮相,只是將觀眾引出框外。”[5]值得回味的倒是.對行為藝術身體媒介的“淫穢”指涉,反而裸露出審美專制主義全景敞視(Panoptic Gaze)的肉體政治欲求。
附會癖的另類表現則是泛行為主義.即使在相當專業的藝術媒體中.時而也會冒出一些“博學先生”,使出附會的解數,一直把行為藝術“索隱”、“考據”到儺戲、社火、酷孝、封禪、埋尸會、佛教儀式、帝王行樂,[6]乃至希特勒納粹軍事化的“cI形象”,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種附會除了顯耀作者聰明的饒舌功力和稗史知識外,在學理上沒有任何價值。制造偽知是一種不失風雅的智力游戲,它始于附會,終于媚俗。歷史上,“古已有之”論+“革命功利主義”以及莫名其妙主義的附會,也不乏風流顯要——康有為就曾指認歐洲油畫是馬可·波羅從中國元代攜入歐陸、又于萬歷年間由傳教±引入本土.并言之鑿鑿論證宋代就有的“中國油畫”,他在《萬木堂藏畫目》中收錄了這種數量可觀的“油畫”佳作——幾乎都是贗品。
行為藝術的學理邊界
從藝術史的史實考釋,行為藝術(Performance Art)是發韌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而多相衍化到當今的一種國際化的藝術形態和樣式.它與裝置藝術(1nstalIation Art)同步生成而早于錄影藝術(Video Art)。西方行為藝術的經典文本大多產生在七十年代,尤其是1 968年法國“五月風暴”后的歐美國家。八十年代.由于西方藝術界的新形象(New image)運動使然,遂趨于偏鋒地位,但它在九十年代的亞洲卻獲得了無可替代的先鋒精神,反過來又在國際藝術格局中激發出新的命題。
盡管某些中外行為藝術家們反對任何為之理論上的定義,以便于從策略上僭越藝術學的學科規誡.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但行動(Action),能夠成為藝術(Art).本身即已在藝術范疇之內(而非政治學或精神病理學)決定了它的樣式、語言、方法,只不過每一次對其邊界的逾越.都豐富了自身定義的內涵,擴大了原有的概念。這也是行為藝術能夠被匡正為藝術史和藝術批評對象.并得以在諸多國際藝術大展中成為獨立的展示類項的主要原因。
作為正在被歷史化的一種民間性新傳統的藝術形態和樣式,行為藝術的學理定義雖有中外各家學說上的分殊.但其基本概念大致可做下述梳理——行為藝術是傳統架上藝術形式(繪畫、雕塑)的觀念化移置或拓擴,尤其是抽象表現主義之“行為繪畫”(Action Painting)和“無形式藝術”(Art informal)的延伸和變異。它突破了架上藝術單純靠二維或三維視覺感知創造靜態藝術空間的限囿.[7]將空間的物像延異為時間的事像,將靜態的被動接受轉換為動態的交互關系.并借此達成易于和觀者交流、對話的場所和情境。
就行為藝術的形式變化而言,它衍生并凸現于現代藝術史背景.除了脫胎于“行動繪畫”、“無形式藝術”,它還秉承了現代主義藝術的諸多創造形式:達達的表演、美爾滋建筑(Merzbau)、無意識自動寫作、包豪斯劇場、超現實主義電影等。行為藝術在新傳統的藝術堂奧里尋求可能性,而傳統架上/手工藝術必須多死幾次,才能在藝術史中得以再生和轉生.這本身符合全部現代藝術史規律和史實。但也無可否認,以“新”為新的達爾文式語言進化論和線性歷史進步觀已經同時終結。
行為藝術的悖謬邏輯
行為藝術以參與性、日常性和事件性(Events)體現藝術社會的民主精神,這種性質和意向,在歐美發達國家始終是對博物館、美術館展覽/收藏機制的反動,對權力與資本合謀下的資本主義市場意識形態最直接的嘲弄和疏離。在“全球化”了的藝術市場神話中,隨便一幅梵高的油畫,都可以炒作到上百萬美元.而這位傳教士出身的荷蘭畫家生前窮困潦倒,最終投于精神崩潰。他終生淤積的激越的道德力量,充其量被兌換成風格化的利率,變為中產階級“消費苦難”的符號,成為商戰優勝者一一跨國資本的身份化標簽。
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從行為藝術的“民間立場”發現了別樣的悖謬,認為行為藝術家時常把觀眾和警察同時當作動態事件要素設計在內,是試圖為國家找出資本與勞動合法化的同一性,行為藝術及其相關新藝術(過程藝術、地景藝術、錄影藝術、貧困藝術等)所尊祟的藝術自由化、民主化、公眾化.結果變成了資本的官方改革策略。德國藝術史學家馬丁·達爾姆(Martln Damus)指出:”要求藝術作品對人類生活塑造有所貢獻,就如藝術與科學表面上的自由被用來作為形式民主的幌子一樣,其實都是用來維護統治的。兩者都為企業家所利用,他們容許藝術家在其領域內工作。”[8]由此可見,與中國自漢代以來逶迤貫穿至今的“儒法互補”實用理性主義(“成教化,助人倫”)不同,西方當代資本主義 Eve rything goes(怎么都行)的終端底牌,翻過來就是:以藝術的名義行使什么權力都不必干預,但必須保障我在你的“行為”中獲利。典型的事例,如意大利行為藝術家曼佐尼(Piero Manzonl)的《100%純藝術家糞便》(1961年),被當成頂級藝術品收藏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1968年,以巴黎“五月風暴”為核心而形成的全球化反體制運動,主要以前衛藝術的形式——海報、標語、涂鴉創造了自己的形象,那些為自由而設計的革命海報,變成收藏家們急切搜羅的收藏項目,展示在紐約博物館的墻上。越是前衛的海報就越是批量復制.廉價出售。它們不再是自由傳播的免費媒介,革命性的“行動”沖擊被消解殆盡。生前被批評家視之為“耶穌與薩滿的當代聯袂“的德國前衛藝術家博伊斯(Joseph Beuys)的全部行為藝術“道具“,被杜塞爾多夫的”博伊斯藝術紀念館”收藏。他倡言并踐行的“社會雕塑”觀念涵項,如綠色政治、直接民選、大學自治等至今仍是未遂的普遍社會理想,其遺存物卻成為以消費主義為價值依歸的文化代碼,資本對于藝術主體的客體化鑄壓機能,在上述個案中略見一斑。馬克思曾評論說,商品絕對沒有軀體.只存在于一種形式化的交換行為中。生產不僅把人當作商品.當作商品人、當作具有商品的規定的人生產出來:它依照這個規定把人當作既在精神上又在肉體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產出來。[9]在商品的時間里,疏離或反抗的“行為”,都可能被虛構成商品的專橫而不允分辨的“超驗價值”,而這種被特許的藝術等于商品大于交換價值的等式,又不斷填充了意識形態權威所必需的象征資源。
后革命氛圍中的表演:反諷與救贖
行為藝術有三重形式能指或三種呈現方式:行動(Actlon),身體(Body)、偶發(Happenlngs),三種方式有時單獨運作,但更常見的是在同一件作品中互為發生、演進的條件,相互串并,秘響旁通.尤其兼融了實驗戲劇、音樂、舞蹈、雜技、魔術、影象、裝置藝術.過程藝術、電腦媒介的適應性因素后,則進一步演繹出與社會。文化、政治、性別等相互交契和辯難的可寫性空間形式。因此,在當代藝評術語中,行為藝術的稱謂被統一又模糊地稱之為 Performance Art“——既強調其”表演“成份,但又與傳統的演藝明顯區分開來。
行動(Action)的特征是視藝術家為巫師,博伊斯的思想資源有相當的韃靼薩滿教成份,被闡釋者們有意忽略、諱避的或許還有彌賽亞精神,十字符號一直貫穿著他的全部作品交替地出現,喻示著喚起的能力和啟示的奧義。[10]不幸即愛的本源表征,寄寓著十字架上的真理,因而苦行應然就是“行動”的最高境界,它企及了神秘精神而植根于身體。苦行需要意志,意志屬于靈魂中的自然部分。善于運用意志無疑是拯救的必要條件。旅美臺灣藝術家謝德慶始于七十年代末,終于八十年代初期的三項行為藝術《服刑》(1 978年9月至1 979年9月)、《打卡》(1 980年4月至1 981年4月)、《仍在服刑》(1 981年9月至1 982年9月)三項行為每項持續一年,即體現著苦行的當代象征意義。借由自我囚禁、精神自虐和內在流放的肉體與心理雙重的“極限體驗”,來追問生存的合法化,倘使沒有崇高的認信,沒有“因信稱義”的蒙召,便不會承受類似十字架上磔刑的人間苦難。[11]
行動包容了與身體相關的全部因素:動作、姿態、表情、活動、呼吸、聲音、語調、皮膚、體液、體味等都是作品必然和有機構成部分。早在六十年代末期.就由一群維也納藝術家[11]開創出具有相關主題的行動,在儀式化的表演中使用人和動物的身體、血、液、結合于原始宗教的神秘精神,探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命題。
在后現代理論話語中,[12]身體既是激進政治的深化又是 種對它們的大規模替代超越異化勞動的身體和革命道德理想主義的身體,遁向靈魂與血肉之軀及其器官的主體鏡象化(拉康),進而以身體取代思想主體的認識論至上性(梅洛一龐蒂),建構性別身體的自我空間(米歇爾·福柯/女性主義/怪異理論).回歸以身體、自然和地方為真實性的生態中心論(查倫·斯普瑞特納克)。總之,身體以其所有促成了對于傳統哲學二元論的重大超越。在中國,小康社會理想迅速將身體的美學化帶進大眾消費文化,而身體的視覺消費又左右著身體美學化乃至“情色化”。從醫藥、保健、桑拿、按摩、餐飲、體操班、舞蹈班、美容、化;l女到影視、網絡、廣告、時尚、服飾、武藝、人體攝影、裸體畫、人體彩繪等等,無不體現著上述消費產生的“力必多經濟”景象。藝術與文化的舊有結構關系裂變.大眾身體消費文化已然將前衛藝術的意義液化、過濾、蒸餾為小康牌實用理性主義花露水。凡此種種,誰能說中國沒有后現代(性)。小資讀《鼠疫》(加繆)、精英看“規懲”(福柯《規訓與懲罰》),此乃SARS時期的經典閱讀經驗和解經學之現象。
在行為藝術的理念中,身體自身已不是審美意義的對象。與傳統的架上藝術及人體攝影所迷信的“人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