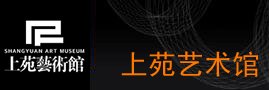|
程小蓓的小說<<你瘋了>> 五
[2006-10-1 13:47:06]
她
她不讓他人及大自然來左右她的死亡。一個人無法控制自己的生,那就一定要爭取控制自己
的死。她認為這是有主動權的人生。
當她爺爺讓她想明白了再來時,她的第一個反應是她不明白要她想明白什么,她卻像火箭一
樣蹦上了天。要不是她的父母過來拉住她的手臂,要不是格子飄過將她按住,不定還要在那
兒蹦多久。
格子像一枚針卡在揚家的咽喉部。時不時被仍活著的她奶奶用手彈撥一下。整個山林里八十
代以內的亡靈都會痛得尖叫起來。現在它們要聯合起來對付揚子與苛多。它們不能讓楊子與
苛多在活著的人面前再落下那怕一丁點兒的口實。
整個山林自起狂風——阻止!阻止!阻止!堅——決——阻——止——!!!節奏就跟文革時
期大街上的群眾觀點——鮮明、不容質疑、鏗鏘有力。腳上踏著鐵靴,踩過的地方一片泥濘。
那著黑風衣的挖坑人,又提了一桶水來,還是那么不緊不慢地給他的地撓水。刨平的地上已
綠草蔥蔥,細細的樹苗在風中搖頭擺尾。她盡力地去辨別哪一株是銀杏的樹苗,那是她的母
親;哪一株是香樟的樹苗,那是她姥姥;哪一株是松柏的樹苗,那是她爺爺;哪一株是杉木
的樹苗,那是她奶奶,哦,她奶奶還活著呢,在這兒是找不見她的;哪一棵是玉蘭的樹苗,
那便是靜靜。
靜靜是她童年唯一的朋友。看到她揚子很高興。她一想到馬上就可以與靜靜重逢,再也不用
陰陽隔絕,揚子伸手想將靜靜拉住,靜靜卻不見了。她能感到,靜靜被什么控制著,不能與
她接通。
她四處找尋,她看見祖先們——母親、父親、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還有親外婆王木姬等一
大群——聚在一起,熱烈地討論著什么。不時有人回過頭來瞅瞅她,并指著她說三道四的。
氣氛激烈、緊張。但揚子只看見他們似水滴一樣透露著,使背后的景物在形態上發生一些扭
曲。還有很多的亡靈她不認識,但她能聞到她家族的特殊氣味,是甜中帶一點澀澀的水果味。
有很多年輕人,也就是說是短命鬼呢。這讓她想到自己的家族是有些問題的家族。用現代基
因學者的說法就是:家族的遺傳基因里有特殊變異,致使身體在陽間的空氣中不能應付自如。
不是得病早死,就是精神崩潰,自己結果自己。她姥姥算是活得最長的祖先,可這亡靈里沒
有找見她。她要知道揚子將到來,一定會出來迎接的。她很愛揚子。估計她姥姥準是反陽了。
可她爺爺明明看到了她,也沒見有一點親熱勁,一副不歡迎她的樣子,就只一個勁地要她想
明白再來。要能想明白了就不會再來了,她想,然后垂頭喪氣地閉上眼睛。
這時,在她閉著的眼睛里靜靜又出現了,還牽來一個陌生人,她們倆也都有她家族的水果味。
這是怎么回事呢?這陌生人有點像靜靜她媽,對著她拼命搖頭,像是要阻擊她什么。可靜靜
和她媽也都是一種半流體狀的透明物,朝著她艱難地流過來,似要將她粘連在她的墓穴里。
揚子驚慌地張開眼睛。
揚子與苛多
“嗨,揚子!嗨!你怎么了?”
苛多在搖晃著她,她的眼睛釘在海子里一棵樹的倒影上,扯都扯不回來。苛多不知發生了什
么事,著急地對著她的耳朵大聲喊道:
“揚子,醒醒。你怎么了?”
喊畢,仍沒有反應。他將她從石頭上抱了起來,將她的臉貼在自己的臉上。他發現她的臉冰
涼,于是解開自己的外衣將揚子緊緊裹上。嘴里喃喃地說:
“哦,對不起,對不起。天這么冷讓你坐在石頭上說了這么久的話。”
天空上還有最后的一抹陽光,如舞臺上的追燈將他們倆籠照。揚子的眼睛從海子中的那棵樹
上移向這束陽光:
陽光在天窗上,國王一般傲視我們,
邁著不屑一顧的步伐走了。
我所有的傲慢和尊嚴頃刻間土崩瓦解。
我跪求陽光的憐憫,
請停下你的腳步,將我照射。
地面上陰冷,沒一絲暖意,
我守候著記憶中最后的那束陽光,
它的溫暖,它的嫵媚,以及
它寬容、平等地普照每一個生靈。
我像水杉吮吸它的養分,
靈魂脫離開肉體,飛升上去,
追尋它的足跡,久久不肯回來。
……
尖尖收撿起自己的畫具,遠遠看著他們,一種難以表述的心情使她斜歪了一下自己的腦袋,
解嘲般一笑,背上畫具獨自一人朝阿夷扎家走去。
那束陽光消失了,紫色的晚霞抹上天空。這時,揚子的眼睛終于回到了苛多的臉上,她象不
認識苛多似的看著他。苛多坐在石頭上,懷里仍然抱著她,見她的眼睛終于活過來看著他,
就伸手將她額頭上的頭發撫向耳后。輕聲對她說:
“揚子,你凍壞了,是嗎?”
揚子真的打了一個寒顫,將頭和肩膀統統縮進苛多的懷里。苛多的手臂收緊,像被子一樣將
揚子裹住。
不知過了多久,天空最后一點點紫色的晚霞也不見了。揚子將頭和手從苛多懷里伸出來,她
說:
“我剛剛在追趕一束陽光,它走了,不肯等我。哦,我好像還看見了我小時候的一個朋友,
名叫靜靜,她是我表叔的情人。我表叔迫于各種壓力沒有娶她,最后她死了。她是殉情?”
“我們在說外公外婆,你怎么會想到你的表叔和靜靜了呢?”
“是啊,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我的腦子總是亂七八糟的,不能集中在某一件具體事情上。時
不時地飛呀飛呀飛……,跳呀跳呀跳……。”沉思了片刻,她又說:“我總是不能忘了靜靜,
一想起她,我的心就沉甸甸的。”
說著她用手摸著苛多的臉,將自己的臉貼上去,繼而抱住他的脖子。在他耳邊說:“我要有你
這么個親哥哥該多好啊。”
苛多在揚子臉上吻了吻,說:“揚子,以后我不但是你哥哥,我還要是你父親,是你的愛人。
沒有什么能阻止我。”
揚子閉上眼睛,淚水流了出來。嘴里不斷地說:
“是真的嗎?是真的嗎?……。”
“是的。是的。沒有什么能阻止我,沒有什么……”
“是真的嗎?是真的嗎?死亡也阻擋不了我們嗎?”
“是的。是的。死亡也阻擋不了我們。”
“沒有上帝來為我們祝福,那么讓所有的亡靈來為我們祝福,好嗎?”
“好的,好的。”
苛多像珍寶一樣將揚子抱緊在懷里。他感到他找到了這個世界上唯一還存活著的親人,他不
能再像消失了母親、妹妹、外公、外婆那樣讓揚子再從他的生命中消失。
揚子在苛多的臉上找尋到他的嘴唇,他們長久地親吻著。苛多不斷能舔到從揚子眼睛里流出
來的咸咸的、澀澀的淚水。
夜深了,尖尖一個人在阿夷扎家的床上睡了。早晨醒來,看見揚子在她身邊還睡得很香。她
心情矛盾地看了一會兒自己的姐姐,突然她決定她要離開九寨溝,離開這個國家,到遙遠的
地方去。她收拾好自己的行囊,在床頭留下一張紙條:
老姐:
我走了。拜拜。我不能當你們的燈泡呀。是吧?
祝福你們!真的。無論我走到那兒,我都會祝福你們。
苛多:
我知道你的老底。哈哈,你要是對我老姐也像對待你那一千個女朋友那樣,你就得留點神了。
我會令我那一千個男朋友來收拾你。不過我知道你不像我們那混賬父親,你骨子里卻是一個
珍視真愛的家伙。所以,我把你讓給老姐了。
拜拜
尖尖上
揚子還在疲憊的睡眠中,苛多已經來到她的床前,守著她的夢。等她醒過來時,張開眼睛看
到苛多正溫柔地看著她。她伸手抱住苛多的脖子,苛多在她臉上吻了一下說:“尖尖走了。她
給我們留了一張紙條。”
說著將那紙條遞給揚子。揚子驚詫地將手從苛多的脖子上放下,在床上坐起來。接過條,看
了后良久,她說:
“尖尖不會是在生我們的氣吧?”
苛多笑著聳了一下肩說:“怎么會呢?她干嗎要生我們的氣?”
揚子沉思良久,而后說:“是不是她也愛著你呢?”
“嗨,她足有一千個男朋友,哪兒還輪得上我呀。”
“你不也有一千個女朋友嗎?”
“嘿,揚子。”苛多嚴肅起來,不再開玩笑。他認真地說:“她是一個有才華的女孩子,對色
彩和線條都有非常好的感覺,并有自己獨特的表現手法。如果能讓藝術成為她生命的一部份,
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玩世不恭,她會畫出了不起的畫來。對我來說,僅此而已。”
揚子變得憂郁起來,她說:“除了我表叔,這個世界上活著的就只有她是我親人了。我才剛剛
找到她,不能又失去她。我們約好,要去尋找格子的。這樣我們就有仨姐妹了。”
“我的傻揚子,你不會失去她的,你太多慮。她不過提前回學校了,我和你們一起去尋找格
子,好嗎?”
說著,苛多將揚子攬進懷里,手在揚子背上拍拍。揚子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安全和幸福,她
放松自己的肌肉,軟癱在苛多的手臂里,任他在自己臉上細細地吻過。
“我愛你,苛多。”
“我也愛你。”
“你真的和我們一起去找格子嗎?”
“是的。”
“那咱們走吧。尖尖她媽或是我奶奶會知道一些格子的消息。”
“好的。”
他們收拾好自己的畫囊,告別阿夷扎,在九寨溝的仙境中穿行著返回成都。
汽車在險峻的山嶺中盤旋著,久久望不見終點。泥沙石路坑坑洼洼,常常被山上滑坡下來的
砂土堵塞住,不能順利地行進。一邊是陡峭的懸崖,一邊是滾滾的白水江冰河,而汽車司機
一個人連續三天不合眼地開車,九十度的拐彎都不帶剎閘。所有的乘客們都看到了死亡之神
——閻王爺高舉著屠刀,向他們砍來,他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苛多則一臉的幸福,用一
支手挽著揚子的腰,對眼前的險情卻生出一種莫名其妙的得意。揚子心神恍惚,頭靠在苛多
的肩膀上,對這些心驚膽顫的場面似早以經歷,一副熟視無睹的冷淡。
“揚子,我們要是就這么翻下山去死了,你愿意與我合葬在一起嗎?”苛多說。
“是啊,死!”看著那些高大的山,看著車子在這原始森林里風一樣地穿梭,山中的樹木筆直、
粗壯,揚子的心身又似在遠處,她不知道自己是活在現在、過去還是將來。她說:
“死是一種美?記憶中我爺爺總是在尋找這樣的山和這樣的大樹。我想他是在尋一種死的藝
術。”
“你有這么多的親人可以回憶,而我從沒有什么人可以讓我叨念。”苛多突然苦笑一下說:“我
說不定是從天空中掉下來的外星人。”
“這或許也是一種美。你的根漂浮在天上,很遠很遠;而我的根扎在地上,很深很深。我在
看達利和梵高的畫時有這樣不同的感受。”
“不。揚子,我不認為有什么美。一個不知道自己來源的人會有很多的困惑,包括對時間的
困惑,對生命來去的不可知是線性的還是與現世空間重疊或在無限空間里零落著?這些都讓
我不安、空虛,在我的畫里變成了漂浮不定的形和色調晦暗的光。它們帶給你的不應是美的
信息。我想找到生命的軌跡,以為它是象鐵路般,有兩條鐵軌,生命像車輪一樣在上面滾來
滾去。小時候我愛到鐵路上去玩,總想知道這鐵軌從何來到何處去,我想沿著它走下去,去
尋到它的頭和它的尾。有一天,我真走了下去。在路上我遇到一個名叫三路的浪人,他說他
一輩子都在路上,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他最初的記憶是一個早晨,一覺醒來,轟轟隆
隆的火車從身邊開過,他的腳被震得在地上跳了起來,當一切都安靜下來時,他發現他在一
個三叉路口上,周圍沒有一個人,只有一排排高大的楊柳樹在路的旁邊。他不知道接下去該
干什么,但他的腳開始邁起步來,在兩寸寬的鐵軌上走如平地,并對自己能如此感到十分得
意。從此他再也不能離開鐵軌,就是火車來了不得不下去躲避一會兒,他都覺得難受。他說
是三叉路生了他,這鐵軌就是他祖宗的血脈。我問他這鐵路通到什么地方?有沒有看見過它
的頭和尾?他說,有很多的頭和尾,它通向很多地方,所以他比一般人要了不得的多。他到
達過無數的頭,然后又反過來走,但他有原則:決不讓自己的腳印有重疊的可能。他走的不
是同一根鐵軌,他只走右邊的那一根,遇到叉道口他就在叉道中間拉一堆屎或撒一泡尿,接
著就右拐,到頭了返回來還是走右邊的那根,遇到叉道口他再拉一堆屎或撒一泡尿,接著仍
右拐,這樣他就永遠也不會走在同一根鐵軌上,也不會落下任何一個叉道口。我問他為什么
一定要在三叉路口大小便?他說:‘誰叫它生了我,我恨它。’我又膽心地問,要是所有的鐵
軌都走完了怎么辦?他說,如果真要是走完了所有的鐵軌,那就是到了他該死的時候。”
“你跟著他走了多久?”
“聽他說完這些后,我就沿著鐵路回來了。因為他說,快走完了,沒多少了。我說:‘那就是
說你快要死了?’他說,是的,前些天走過了生他的那個三叉路口,路邊大楊柳樹上多年前
拴著他的小紅褂子還在,只是紅色變成了黑色。他說,無論如何他都是認得的。到這條路的
頂頭再返回來到達那個路口,他就要死去。”
“他有多大年齡?”
“我想,他應該只有二十多歲吧?不過他看上去足有五十歲。”苛多眼睛看著車窗外,沉默良
久后又說:“我總在等待他的死訊,何時?用什么方法?如果我聽不到他的死訊,那么就是路
還沒走完。揚子,你說,他要是到達了生他的那個路口,而他還活得好好的,那他如何死呢?
我說的是用什么方法結束他的一生?”
“我不知道,不是每個人都是這么有計劃地安排自己的死,我尊敬這樣的人。我爺爺就是這
樣的人。”
揚子看著車窗外的崇山峻嶺,再次感嘆:山是那么高,樹木生長得如此繁茂,任何一棵樹都
比她的腰粗。特別是那些松樹,從沒有土的巖石縫隙里生長出來,舒展著手臂,昂著堅強不
屈的頭,召喚著她。
她說:“只要一看到大山上的大樹我就會想到我爺爺,他一輩子都在尋找它們,他對松柏是那
么癡迷。”
“給我說說你爺爺吧。”
揚家老爺
我爺爺,算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他是我們老家精州鄉里第一大家族的長子。
清朝末年的中原大地,一片驚慌的貧瘠。我爺爺他爹,早早地就得肝病,將家里所有積蓄都
花在了郎中那兒,也沒將他爹的病給治好。最后肚子脹鼓鼓的(現代醫學名稱為肝硬化,肝腹
水)死了。
丟下他娘和十二個崽女。我爺爺排行老二,那年他十六歲。老大是個女兒,自然,他就是當
家的了。
他娘揚張氏就是在我童年時老叫著的“姥姥”,是鄉里出了名的織布高手,為此他爹才肯娶了
這嫁妝不太多的他娘。祖房的后半個箱房,后來就開做了專織布的紡織間。家里常年請有工
人(我想是不是紡織廠的一個雛形)。
我爺爺他娘織的布:平細、均勻,很受布商歡迎。那天,我爺爺像以往那樣,將布拿到常接
他家貨的店里,老板不象往常那樣殷勤。我爺爺是直性子,就問,何故?答說,現如今都興
起洋布來了,他娘這貨不再好賣了。我爺爺拿起店里柜臺上的洋布來摸看了一番。什么也沒
說,拿了她娘織的布。就回了。
年輕氣盛的他,到家后,讓他娘歇了,只讓工人去織布。
將家里的幾十畝農田賣掉十幾畝,剩下的田地安排給弟妹們去種。自己則帶上賣地的光洋,
作本錢,領著他最喜愛的小弟,到城里去做起洋布買賣來。
沒想,鬧起了兵荒。買賣做不成了,只得收拾了回家。
回到家里發現他娘和弟妹們個個臉色發黃,肚脹腹瀉。所有的表象都跟他死去的爹一個樣。
又是肝病。而且,揚家村子里,滿村的人都得這病。
村里人都喝一個池塘里的水,洗菜、洗衣、洗馬桶、飲用等。
村子里還就只有揚老爺家請得起郎中。請一次郎中要好幾百吊錢,用八抬的轎子從縣里去抬
來,那轎子全用了松柏的木頭做成,沉甸甸的,一走三步搖,那個眼饞呵,把個鄉里人看得
不吃藥也好了一半。
待郎中給揚家的人把過脈、看過舌相、開罷藥方后,揚老爺千恩萬謝地將郎中抬回去。郎中
臨上轎前說,不能再吃那口池塘里的水了。
我爺爺想,這郎中說塘里的水不能喝,難道說他這么神,知道這池塘里怨鬼多。他上輩子的
姑姑,因要將她嫁給一個她從沒見過面的、有錢的大老爺做太太。而她自己已相中了家里的
一個長工。在出嫁的前一天,跳到這池塘里自殺了。那時候他十四歲,跟著他爹去把泡了幾
天,變得白腫的姑姑撈起來葬了。當時還曾很惡心地想,那幾天泡著他姑姑的時候,還擔了
幾擔水在家的水缸里,吃喝呢。葬完姑姑回來,他將缸里的水全倒了,去很遠的山上擔泉水
吃了些日子。可后來就又不知不覺地開始吃用起這池塘里的水來了。那以后,村里就老有人
臉色黃黃地死去,包括他爹。
這是姑姑的怨恨找來了。
想到這兒,他朝著郎中所去的方向,跪下,三叩首,感謝郎中向他道出了謎底。他要解救余
下的鄉親。從此以后在他的心里,郎中,如神一般。
我爺爺根據郎中開的藥方到很遠的鎮上去撿藥。這藥得半年一年地長期喝。家里如此多的病
人,花盡了他做買賣時的所有積蓄,又賣掉了十畝地。最后,只救得了他娘和一個生命力很
強的妹子。其它的,都相繼去了。
一個大家,十好幾口人,只剩下他娘、一個妹子、一個小弟和他。
過后,他將村子里沒生病的人招集起來,硬是挖掉了半座山,將那口池塘給填平了。
又根據他在城里做買賣時看到的那些水井,請風水先生在村里點了一個地方,挖了一口水井。
好在是江南的水鄉,任何一地開挖不到三米,便有清亮的水冒出來。這以后,村里人就結束
了用池塘水的歷史,開始了用井水的歷史。
后來就家家門前都有口水井了。但由我爺爺請風水的那第一口井,成了鄉人敬完神后,必取
一杯的仙水。能祛病免災。井邊一棵挺拔的松樹下,立著一塊青石板,上刻我爺爺的名字,
后面寫著——吃水不忘挖井人。
這事很傷他的心。自十六歲他爹死后,他滿以為他能擔起這個大家族的梁柱,給弟妹們做個
樣,不能讓這揚家的家業和人丁在他的手里給敗了。
其實,揚家村子和鄉里的人,就看他能用八抬的轎子,將郎中給請了來,還救了他娘和一個
妹子。其它得病的鄉人幾乎都死了。沒得病的人自他開挖了井水后,便沒再有人得病了。在
心里老早就敬佩起這個后生來。
可他還是難受,一輩子都在唸叨這些死去的姐弟。感到自己當時沒有錢再一次地去八抬大轎,
將郎中請來,是個罪過。不然的話,他們就不會死去。
為此他自責了一輩子。
為此他后來把蓄錢看得很重,無論如何,他都要蓄點錢在手里,從不亂花錢。他總說,錢要
用在甘貴的地方。
這事耽誤了他娶親。直到他二十一歲,由他自己相中了一個大腳的姑娘。那大腳的姑娘也相
中了他。
他可沒忘了自殺在池塘里的姑姑。
鄉里人都看不起大腳女人,何況還是自己訂的親。他可不管這么多。在城里做買賣那陣,他
就看城里女人時興不裹腳了。那時,就下決心要娶一個這樣新潮的女人來做堂客。他娘也不
干涉他。家里的一切都由他說了算。
這樣,堂客娶進門了,三年后才給他生了一個大胖兒子。這兒子就是我父親。這個寶貝喲,
含在嘴里怕化了,拿在手里怕掉了。揚家總算是又添人進口了。
滿一周歲時,請了鄉里所有的頭面人物來,辦了七天的酒席,請了三個戲班子來唱戲。可第
一天的酒桌上少擺了兩雙筷子。對此他悶悶不樂。
為了再多蓄點光洋,他又開始帶著他的小弟到城里去做買賣了。他老說他的財運不好。買賣
做得正紅火,又鬧起了跑日本鬼子。天天城里有一個怪叫的號聲,一叫他們就要跑到山洞里
去躲起來。躲完了出來,東西都被人偷跑了。
這些發國難財的。
我爺爺罵一陣,也怪起自己來,這些發國難財的怎么就沒被日本鬼子給炸死?單單就我這條
命會被要了去?于是任你再怎么怪叫,他不再躲了。果然,只看到炸彈在遠遠的地方炸開,
并沒傷著他們。
但是,這樣兵荒馬亂的,有什么買賣可做呢。他只有又帶著小弟回到鄉下。本想這鄉下日本
鬼子不會去炸的。誰想,村頭那廟子都給炸沒了。
可不能拿他那寶貝兒子去冒險。
想著,就決定將全家南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這日本鬼子來勢可兇呢。連人影子都沒見著,就能把個武漢城弄得人心惶惶。指不定見著人
了會是什么樣?!
他是那種想到什么事要做,就能立即行動起來的人。于是,他給那生命力很強的妹子找了一
個上門妹夫,守住這份家業。再買掉十幾畝地,作盤纏和不備用。
帶著老娘、小弟、堂客和兒子上路,南下江西。
在途徑武漢候船時,又遇那怪叫的號聲。
人們一陣混亂,沒見過世面的他娘和兒子嚇得不知所措。而他非常鎮定。安排小弟帶著他堂
客堅守他們的行旅和難得候到的船坐位子。自己則帶著老娘和兒子躲避到就近的山洞里去了。
其實,他并不想去躲,就像上次在城里做買賣那陣,不躲不也沒傷著嗎?可他是個孝子,看
見老娘嚇得不得了,兒子又哇哇地哭,就躲了。
在他的心里,家人是分有等級的。老娘和兒子是排在第一的,小弟排第二,堂客和妹子則是
排在第三。不過他都很愛她們,對她們都有一股男子漢的責任心。
有好幾聲悶悶的轟轟聲,響得很近,似來自江邊。在他心里引起了不安。
等到又一次響起怪叫聲,空襲警報解除了。他知道日本飛機走了。便急急地朝江邊走去。
還沒到江邊,就聽見那里一陣陣的哭叫聲傳來。
他將兒子交給他娘抱著,讓他娘用那三寸金蓮的小腳,慢著點走到江邊去等他。而他滿心的
不安,跑到江邊。那里已是橫尸遍野、船翻人沒……。
我爺爺瘋了似的,在江邊的碎片中翻找。最后又無望地順江而下去找。滾滾的長江上滿是肢
體的碎片和飄浮的船板。
沿江一線的船,都被炸沉了。原來,這次日本鬼子是專門來炸船和橋的。則讓揚家給趕上了。
程老爺不禁想起,兒子周歲筵席第一天的桌上少了的那兩雙筷子。
這真是命啊!
我爺爺一聲長嘆。雙膝跪在長江邊上。平生第一次痛哭了起來。
從此以后,我爺爺在年三十、年初一、生日等重大的家族筵席上,筷子是必由他親點過后,
再多放幾雙在邊上。而且決不準有單根。
《中國旅游報》報導:
來自四川省廣元市的消息:昨天一輛滿載游客的汽車,在從尚未開發的風景旅游區——
九寨溝開出,沿著白水江邊崎嶇的山路,順利進入嘉陵江段后,由于司機連續三天三夜開車,
疲勞駕駛,在廣元市境內的嘉陵江邊失事。
目擊者是一名藏族卡車司機,據稱汽車在一個雨后山體滑坡,路面已極度傾斜的路段上仍急
速行駛。加之兇猛的江水將路基沖松,車行至緊靠江邊的路面時,路面突然坍塌,先是左側
車廂向江中滑去,司機無力挽回慘局。最終,在一片悲慘的尖叫聲中整車翻入滾滾的江水之
中。汽車在江中漂浮了約有十多米,這其間有數名乘客從窗口跳出,但由于江水洶涌澎湃,
人和車不久就全部淹沒在濤濤的江水之中。
車上乘客約六十多名,全部失蹤。現在各有關領導及解放軍部隊正采取積極措施全力搶救,
組織沿江數百公里的各地廣大黨員干部逐段搜尋。涌現出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另請各位遇難者親屬,前來認領尸體并報告失蹤人員身高、年齡、性別等,以便我們將有關
善后工作能順利地完成。
……
她
清澈的嘉陵江水歡呼雀躍般流到了重慶,在這里極不情愿地匯入混濁的揚子江。它們順江而
下,路過了無數祖先的故土。
當流經一座古寨時,濁水在這里不停打著旋窩,留連一隱藏于郁郁蔥蔥林木之中,建造于秀
深峽谷之處,周圍的峰巒疊嶂下有古亭、廊橋、驛道的鎮子。這鎮子依山旁水而建,祠堂、
官邸、書齋、宅第、戲臺、寶塔等星羅棋布,五里十里,粉墻黛瓦。這里山、水、竹、石、
樹、木、橋、亭、澗、灘、巖洞、舟渡、古宅等組合的景觀,有如世外桃源。走入鎮內,四
處是彩燈:板花燈、馬燈、獅子燈、塔燈、香火燈、梅花燈、花船燈、鷸蚌燈、寶蓮燈、草
藤燈等。(詳情請翻閱黃利主編的《古鎮游》)
這鎮子便是她在人間最后停留過的地方,從這鎮子北去就是她選定的墓地,她的祖先們聚集
的山林。
她像一葉帆,在碎裂的江水上飄蕩。沿岸的亡靈多如牛毛,比她來的世界還要擁擠。好
在它們可以重疊、可以穿透、可以變形,并且可以像一縷煙一般裊裊升上天空。
“你戀愛了,揚子。”
“是的,是的,我戀愛了。這是我第一次戀愛,我的血管里有他的血,他是我的哥哥,他還
要是我的父親、我的愛人。他說他死后要和我葬在一起。”
“這是不可以的。你必須阻止你自己。很多事情你都還沒有弄明白,請不要輕率地作決定。”
“為什么?為什么?你要我阻止什么?我要弄明白什么呢?我爺爺這么說,現在你們又這么
說。”
“你先得將你家族的事情都講給苛多聽完了之后,你就有機會弄明白我們要你弄明白的事
情。”
揚子不得不返回到她人間的狀態里去,將她所知道的家族中的每一位成員的故事講給苛多聽。
為什么要講,有什么好講的?人間的故事多如牛毛,有多少亡靈就有多少故事。每個亡靈的
故事都不一樣,也都大同小異。講完了她家族的故事也就是講完了所有人間的故事。
一滴露水掉下來,落在揚子的鼻子上。露水說:“不對。你家族的故事只對苛多有意義。人間
的故事由不同的人講出來就有不同的聽者。你的故事不能代表所有人間的故事。”
一陣風吹過來,嗚嗚地咆哮:“所有人類的故事都是重復的,不外就是愛情與性、金錢與死
亡……,還能有什么?”
揚子伸出手要擦掉鼻子上的水,要堵住耳朵里嗚嗚咆哮的風聲,不讓這些問題去擾亂她對苛
多的愛以及她所要完成的對苛多必講的故事。卻發現她什么也阻止不了,她的手是無形的氣
體。最后她只有絕望地叫喊:
“求求你從我的鼻上走開,水滴。求求你不要在我耳朵里咆哮,風。你們誰也不能阻擋我的
愛,我對苛多的愛是人間最美的愛。”
“好了好了,讓她講下去吧。”
揚家老爺
揚家老爺嘆息著揚家的祖業、揚家的好風光都敗在了他這一代手里了。對不起列祖列宗啊!
他常常為此無奈地感嘆 。
他帶著老娘、兒子繼續沿揚子江南下到九江,江兩岸滿目的青翠,在他只是蒼涼。前面的路
如何走?在他心里也是無著無落。只憑著一些感覺沿水路南下,只要不離開能生長稻谷的土
地、只要離日本鬼子的炸彈遠點便感覺好一些。他畢竟還年輕,雖然經歷了如此多的災難,
仍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勁頭。這樣他從鄱陽湖、贛江到達吉安城。在那里的碼頭上遇到幾個說
家鄉話的漢子。
在路上折騰了一、兩個月,離自己的家鄉越來越遠。一聽到這種鄉音,一種無由的信任和親
切感油然而生。他立刻上前去搭訕,將自己介紹一番。那幾個漢子剛開始非常謹慎,過后看
到他滿臉的誠意和他身后一老一少的三代人,一派孤苦零丁的景象,就熱情地與他攀談起來。
原來這是幾個安源煤礦的工人,當年曾參加過劉少奇發動的煤礦工人大罷工。聽到“共產黨”、
“革命”這樣一些新名詞在他們的嘴里說出來,揚家老爺就把這幾個漢子視為高人,心里無
比的敬仰。
他們鼓動他跟隨他們一起到安源去,一邊謀生一邊參加革命。
揚家老爺自然非常高興。這漫無目的的逃難,已使老娘和兒子疲憊不堪,身上的積蓄也不太
多了。從家鄉出來的五個人走到這里只有三個人了,程大家族在他這一代里變得人丁稀少,
過著顛佩流離的生活。在他心里也逐漸地對自己不太有自信心了,心中除了悲傷還有些對時
局的無奈。現在遇到這樣的高人自然是自己的福份。于是千恩萬謝過,拖兒帶母的來到了安
源煤礦。
工人們幫他找了兩間房安頓下老老少少一家三口后,又推薦他到礦井當上了挖煤的礦工。每
天隨著大批頭戴一盞小油燈的工人們,由一個“吱吱”作響大鐵架子吊入一百多米深的礦井
里去,屈膝彎腰地挖煤、運送。
在井下干了不到一年,由于他能讀能寫,善言會算,不久就被礦上的資方負責人提升到井上
地面的抽風機房里去管理那些“嗡嗡”巨響的機器了。這些機器上有很多儀表,說是英國還
是什么其它外國人的機器,寶貝的不得了。它關系著礦井下成千上萬人的呼吸問題,是人命
關天的大責任崗位!
揚家老爺在他爹沒過世前讀了六年私塾,在這礦上就是很有學問的人了。加之他聰明、靈動、
好學勤快,是個有膽有識的人。很快獲得了當時地下黨領導人張大鑫的關注。
一段時間的考察,張大鑫認為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可以發展成為黨的中堅干部。于是,
決定作為一個特殊的人才用最保險的方法:發展為與他單線聯絡的地下黨員。
于是,揚家老爺莊嚴地成了一名共產黨員。但只有張大鑫和他兩個人知道。
這之后,由于他處處都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嚴肅表情來為人處事,漸漸地礦上的工人們都管他
叫起老程來。他覺得共產黨員是有身份的人,有身份的人都有一個嚴肅的臉具。
從張大鑫給他的“老三篇”中,揚家老爺開始認識到有土地是一件罪惡的事,他非常慶幸自
己將土地給敗落了。立刻寫信給遙遠的老家妹子,讓她將剩下的十幾畝地都分給村里的鄉親
們,還開了一個名單,張三、李四、王二麻子各戶一畝。
當信到鄉里時,田地都給上門的妹夫賣來抽鴉片去了。沒得可分了。
揚家老爺收到妹子的回信后,點著頭在屋子里轉了好幾圈,嘴里喃喃地說:“也好,也好。省
了事,省了事。”
全然沒顧到老娘在抽泣,擔心這女兒沒了地可如何活。
張大鑫策劃了一次大的罷工,要求他將那臺供應井下空氣的抽壓風機給停了。這樣,那些個
別害怕資方懲罰的工人就沒法去上班了,能達到百分之百的全員大罷工。
揚家老爺在抽風機房工作的這幾年里,將這臺被廣泛認為了不得的機器摸得透熟。哪些部件
是要害,哪些部件壞了不好修,他都了如指掌。
接到張大鑫這個命令,他利用夜班上工時將一個不好修的部位給弄壞了。工程師來看時也無
法懷疑是他有意而為之的。能把高高在上的工程師給懵了,這使他在心里無比的得意,比這
大罷工的勝利還讓他得意。
最后,大罷工變成了流血的斗爭。
張大鑫在這場流血的斗爭中犧牲了。他失去了與黨唯一的聯系。
不久,安源煤礦被共產黨、解放軍收復了。新來了黨的領導人,所有的共產黨員都不需要躲
藏了,都從地下到了地上。
揚家老爺也找到新的領導,將自己的情況如此這般地介紹了。新領導忙得不可開交,沒時間
處理他的問題,就說:“啊,等等吧。這事以后再談。”
是啊,是啊,剛剛收復了舊社會,清理事物多得不得了。我就別去擾亂了。等等吧,等等吧。
揚家老爺自言自語地就回了家。
不久土地改革了,劃分成份了。揚家老爺順利地、光榮地被劃成了貧下中農。
他越來越覺得他這個共產黨員的事一定要去說清楚,解放前的共產黨員與解放后的共產黨員
是大不同的。這有關資格的大問題。
他又去找剛換來的新領導,將自己的情況如此這般地說了。新領導要做的事情更多了,沒時
間處理他的事,就說:“你這問題怎么不在上一屆領導那里解決呢?現在我們沒有這個時間和
精力來調查你的問題。以后再說吧。”
再說吧,再說吧。揚家老爺對新共產黨有些失望了。
但是,新上任的礦長對他的機械修理技術很是贊賞,提升他為礦井空氣安全系統的負責人。
還在他的肩膀上拍拍,說:“老揚啊,我把礦上幾萬名兄弟的生命都交到你手上了。”
說完后又若有所思地說:“既然你對黨有那么深的感情,現在申請入黨也不遲嘛。”
揚家老爺頓時感到自己是不是老資格的地下共產黨員這事的重要性,也比不上礦長的這番囑
托。
揚家老爺在心里重重地掂著自己的份量。
五十年代,他第二次又申請加入了共產黨。
再后來,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時候,有人終于清查到他是混進工人隊伍中的地、富、反、
壞、右份子;混進黨組織的前國民黨特務。家有百畝良田,佃農百人,是罪大惡極的剝削階
級;解放前,是資本家的孝子徒孫。曾幫助國民黨、資本家殺害罷工工人,關閉往井下運送
空氣的抽壓風機,致使死亡工人多少多少人。
揚家老爺看到那虛擬的自己,罪孽是如此地深重。身上張著一百個嘴也說不明白了,越說罪
孽越重。
突然間,他哈哈大笑,喘不過氣來地大笑。我從未見他如此瘋狂地笑過,那笑令人害怕。然
后他不停地甩腦袋,裂開著做笑狀的嘴里發出一連串的詞:“人啊!人啊!人啊!何似苦,何
似苦,何似苦……,人哪……!”
最后的那個“哪……”字,是用了京劇里老生的腔調,“哪”了很長時間,很多彎,很多圈子
的。隨后,他學那些年里天天唱的京劇《沙家浜》里面郭指導員樣子,右手舉過頭頂,左手
叉腰,雙腳并攏,脖子堅硬,眉毛上揚,兩眼圓睜,氣宇軒昂,唱道:
“要學那泰山頂上一棵松……不屈不撓不罷休……。”
從第二天開始,他拿了一條繩索,爬到他居住地附近的山上,四處尋找一棵能吊死他的大松
樹。
滿山的灌木叢,所有超過胳膊粗的樹,都被砍了。煉鋼鐵了、燒制木炭了、當柴火了……。
坡上滿是樹樁子,樁子上又發出新芽的是去年以前砍的,今年砍的則是新的刀痕。有些樹看
得出是被力氣大的人砍了的,樁子上只有干干凈凈一個斜面的刀痕,或顯兩刀的V字形痕跡;
有些則是被力氣小些的婦女或孩子砍了的,樁面上是亂七八糟的木頭楂子。他對這些刀痕做
了很長時間的研究后,說:
“這世界上,連找個能體面地死去的地方都沒有了嗎?瞧瞧,這些樹也如此,剛活了個頭,
還沒看清這世界是什么樣的,就被燒成了炭灰。其實,它們比我好,看清了再死更是沒勁。
只是它們不能選擇時間和方式,比較遺憾。不管怎么樣,到這世上來走了一遭,總得畫個句
號,一個很圓的句號。不能由著那些沒有力氣的小孩子或女人亂砍一氣,把個圓圓的樹砍得
只留下些亂七八糟的木頭茬子。”
他晃晃悠悠地往回走。嘴里不停地叨嘮著,要找個高尚而安靜的地方死,不能死得沒有身份。
那就一定得是大山林里的一棵大松樹上。最好是像毛澤東背后黃山頂上的那棵迎賓松。
一路上他見人就問,哪匹山上有一棵能掛住他的大松樹?
在以后他被煤炭部調到離我父親工作不太遠的一座煤城里去工作,這并沒讓他改變主意,他
仍然是四處去尋找大松樹。還天天唱著京劇《沙家浜》里郭指導員的那段唱腔:
“要學那泰山頂上一棵松……不屈不撓不罷休……。”
好多年里,只要一有機會他就朝大山里去。但他始終沒找到一棵能掛住他的大松樹。煤城里
的人在飯后都嘲笑著談論他要找的一棵大山里的大松樹。他用十分鄙視的目光看著那些嘲笑
他的人說:
“他們是一群多么可憐的人啊!并不知道他們每過一天就離死亡近了一丈,死亡無可阻擋地
在前方設下了陷阱,等著你掉下去。與其這樣被動,還不如自個兒主動作決定,這是人唯一
能自己決定了的事情。”
等到松樹終于長大到能掛住他時,他卻已無力再去爬大山了。
最后不得不屈辱著,在自己家的破房梁上上吊。那房梁可不賴,足有一個成年人的腰身那么
粗,是松柏木的。從上面掉下來的木頭屑里我還能聞到松香油的香味。那年我二十歲,他都
差不多要老死了,可他說:
“我決定了的事情就是決定了的。不能眼睜睜看著自己躺在床上,等著皮膚皺巴巴、肌
肉全部萎縮、將最后一口濁氣吐完。那是最最窩囊的。爬我也要爬起來,自己選個良辰吉日
去死。”
“要學那泰山頂上一棵松……不屈不撓不罷休……。”他吊在那上面仍用最后那口氣將這個唱
段唱了一遍。
查看8877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