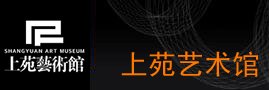|
程小蓓的小說<<你瘋了>> 二
[2006-10-1 13:52:41]
二、我
苛多,我真的在心里將上苑村那道院門給封了起來——我乘木頭外出不在家時就這么干。
沒有人能進來也沒有人能出去。像監(jiān)獄里判了死緩的人,時間對他已經(jīng)沒有了意義。只有昨
天和明天,只有開飯的時間,只有飯碗底下的菜葉是五片還是六片。我不要有人再來提審我。
不要在筆錄上簽字,也不要用手去沾紅印泥什么的……。那些人的嘴臉讓我討厭。特別是那
個自作聰明的胖子,每次他到監(jiān)獄來,我都想照著這張肥嘟嘟的臉狠狠地一拳,打得他四腳
朝天——如果不是有鐵柵欄隔著。他們總問我,什么時候用什么方法在什么地方搞到的毒藥?
怎樣放入酒杯?仇恨從何而來?我告訴他們只有玫瑰花,紅色的玫瑰花,一大朵一大朵地開
放著。他們說不對,那不是玫瑰是牡丹。哦——,對的,是牡丹花,大朵大朵的紅牡丹花開
放在你母親的衣裙上。我把它們采摘下來,帶到了監(jiān)獄。
常常與胖子一起來的年青人小劉——一個假模假樣的家伙——每次來提審我時,都告訴
我,他是如何如何喜歡文學藝術。每次說到牡丹和玫瑰,他總要加上中華民族傳統(tǒng)的牡丹或
是象征西洋人愛情的玫瑰。只要沒有其他人在,他就大段大段地背誦他寫的散文給我聽。寫
得真他媽臭——像臭豆腐,那樣的臭直撲你的鼻子——在他的這些文字里,沒一個詞不是別
人用爛了的。而且他所感嘆的東西都是你在哪兒聽人們說了上百遍的感受。然后他再在那兒
又拿來大大地抒一番情——最后這情搞得來就像是春天里的一只貓,在夜里“喵嗷……喵
嗷……”地亂叫。要不是在監(jiān)獄里呆得膩味了,我準得在他剛背誦不到兩分鐘時就打斷他。
說,行了,行了,什么狗屁東西!簡直是污染我的耳朵——還有鼻子——幸虧在牢里餓得來
對臭豆腐這樣的味道也覺著是香了。再說對于一個長年累月被關在密不透風的籠子里的人來
說,這等于是調節(jié)調節(jié)胃口。所以,我不但不打斷他,反而鼓勵他多背誦一些。這樣我可以
在號子外面多呆些時間。暫時不用煞費苦心地去對付皇后芭蘿要調查的那些個沒人敢承認的
屁;也暫時能呼吸一點點新鮮空氣、在更多的光線里讓眼睛不要忘了物體有更多的細節(jié)。真
的,在黑暗的牢里呆久了,很多東西都省略了它的細部,只呈現(xiàn)出它概略的線條和中庸的色
塊。剛從監(jiān)獄里出來那段時間,我的畫都是這樣的一種情況。后來木頭說,你要就這樣畫下
去,那你就是一個廢物了。真的,有時候你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腦子里裝的東西
就像漿糊似的——任你怎么晃蕩,它們就是粘粘稠稠的不清晰起來。我真他媽的倒霉,什么
倒霉事都會趟上我。
現(xiàn)在——是的,現(xiàn)在——上苑有一所屋子封在了圍墻里。并且切斷了電話線;拉了交流
電總閘。電信局反應出61700001的電話號碼是空號。大門外電線桿子的電表紋絲不動——死
了一般——我要的就是這個效果。
晚上要點燈時,我將所有的窗戶用被子嚴嚴實實地蒙住。在蠟燭光下畫一幅巨大的油畫。那
效果你能想象出來嗎?苛多。沒人能想象出來,連我自己都沒想到。有一次,我在香蕉水的
濃味下暈過去了,差點中毒而亡。我不知道自己在地上躺了多少天,所有的計時器——電子
的、機械的、石英的——都死了。調色板上的顏料結成了硬疙瘩——花崗石一般。畫布上是
一具木乃依的臉,蜘蛛在那張臉上結了十幾層網(wǎng)。我從地上爬起來,骨骼“咯咯咯……”地
響,像年久不用,生銹的自行車,所有的關節(jié)都得拆洗上油。身上的衣服一扯就爛——朽了。
撕開那衣服,底下的皮肉干裂,用手指一戳,皮痂如白灰糟了的舊土墻,嘩嘩啦啦地往下掉。
要想救自己,首先得去喝水——打開水龍頭,流出來的是黃色的濁水。墻角長出了毛。樓板
晃晃悠悠,隨時會坍塌。天花板上的瓦礫掉落下來,砸碎了不少家具。打開屋門,院子里成
了原始森林,藤蔓將門圍繞起來。透過藤蔓的縫隙看天空,好像是在水底下,而且是幾公里
深的水底。混混濁濁,天空沉重得要將你壓閉氣。整個房屋在水底下像一株腐朽的海草——
一點點波浪的搖擺就能使它四分五裂、碎尸萬斷……。這是我的家?我曾有在多年前就在一
首詩中寫過的家?
我的家被風吹得嘩嘩作響,
沙塵暴中的一片廢紙,
在空中久飄不落。
廢紙上寫著門牌號碼,
還有不斷變動區(qū)號的電話信息,
像液晶顯示屏上不斷閃爍的網(wǎng)絡數(shù)據(jù)。
揚子江、九寨溝、成都還是上苑,
都沒有確鑿的證據(jù)證明,
這個家已經(jīng)注冊在案。
不,這一切根本沒有存在過?!上苑村原本就是沒有的?!不可能!
我合上電閘。給手機充電。拔鄰居們的電話。電話里回答:“你已經(jīng)欠費停機,你已經(jīng)欠費停
機……。”
哦!不可思異。我莫非睡到了另一個世紀?這些人在這個年代里已不存在?我突然想起孫文
波這家伙就住在隔壁的院子里,從我家涼臺能看到他的院子。只要他院子里還有人,就能叫
到人來救我。
我像一條無骨的軟體蟲子一樣蠕動著,來到了涼臺。陽光像亂針一樣刺入我的眼睛。空氣一
點點的流動也形成了暴亂,使我真得像一片廢紙,飛揚起來。我落花流水般進入了孫文波家
的院子,惹得他家的狗狂叫起來。一個人的聲音:
“波特,不準叫。深更半夜叫啥子?要讓全村人都罵我唆?”
怎么是深更半夜?那天上不是太陽嗎,哦,是一輪明月。為什么月光像陽光一樣強烈?那狗
——波特,哦,波特。他管狗叫波特。笑死我了——仍然狂叫。這時一個人來到了院子里,
用四川話嘟囔著:
“波特,你今天咋子?有啥子在我們院子頭唆?”
那人打開院子里的燈,我不能睜開眼睛,那些光線能將我的眼睛穿插成冰糖葫蘆,并讓狗一
口吃進肚子里。
“唉呀呀——,唉呀呀——,你乍個在這兒喲?這么多年你到那兒去咯?木頭到處找你。為
了找你他都辭了學校的工作,賤賣了他所有的畫。結果你在這兒唆。”
孫文波像拈一片樹葉一樣,將我從地上拈起來,又把我像一片樹葉擱上了他的破汽車,送到
了醫(yī)院的病床上。醫(yī)生在我身上掛了無數(shù)個輸液瓶子,一滴滴一滴滴的水進入我的身體。于
是,我像氣球被吹漲了一般,從一片平面的樹葉又恢復到了立體的人形。
苛多與揚子
等揚子醒過來,已是第三天的早上。她躺在南平縣醫(yī)院的病床上。她想剛剛的那些事物是不
是自己曾遇見過的?它們好像是很遙遠的將來的事情,又好像是過去一個死去了的人的事
情……。
她漸漸清醒過來,看見苛多蠟黃的臉。她詫異地發(fā)現(xiàn)這張由紅潤健康變得憔悴的臉,說:“苛
多,你怎么了?”
苛多張大著嘴,由憂變喜地說:“啊,你醒了,你醒了,你終于醒了。”轉身對另一張床上和
衣趴著的尖尖說:“尖尖,她醒了,她沒事了。”
尖尖急急地走過來,將她的手握住說:“老姐呀,老姐,你急死我們了。你都睡了一天兩夜,
昨晚上我們才將你送到這里。醫(yī)生說你是失血性休克,檢查完就下了病危通知,說要立即輸
血,醫(yī)院里四處找管血庫的人,結果才知道昨天是周末的晚上,管血庫的人回鄉(xiāng)下家里去了。”
“好了,好了,沒事了。”苛多打斷尖尖的話,對揚子說:“你現(xiàn)在感覺怎么樣?”
揚子晃晃腦袋,有點暈;抬抬手臂,一根輸液管牽著有些酸;抬抬腳,一陣脹痛使她不免倒
抽了一口冷氣。嘴里卻說:“沒什么,還不到死的時候。”
說完對他們一笑。尖尖責備地看了她一眼說:“昨晚上我還真以為你要死了呢。急得只知道哭。
還是苛多行。”
說著朝苛多意為深長地揚起半邊眉頭,用一種曖昧的口氣說:“我認識苛多老師又更多了一
些。”
尖尖將老師兩字故意說的很重。她平時稱呼人總是沒大沒小。對苛多很少叫老師。苛多急得
臉都紅了,說:“行了,行了,我們還是想想辦法看怎么將住院費、搶救費湊齊,不然后面的
治療就麻煩了。”
揚子的腳腫脹得很厲害,阿夷扎家里的衛(wèi)生條件太差,加上高原水的沸點低,消毒不完全,
又一天一晚的折騰,傷口有些感染。回成都市里治療是不現(xiàn)實的,那些崎嶇不平、險象環(huán)生
的路,至少要讓人走三天。留在這所醫(yī)院繼續(xù)治療是首選方案。尖尖搶先說她回成都去籌錢,
由苛多照看揚子。苛多在尖尖的肩上拍拍,然后感激地抱了抱她,說:“路上小心。”
隨后從口袋里拿出一串鑰匙遞給尖尖,又說:“我學校宿舍的書桌里有些錢,你拿這鑰匙去開。
籌齊了錢先電匯過來,不要帶太多的錢在身上,不安全。”
“知道了,你什么時候變得這么婆婆媽媽的?哥們?我姐姐就交給你了。”尖尖說著回頭看了
一眼揚子,說:“老姐,你同意我們的安排嗎?”
揚子抬起那只沒輸液針的手,揚了揚,說:“真不好意思,破壞了大家的計劃,還那么麻煩。
往后還你們吧,也就一頓火鍋。”
“嗨!老姐,說什么呀?十餐海鮮還差不多。”
“你這是乘人之危,敲詐勒索!”
“別太小器了,最起碼也得是一餐海鮮再加一頓火鍋。”
尖尖說著,不再開玩笑了。要走就得趕緊,每天只有兩趟班車,趕不上就又得等一天。
尖尖走了,留下他們倆在醫(yī)院里。揚子感覺較好的時候,兩人沒有其它的事來打擾,就有說
不完的話。
苛多打開他的話匣子,他告訴揚子,他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母親拋下他和當兵的父親,被一
個男人帶走了。走的時候還帶走一個妹妹,聽說這個妹妹不是他父親的骨肉。不知道她們?nèi)?BR>了哪兒,他一直都在等待母親和妹妹的歸來,但從那以后再也沒有得到過她們的消息。為此
他痛恨那個帶走他母親的男人。
自他母親離去后,他開始在學校里寄宿。有位醫(yī)生是他母親的朋友,常去照料他們父子倆,
后來這位醫(yī)生嫁給了他父親。但她仍代替不了母親的角色。苛多認為,他們的結合是個悲劇。
他們一結婚父親就被責罰轉業(yè),下放農(nóng)村。不到一年便雙雙在文革中被人整死。從此他成了
孤兒。
苛多說到他母親時心情復雜,在灰白色的背景上,有圓的泡沫狀的飄浮物、有銳角的三邊形
沉淀物,青紫的、土紅的以及深棕色布滿了所有的感覺器官。
這些情緒在揚子那里都有感應。當她處于休克狀態(tài)時,正是這樣的感覺讓她飛往那片祖先的
山林。
她說:“為什么留在我們記憶中的母親,不像其他人回憶母親時那樣,有那么多的鵝黃、桔紅、
嫩綠,在晴朗的天空下布滿鳥語花香?為什么?”
揚子開始細細地向苛多說著她記憶中的母親。
查看10601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