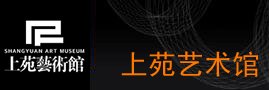|
���u���](m��i)���Ҹ���ֻ�����ɺ�ƽ�o
[2006-11-26 15:13:46]
���u���](m��i)���Ҹ���ֻ�����ɺ�ƽ�o
�ƕԶ�
�ڱ��w�롰���VԊ(sh��)����һ��Ԋ(sh��)���У����u��һ�_(k��i)ʼ�������ҫ�۵�һ��(g��)�������SҲ���ע���ɞ��ܳ�Ҋ(ji��n)�ֺ������һ��(g��)��������������Ʒ����������С�f(shu��)������^�������ᵽ��������1974�ꡢ�l(f��)����1978�����ƪС�f(shu��)������(d��ng)���������ҿ���(l��i)���o(w��)Փ�ڷ����ώ��ж���ģ�µĺ��E���@��С�f(shu��)�ڮ�(d��ng)��С�f(shu��)ʷ�϶���(y��ng)ռ�в��ɻ�ȱ��һϯ����һ�ӣ�Ԋ(sh��)����ڴ����r��Ҳֻ���ζ�ס���ġ��ش𡷡������桷����;���ȷ��ϡ����VԊ(sh��)�����x����Ʒ���ţ���������ҕҰ�U(ku��)չ�����t������������(x��)�T���Ȟ锵(sh��)����Đ�(��i)��Ԋ(sh��)������(du��)�T�硶���ӡ�����һ��(g��)����Ԋ(sh��)�˵�Ф���@ʾ�˄eһ�N�L(f��ng)�eһ�N�����Ե���Ʒ���s������ҕ����Ҋ(ji��n)���������f(shu��)�Ժ����|늡��������g���ǘӼȸ�����|��������������������L(f��ng)����Ҳ���龫��(x��)�����߂�(g��)��ɫ�ʵij��F(xi��n)��(sh��)���x��Ʒ�ˡ����o(w��)�Ɇ�(w��n)���@�N����������̖(h��o)������K���R(sh��)�ΑB(t��i)���ij�Ҋ(ji��n)��ijЩһ��Ҫ�����u������pass���u���ĺ���Ԋ(sh��)���ṩ�˷��㣬��Y(ji��)����ʹ�����u���@��(g��)�����ڱ����ٶȵؽ�(j��ng)�仯��ͬ�r(sh��)��Ҳ���������˞��O(sh��)Ӌ(j��)�Į�(d��ng)��Ԋ(sh��)��l(f��)չ��ܵ�ijһ�c(di��n)�ϣ�����Ԋ(sh��)�費�೬Խ������һ��(g��)�C��������(zh��n)�_���f(shu��)��һ����Ʒ�����S���@ЩԊ(sh��)��ͬ־����(l��i)�����߱���(l��i)����һ���¡�
��(d��ng)Ȼ���@���f(shu��)��ֻ��һ�N��Ҋ(ji��n)���������֮�����^С���^��o(w��)����һ�N����(l��i)����һ��ȣ���(gu��)��h�W(xu��)�����ȣ������c�ˌ�(du��)�Q�ģ��Ʌ�Ҋ(ji��n)�����W(xu��)����˹�ٷ�. �W�ģ�Stephen Owen�������ġ����^����Ԋ(sh��)�衷�������g������Ҋ(ji��n)�d���Ϻ������l(xi��ng)�ˡ�1992�괺��̖(h��o)��������ͬһ�����������(li��n)��(sh��)�����ġ��Ԙǡ�һ��(sh��)����Ԋ(sh��)�˚W�(y��ng)���Ӟ鱱�uԊ(sh��)����������ϵ��L(f��ng)��������(xi��)�����ġ����ѕr(sh��)�Ĺª�(d��)�����������u(p��ng)Փ����վ��̓��(g��u)�@߅���r(sh��)�����顶���uԊ(sh��)�����N�x��������(li��n)��(sh��)�꣬2001�������¡����ڸ��麦Ҳ���ҵij�Ҋ(ji��n)���@�ﲻ�f(shu��)Ҳ�T����Ҫָ�����ǣ��N�N��Ҋ(ji��n)�M�ܸ�������(j��)������һ�Ŷ�Փ��������Ԋ(sh��)��B(t��i)�ȅs�ֱ��F(xi��n)���@�˵�һ�£�������Ԋ(sh��)������һ�N��(qu��n)�����@Ҳ�͛Q���˳�Ҋ(ji��n)�����ߵĹ�ͬ���ݣ�������Щ����(zh��n)��(zh��ng)�Ŀ��˂������@һ�����S���ԵķQ�^���Ա��u�ġ�������һԊ(sh��)���c�����P(gu��n)����һ��(g��)�����և�Ĉ�(ch��ng)����
�����������Ļ���/ ��(zh��n)��(zh��ng)�Ŀ��˂�/ ������ȡů
�Ƿ�Ҳ���Ԍ���ҕ�顰ȫ�������¶���\��һ�NԊ(sh��)�衰�澳�������M����F(xi��n)����������ֳ����ζ��Ԋ(sh��)�衰���^�������߸��ص�Щ��һ���L(f��ng)�������@����և���L(f��ng)�����϶����鱱�u�����٣��sͨ�^(gu��)���@ʾ�ø����|Ŀ���������o(j��)��ʮ���ĩ�ԁ�(l��i)�����ڟo(w��)���x�������µ���Ʒ������Ԋ(sh��)�˵ı��u��(du��)��(gu��)��(n��i)�^�����(sh��)�x�߁�(l��i)�f(shu��)Խ��(l��i)Խ����һ��(g��)Ԣ�ԣ�һ��(g��)�������L(zh��ng)��������x�e�ĵ�ַ��ȡ����֮�������鹫������ı��u���˂�?c��)��?l��i)Խ��(x��)�T��Մ?w��)�һ��(g��)�����ǘ�Մ?w��)����ć?gu��)�H����Մ?w��)�����˷�������Ҫժȡ�Z��(ji��ng)��ڻ��c֮������^(gu��)����Ϣ���Լ��N�N�c�����P(gu��n)�Ă���ݛՓ���ܜy(c��)������������������Ԋ(sh��)�������u�����֡���һλՓ�߲��o(w��)�n�]�،�(xi��)�������ڳɞ�һ��(g��)������ͬ�r(sh��)Ҳ����׃��һ��(g��)�ն�����ָ���������n�]���c���f(shu��)�DZ��u�����֣������f(shu��)����Щ��Ū���@��(g��)���ֵ���ͣ����ڲ���(l��i)Ūȥ�б����Áy�߰��㡢���ײ�����Ԋ(sh��)��Ȥζ��Ԋ(sh��)��ӛ�������S��������ͣ�����һ�wʧ�����X����߀��ʲô���@���m���������^���ն�����ָ������ָ�أ��ʹ˶��ԣ�����l(f��)����һ��Ȥ�²���(y��ng)�H�H��������һ��(g��)�o(w��)�����ŵ�ЦԒ��Ҳ���Ա�ҕ��ij�NСС�İY����(ji��)���g���؇�(gu��)ʡ�H�ı��u��(y��ng)����֮��ȥij�ء���(d��ng)?sh��)�һλ�?j��)�Q����ʮ���Ҳ��(xi��)�^(gu��)Ԋ(sh��)���ġ�Ԋ(sh��)��(��i)�ߡ� (t��ng)�f(shu��)����d�^�������u����֪�������������_(k��i)ʼ��������ر��b�����J(r��n)��ı��u�����������Ї�(gu��)���ҵ�耳ׁG�ˡ�����
���@�ӵı����£��R���˱��u������Ҫ��Ʒ�ġ����uԊ(sh��)�輯��ȥ�����Ϻ����湫˾���棬����һ��ֵ�Ñc�R���¡�Ԋ(sh��)��һӡ��ӡ�����l(f��)�Д�(sh��)�ѽӽ����f(w��n)����ֵ�Ñc�R����(j��)����֪��һ��Ԋ(sh��)����������˸ߵ�ӡ�Д�(sh��)����ʮ���(l��i)���f(shu��)�ǽ^�o(w��)�H�У�Ҳ�ǘO�麱Ҋ(ji��n)�ġ��@�Ƿ�������u��Ԋ(sh��)��һ���������x�ߣ���(du��)���Ҍ��ɳָ�֔(j��n)���Ŀ�������������ô�f(shu��)���@����һ�΄���������һ��(g��)�˺�����Ԋ(sh��)�Ą�����Ҳ��������Ԋ(sh��)���x�߂��Ą��������ǡ�ȱϯ�ę�(qu��n)�����Ą�����Ҳ�ǡ��ڈ�(ch��ng)�ę�(qu��n)�����Ą��������Ǖr(sh��)�g�Ą�����Ҳ�nj�(du��)�r(sh��)�g�Ą���������ǰ������@Щ������һ�����h(yu��n)��(hu��)�ݳ��vʷ������ġ����ꡱ��������(f��)���Լ��@ʾ������/�Z(y��)��֮����𡱵�����/Ԋ(sh��)�豾���Ą�����
���u�������ӿ����Լ���Ʒ�ġ�߀�l(xi��ng)������һ��(g��)��(w��n)�}���@Ȼ���@����Ҫ�IJ��ǟ��飬�����صĶ�����������(xi��)�ھ�ʮ������ڵġ�������һԊ(sh��)�ڴ˸�����ij�N�A(y��)��(y��ng)ʽ�ģ�����ֿ��]�˸��N�����ı��_(d��)��Ԋ(sh��)�Ļ��{(di��o)�����ҽ�Մ�Եģ�������һ��(ji��)�sʹ���˔�ᔽ��F�ėl����Փ���ʽ��
����ı���/ ����܉��ط����l(xi��ng)
�����ؿ���(hu��)�X(ju��)�ü������°���ͻأ��ֻ���I(l��ng)���˵ڶ���(ji��)���������o�ͷ��S���n���ͻ��_(d��)������ֵ������У��Լ��S�����P(gu��n)һ��(g��)��ͥ���(hu��)�İ����{(di��o)٩���Ƈ@Ϣ�ĸ�������������Ʒ�����еď�(f��)�s��ζ��ȥ���°������ܡ�Ԋ(sh��)̽������ί�У�ͨ�^(gu��)E-mail��(du��)���u�M(j��n)���LՄ�r(sh��)���h���@��Ԋ(sh��)���ڿ϶��������������ط����͡����l(xi��ng)�������ж��غ��x��ǰ���£��ҵĆ�(w��n)�}�ǣ����硰�ط��������e(cu��)λ�����(hu��)ʧ������Ļش����Ҹе�����������Ԋ(sh��)�䌍(sh��)��δÓ�x�^(gu��)ĸ�Z(y��)�Z(y��)����
�����@�ǂ�(g��)�Փ�����^���ı�������ָ���nj�(du��)�Ѹ�׃�ı����ď�(f��)ԭ���@�Dz�����
�ģ�����ط����l(xi��ng)Ҳ�Dz����ܵġ��@��Ԋ(sh��)���ǻ����@�N�Փ��������ؼң����ؼ�֮·
�Ǜ](m��i)�еġ��@�����f(shu��)������ʧ����������������ևǰ�������c��ʧ��
�Ҳ�֪����(du��)��(y��ng)��ȥ�x����(xi��)�������ġ��h(yu��n)����һԊ(sh��)�Ƿ���m�����@��Ԋ(sh��)�У��l(xi��ng)����L(f��ng)�����f(shu��)�͵�·�����[���������{��(l��i)�Ե�·�M�^��ֻ�����b��ҹ���ġ��vʷ���߹�����Ԋ(sh��)�ĽY(ji��)β��n�������҂���������һ��(g��)���u��һ��(g��)���c(di��n)�����ɡ������ܿ���Ҳ���ӱ���ı��u��
ҹ�ı���/ �Пo(w��)߅�ļZʳ/ ���ĵĐ�(��i)��
���o(w��)߅�ļZʳ���������ĵĐ�(��i)�ˡ����@�ﶼ���нK�O��������|(zh��)���J(r��n)�������ı��ڱΘ�(g��u)���˱��u��(xi��)�����^�m(x��)��(xi��)�����������^(gu��)�ں�(ji��n)�λ��ˣ�Ȼ�����@�������K�҂����аl(f��)�F(xi��n)�����n�������ɣ�������(du��)�vʷ�������Ļ�ևһֱ���ИO�����е����ɣ������J(r��n)ͬ��Ԋ(sh��)�Ǒn�����d�w����������Ԋ(sh��)���R����Z(y��)������������ʹ��(xi��)���ɞ錦(du��)��և�ij��m(x��)��ʾ�����ɡ���ͬ�ӵ����ɻ��SҲ��������Ԋ(sh��)�����҂�һ�x���x�����ɡ�
�͡���և��һ�ӣ����n�����϶�Ҳ�DZ��u��(xi��)������Ҫ�ĸ��~֮һ����ǰ���ᵽ���LՄ�У����n�����d�w�����H�����u��(bi��o)�e����һֱ�ڌ��ҵ�Ԋ(sh��)�W(xu��)�����ұ��Á�(l��i)���������L(zh��ng)��Ư���Ќ�(du��)ĸ�Z(y��)�ĸ��ܣ��ڲ��_˹���������ġ������ܺ�����œ���⣬���ּ����ˡ����ڡ�������������������˼��Ԋ(sh��)���y(t��ng)�ġ���(d��ng)����ȱ�����ă�(n��i)�ڳ߶ȣ�Ҋ(ji��n)2003���4�ڡ�Ԋ(sh��)̽���������@�Ƿ���ζ����ͬ�r(sh��)Ҳ�ṩ��һ��耳ף���(j��)�˿��Ը�����ش��_(k��i)����Ԋ(sh��)��֮�T(m��n)�أ��Ҳ�֪��������֪����Ҳ����վ����Ԋ(sh��)���T(m��n)ǰ��Թ�����ö������Ǿ��҂�һ����(l��i)ԇԇ��Σ����^(gu��)ҪС�ģ������ɴ����γ�һ�N�µij�Ҋ(ji��n)������ǰ���u����Ԋ(sh��)���Ҷ��x�顰Σ�U(xi��n)��ƽ�⡱����(du��)���������x�߁�(l��i)�f(shu��)���@���S��һ��(g��)��(y��ng)ԓʼ�Kӛȡ����ʾ��
�����ѱ��u��ɢ��Ҳҕ��һ��(g��)ƽ������ء����u�_(k��i)ʼ��(xi��)ɢ���Ǿ�ʮ����к��ڵ��£���߀�l(xi��ng)���s��������Ԋ(sh��)���m����Ԋ(sh��)�ǘӳ�Ҏ(gu��)ģ���ƣ���Ҳ����У���Ҋ(ji��n)�ڡ����ġ�������t�Ⱥ��ڡ��x��(sh��)��������(sh��)�ǡ����s־���Ќ��ڣ���ɢ���еı��u��(d��ng)Ȼ߀��Ԋ(sh��)�˱��u���s������ݞ�Ó�� ������Ȥ�����L(f��ng)���ϵ����@��(bi��o)־��ͻ���ͷŴ���������Ԋ(sh��)�������[�ص��^(gu��)�����Ĭ��һ��(g��)��Ĭ�ı��u�DZ�Ҫ�ģ��������˸е��H�е�ͬ�r(sh��)Ҳ���˰��ģ�����������e���]���d��ȥ�꡶�ի@����6���ϵġ����l(xi��ng)����ա�һ�ģ������Խ���һ��̖(h��o)����ͬһ�������_(k��i)�ٵġ����o(j��)��朡����ڣ����С��堖�ӣ��ϙ��(sh��)�ֵ�һꇱ��L(f��ng)��Ҋ(ji��n)�d�����ܸ�ֵ���P(gu��n)ע������朡����@����ζ����һ��(g��)�˵�Ԋ(sh��)��ʷ�����ľ����Vϵ�����������{(di��o)���Ͷ������^(gu��)�̡���
�����Ư���Κv֮���u��������(gu��)���F(xi��n)�yŮ�����»������һ�������ڼ��ݴ��S˹����ǰ������Բ��r(sh��)�؇�(gu��)��̽ҕ���~���ಡ�ĸ�ĸ�����ĸ��H����ȥ���^(gu��)������Ը���˼ҵ�����֮�`��Ϣ���������Ⱥ�@���P��(hu��)�ČW(xu��)��(ji��ng)������(gu��)�����P��(hu��)�������Ɍ�(xi��)����(ji��ng)�������LJ�(gu��)�HԊ(sh��)�誄(ji��ng)�����@�����ĹŸ���ķ��(ji��ng)�W(xu��)���x������(gu��)ˇ�g(sh��)�ČW(xu��)Ժ�K��s�u(y��)Ժʿ�������������J(r��n)�ɵģ�ĸ�Z(y��)��������Ψһ�ĬF(xi��n)��(sh��)����������(gu��)������ͨ��һ���������һ���ČW(xu��)�s־�����⣬ÿ��߀Ҫ����W(xu��)��̃ɂ�(g��)�µĕ�(sh��)���ԾS����Ӌ(j��)����һƪ�L��(w��n)ӛ�����@�������Լ�Ŀǰ�������ճ̣������猑(xi��)����������˯������ȥ�������x��(sh��)�W(xu��)Ӣ�ģ��oŮ����������₀(g��)���������������Ϣ������������ϣ���һ��Ԋ(sh��)��(l��i)�����@һ�У�
�](m��i)���Ҹ���ֻ�����ɺ�ƽ�o
2004��2��9�գ���ͨ��Է��
�鿴106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