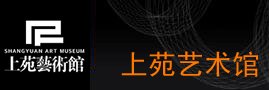七、我
苛多,你在哪兒呢?我老是問這樣的傻問題。已經不下百遍了。我知道。可我就是沒法
讓自己不問。在我還沒有埋葬自己之前,要是能再見到你該多好啊?我渴望你溫柔的撫摸,
你細細的親吻,你眼里流露出的關切以及你神經質地將煙頭扭成DNA形狀時臉上跟著扭動的
怪相。你要是在這兒,我會同意我們一起合葬的。我們將這個墓穴再加大一些,這不需要花
太大的力氣。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我不會像我姥姥和我爺爺那樣,哦,對不起,應該是
我們姥姥、我們爺爺,他們在死后的容器上,也就是棺材上,的確花了很多工夫和很長時間
來打造。
在我家——我們家——堂屋里老早就擺著一具棺材,我想那定是在我出生前就已經擺在那兒。
它的外面非常精致地打磨過,漆上了玫瑰紅的土漆。聽我爺爺——我們爺爺——在我姥姥—
—我們姥姥——哦,他媽的,我真不習慣這么叫——生前時曾用驕傲的口氣對他的同事們說
過,是上了五道漆的。
當姥姥串門去了,我和一幫子小伙伴玩捉迷藏,曾經和幾個大點的小孩使勁地搬開棺蓋,躲
藏在里面。我們便在一股濃烈的樟木香中躲到直至對方認輸,獲得最后的勝利我們才從里面
出來。被對方認為我們做了大逆不道的事,說要告發到爺爺那兒去。他們都知道爺爺是個孝
子,準會為這事打我,他們既出了一口因失敗而感到不快的氣又主持了正義。最后,我不得
不求他們別告,就算我們這方輸了,我這方其他的孩子因為也進了棺材,害怕受到牽連,就
只好和我一起認輸。
姥姥死后,大人們將她放了進去。給她換了老早就準備好的綢緞衣裳。手里放了幾枚舊時的
光洋,上面不知是蔣介石還是袁世凱的頭像,是爺爺特地為姥姥留著的;腳邊放了一些檀香
木香燭。外面的桌子上擺了好些吃的祭品。那張外公畫的姥姥的畫像上,圍著一個紅色的綢
緞扎花。
當天就在我鞋子的前半部縫了一塊紅布,手臂上一個紅袖套,頭上也是紅披麻。而爺爺他們
則都是白披麻、黑袖套。說是紅白喜事,有我這樣的第四代來為她戴孝是有福份的老人,是
可賀的事。爺爺要是知道有你這么個孫子而不是我這么個孫女去為他母親戴孝,還不定喜賀
到什么福份?
爺爺他們在家門前搭了很大的一個油布棚子,桌椅板凳擺了幾十套。各路前來吊唁的人絡繹
不絕。請了嗩吶等吹鼓手,敲敲打打了一個多星期。鄰居家那些天都不用開火做飯。特別是
姥姥不喜歡的對面王家一家十幾口人高興得手舞足蹈,天天在那些桌子間跑來跑去,比過年
還要熱鬧高興。我也受到感染,忘了姥姥的教導,跟在他們背后玩了起來。被爺爺揪回來狠
狠地揍了一頓,還不準我大聲地哭。
后來從棺材內發出很難聞的臭味來,灑很多花露水都壓不住。那都是為了等父親回來見上一
面后再蓋棺。
最后爺爺長嘆一聲:“唉,不孝的子孫。”就蓋棺起駕了。
在送姥姥去墓地的路上,成了當地多年來難以見到的一場聲勢浩大的游行。
隊伍最前頭的是舉著竹子和紙做的白旗幟、白幛子、白飄子的儀仗隊。足有100米長。緊接
在儀仗隊后面的是一組吹鼓手樂隊,鎖吶、笛子、笙簫、鼓和鈸……。吹吹打打的,我都忘
了是些什么曲調。因為我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后來發生的事上。
爺爺在一群人的簇擁和攙扶下,每一百來米就行一次大禮。三跪三叩頭三起,每遇路口還高
聲喊道:“娘呀,娘呀,您老別忘了回家。”
有人在他的身邊不斷地拋撒錢紙。那是姥姥活著時自己給自己裁成的一種長方形的、黃色的
草紙,上面有一串一串圓圓的釬痕。
我在爺爺那個方陣的后面,白衣裳上到處是些紅色的裝飾,紅披麻、紅袖套、紅腰帶、紅布
鞋頭。手上端著從客廳墻上取下來的我姥姥的畫像,有玻璃鏡框子。端久了就覺得重于“泰
山”,姥姥重于泰山。我由吳工家媳婦和大女兒負責照看,不得讓我走快了、走出隊伍了、該
行大禮的時候讓我行大禮、護著姥姥的照片不能讓我給碎了……。為了做到這些,她們倆沒
少費神。特別是當本該半小時就能走到墓地的路程,被爺爺指定繞著礦區游了一周,從而變
成三個小時的路程時,我感到我也想姥姥那樣躺在棺材里讓人抬著走。
在我的后面是由八條一般高的漢子抬著姥姥的棺材,另有八條漢子在邊上隨時準備替換,還
有兩人手里拿著兩條長板凳,在我們行大禮時將板凳放入棺材底下,讓抬棺材的人歇歇腳。
他們那里發出“哼哼卟卟”的、有節奏的聲音來。
最吸引我注意力的是在棺材方陣的后面,我奶奶和姑太她們的哭唱聲。奶奶用的湖南瀏陽官
腔,姑太用的湖北老家那兒的土腔,她們一把鼻涕一把淚,各唱各的內容,此起彼伏。說唱
的都是姥姥的一些事跡,她的美德、優秀、賢良、高品質、高風度甚至于好記性、好耳朵、
好眼睛……,最后是她的小腳如何地走路、她的布掛子斜襟扣衣裳做得如何地好、她的手是
如何地巧、繡品是如何地價值連城……。三個小時下來,那些內容一點都不重復。合起來就
像是姥姥的一部偉大傳記。可惜我都沒記住,那時沒錄音機。
當時騷擾我注意力和記憶的是一個念頭:我奶奶是真心地這么想就這么唱的嗎?我知道她并
不太喜歡姥姥,有時候都可能有點恨。
她們的后邊是爺爺奶奶的朋友們、同事們、鄰居們,以及像王家這樣一些愛湊熱鬧的、“沒教
養”的孩子們,成人手上或胸前都戴著白花。有人在隊伍里不停地放爆竹,王家的這些小孩
子們只所以能三個小時地跟著,主要原因就是這些爆竹吸引著他們。他們不斷地彎腰在地上
去搶那些啞爆竹,最后回到家里時他們的衣服口袋里都裝滿了啞炮。
這整個隊伍長達五、六百米,其聲勢的浩大成了以后幾個月里人們議論的焦點。這正是爺爺
要達到的效果。
爺爺對死亡的形式過分顯派的印象在那時就留給了我。使我終生都討厭參加這種熱鬧、累人、
漫長的活動。所以我不要什么葬禮,一個人安安靜靜在這片山上。死是絕對個人的事,就像
你的畫和我的詩一樣,都是自己的事。如果把它們變成公眾的事那樣去做,這死、這藝術、
這詩歌等就不再與我們有關。
最后我幾乎是被人架著拖回家的。我的腳重于泰山、我手上姥姥的畫像也重于泰山。如此疲
憊不堪地回到家中,迎面撞上的是父親和一個年輕女人談笑風生的場面。
我當時強烈地感到,父親就如我們捉迷藏時,躲進姥姥的棺材里那樣的大逆不道。但我已疲
憊得什么都記不得了。
不知是在多久以后,我在里屋的床上聽見了父親高聲大喊著:“救命啦!救命啦!”
要命的是他的叫喊聲響徹云霄,對面王家的孩子們都聽到了。之后,是一陣驚惶失措的敲門
聲、爭斗聲,人聲鼎沸……。
那是爺爺在狠狠地揍父親。
父親帶回家來的那個女人我再也沒有見過第二次。
王家的孩子們在以后的兩年里或更長的時間里,學著父親的外地口音和他當時的歇斯底里狀,
不斷地對著我喊:“救命啦!救命啦!”
他們似乎永遠也不會將這件糟透了的事給忘了。可學校里老師教他們的一切他們都記不住,
以致老二從五年級降到了三年級,老三從四年級也降到三年級,與三年級的老四在一個班上。
被教師們大喊著頭疼的三年級班。
這事使我倍受痛苦和屈辱,為此我并不想父親回家來,為此我恨王家的孩子們,也像姥姥說
的那樣鄙視他們。
姥姥去世后,家里空了許多。首先是那口玫瑰紅的棺材沒有了,讓我覺得少了一些負擔似的。
可不久,爺爺又請了木匠上家來,為自己和我奶奶打棺材。他自己的是買了上好的樟木做,
而奶奶則用的是山上隨處都有的杉木。這事奶奶沒說什么,但從她的臉上可以看出她心里對
自己的地位有認命的意味。過后她常對我說,在醫院里看多了人死,聽多了現代科學的新理
念,她對死后的尸體處理非常超然。認為爺爺還在舊思想里。當爺爺在家里時,她又是那樣
大聲地對我說:
“揚子啊,奶奶死后就靠你了,不要搞得如你姥姥那樣。人死如糞土,棺材也不要,放火葬
場去燒了,灰就倒河里讓它流走。”
這話我已經聽了上千遍。我爺爺有時候就說:“那不一樣,人死后有三個靈魂,一個在祖先那
兒,一個升天了,還有一個在身體的上空守護著。不能讓身體沒個樣子,或在大樹上掛著,
一直掛上千年那是最好的。但活著的人們不會讓它這么著,所以就得自己給它準備一個像樣
的容器。看看你父親,死得多么丑陋,死在監獄里,連尸體都不讓我們去收。他的靈魂都歸
不到位,誰能幫他?誰能拯救他的靈魂?”
啊!靈魂。我們的靈魂怎么啦?苛多,它也被揚子江的水淹沒了嗎?不,我的靈魂夜里垂掛
在樹葉上,白天穿梭在光影中。沒有什么能傷害到它,它不需要被拯救。它甚至不與我的身
體一同呼吸,肉體在墮落和消溶,靈魂卻始終保持它的鮮活與高貴,它與萬物之靈同在。
我在墓穴里坐了下來,開始吃最后的一頓晚餐。仍然吃得很香。
接著要吃的是那兩百片氯丙嗪。多是多了點,但保險。我才不會像那些天字號的大傻冒,去
吃那些藥店里能買到的“安定片”什么的。你就是吃上千片也死不了,還把自己弄得非常難
受。也不想想,誰都能買到一吃就能安靜地睡過去再也不醒的藥,那所有的失眠者都會死。
失眠者都有自殺傾向,是憂郁癥的一種。
當然,誰也阻擋不了一個真正想要死的人。老鼠藥、上吊、跳河或江或海、跳樓、炸藥、臥
軌、二氧化碳、飲彈、觸高壓電、過量注射毒品……;或干脆使勁吃,吃來撐死;喝酒,喝
來醉死;要不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吃,就這么干耗著,等著渴死餓死,變成枯樹枝。
所有這些方法我都尋思了一遍,沒一個有我現在選擇的這方法好。
吃老鼠藥會肚子痛,且口吐白沫,倒地抽筋什么的。苛多,你媽喝了太多的紅葡萄酒,所以
她身上開滿了花。但她后來仍舊倒在地上抽搐,樣子并不好看。或許她也疼的,只是她沒有
叫喊,因為她一直在聽我讀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但是有誰會有如此好的陪伴呢?在生
時的陪伴都不好找,死時還能有這樣的陪伴?我并不奢想。
上吊要吐舌頭,脖子上索出紅痕。當然,我爺爺這樣了不得的男子漢,在大山里的一棵大松
樹上,那景象就會有一種壯士的英勇。最好是永遠不要將他放下來,就這么永遠吊著。讓那
些肉一點點一點點化成水,滴干凈。最后只剩一幅骨頭架子,嘴張著,從中可以看到后面山
上的一點景色;眼睛也是圓睜著,也從中間穿過去能看后面山上的另一部份景色。當然,你
想讓它們關閉起來是不可能的了,這一點比較遺憾。要不然就如一個寶麗萊照相機,一按快
門一張圖片,再一按快門又一張圖片,最后將這些圖片一張張拼好,就是一個世界。
跳河得水深,否則死不了還在額頭上留個大青疙瘩包什么的。跳江,不成。我看到的江水都
是混濁的,泥沙太多。到時候嘴里鉆滿泥沙,你說那是個什么滋味?跳海是比較壯舉的事,
但海水是苦澀的,鼻子眼睛里那么一嗆,又痛又難受。我不開玩笑,準得折騰個把小時——
海水比淡水重,人要沉下去就得花時間。不信你去試試,反正我不用這法子。
跳樓“啪嘣”,血肉骨一塌胡涂。我母親決不是自愿選擇了這種方式的。不過有一點很誘惑我,
就是到一個上百層的高樓上去,在與地接觸前那段時間,少說也應該有十多秒鐘。那段時間
里我可以做多少個飛翔的動作?但為這十多秒鐘的愉快,將自己搞得一塌胡涂,不值。再說,
上哪去找上百層的高樓?就算找到了,人家讓不讓上去呢?你跟人說,讓我上那最頂層,我
要跳樓。人說,這得到某某部門去蓋章簽字,最起碼也得是街道辦事處,看看人家樂不樂意
讓你在這兒污染環境。然后是城管局、派出所、樓管辦……,一大串需要蓋章的地方,等你
蓋齊了,你差不多已老得沒力氣爬樓了。張國榮之所以選擇跳樓,那是因為他生活在香港,
一國兩制,那兒沒有大陸這么多的手續要辦,況且那兒經濟發達,四處有電梯,不用一步步
爬的。
炸藥“轟”,這種方式是以色列那地方常發生的事,被說成是人肉炸彈、恐怖分子什么的。一
聲巨響后,血肉橫飛,這兒一塊肉,那兒一截骨頭,半個肝臟貼在墻上,一段腸子掛上樹梢。
一會兒就飛來成群的蒼蠅。唉呀!我可不想成了蒼蠅的飯菜。
臥軌,讓火車將自己搞成幾節?像那個叫海子的詩人?他怎么就那么傻呢?尸首相分,血肉
粘著車輪子滾幾十里遠。要是遇到那火車司機是個小馬虎(現在的年輕人都是小馬虎),根本
就沒覺得輾著什么了,你又得被下一輛火車再切一次。那得是多少節了?我的老天爺!你得
讓人們滿世界一節一節去收集。就跟我們村的王老五那樣,肩上挎個籃子,手中拿著木條做
的夾子,看見圓條條的、軟軟乎乎的、臭哄哄的、有時還冒著熱氣的,就往籃子里夾。那是
什么?狗屎!誰樂意讓自己像狗屎一樣被人撿進籃子或塑料袋?海子啊海子!沒人細想過你
是否完完整整地被埋葬了,是不是有一個手指頭沒找見什么的。到另一空間,用另一種形式
生活,少了一個什么部件,這叫怎么回事呢?哈,我不干!
二氧化碳,吸煤氣什么的,像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人普拉斯?那氣味像臭蛋。而且死亡
的時間太漫長,得幾個小時。想想,一個人最后的時間是在憋氣的臭蛋味里結束,讓你的思
維亂的一團糟。你沒辦法從容地離開,再思路清晰地看著新世界的來臨。
槍!“嘭”,飲彈!飲彈!飲彈!像希特勒,對著腦門心,“嘭”!想再來一下這迷人的“嘭”!
都沒門,你已經飛了。哦!槍!手槍!那黑亮的鐵的重量!那食指扣動有彈簧的板機后的“嘭”!
一聲。然后是飛,慢動作地倒地,像一棵巨樹,朝著一個它想倒的方向“嘎——嘎——嘎—
—梆!”啊!帥呆了!包括“飲彈”這種說法都特別誘人。嗨!說那么多有屁用,上哪兒找槍
去?你以為這是美國?拿錢到商店就能買著?說不定在“9·11”以后,美國的店老板一看你
這長像,東方人!?嘿,給多少錢他也不賣你。
觸高壓電,“吱吱吱——嚓!”頭發全部成放射狀,像愛因斯坦?不對。我看見過觸高壓電死
了的人,面目全非,全身黑得象木炭。而且一股烤臘肉味,遠遠地就能聞到。這不成,遇上
木頭這樣嘴饞的,將你炒辣椒下酒吃了。
據我所知,吸毒——海洛因什么的,過量而死是上佳的選擇。但這得是癮君子才成,不然你
都不知道上哪兒去找這藥。滿大街去問,你有海洛因嗎?賣點給我,要多少錢我都給。你掏
出身上所有的錢來買,反正也用不著了,全給押上吧。不等你問上十個人,警察過來,不是
把你關進監獄就是把你送進戒毒所。死不成還活受罪!
誰?誰還有更高的招?說出來!說出來呀……
得,別再折騰了。思來想去呀,還只有我目前的方法是最好的。氯丙嗪!它讓你慢慢地放松,
不知不覺中你就舒展了四肢,躺得舒舒服服,一切人的煩憂、痛苦都一絲絲一絲絲、像裊裊
的炊煙朝空中飄去。剩下的就是一個透明的、干干凈凈的自然物。還有得是時間去慢慢地觀
看新世界是如何一點點一點點地降臨下來。
我數了數帶來的銀杏樹種子,一共十粒。白白圓圓,飽滿水靈。我深情地看著它們,對它們
說了人類最后的話:“請記住,我愛你們。用的是人的那種愛,希望你們在吸收我的肉體時,
別忘了也將我的愛吸收。”
說完,我看見白果們在我手上滾動了一下,似是在點頭。我放心地笑了。
原來想的是這十粒種子都和著氯丙嗪一起吞進肚子里,后來一想,不成。胃里有胃酸,說不
定會壞了種子。于是,我另外多設計了一些地方。
兩粒分別放在了兩個耳孔里,一粒放進肚臍眼,留兩粒含在嘴里,其余的都與藥一起吞進了
肚子。
我平躺下,在藥效發揮作用前的半小時里,我要用鏟子將土一點點地往自己身上拔。先從腳
那頭鋪起,漸漸地鋪到了脖子。由于只是薄薄的一層土,我沒感到難受。但我想盡可能多的
將土鋪到身上去。在我脖子以下我能感到沉重起來時,我的手已累得有些酸痛。剩下的只有
頭和兩上肢了,這會兒我還不想將它們蓋起來。
我握著鏟子歇息片刻。這時,所有我認識的人,都來找我了。活著的尖尖、格子、木頭還有
表叔,要與他們道別;死了的也表示他們歡迎我。
苛多,在我認識的人里,你是我最需要道別的。我知道你大概是在西伯利亞的白樺樹林里,
像列維坦那樣畫畫。我知道你的下落,你也知道我的下落。可我們不能見面,哪怕是我要死
了,我也不能在活著時與你道別。但你會到我的墳墓所在地來,我知道。我還知道,你會一
個人來,但就是別他媽的哭。你一哭,你的眼淚和鼻涕定會將你的臉弄得很難看。我可不愿
意看著你的鼻涕從你的鼻子里流出來而不伸手幫你擦了。那樣,突然從墓穴里伸出一支手來,
說不準還是變了色的手,在你的鼻子上那么一抹,定會嚇得你掉了魂兒。你就帶兩幅你畫的
畫來,我喜歡你那幅《庭院深處》的油畫。我還是不能忘了你的吻,你吻得那么有神,細細
的、淺淺的、密密的。還有你的眼睛,你看著我時,它是獨立的,它脫離開你的身體,專注
地審視我,像一個掃描儀、一個攝像機、一臺X光機或CT機……。我不能準確地說出它是什
么,總之它是我的資料庫,它里面保存了一切真實的我。而且,它比國家檔案館的管理還要
有章法,不會有遺漏和丟失。
木頭、尖尖、靜靜或格子、姥姥、父母、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還有表叔什么的,這些人留
給我的記憶似乎都不如你那么刻骨銘心,他們只不過是組成了我生活的一些章節,留下的是
一些故事,而且是獨立成章的故事,不與我手掌上的生命線相交叉。我死了對他們也不會造
成太大的影響。他們照樣可以按照自己原來的生活軌道繼續下去,走到他們自己的終點。只
有你,苛多,我們像兩條天津麻花般紐在一起,自從不得不拆開來的那個時候起,我們就碎
裂成一小段一小段的。主要的問題是一開始就他媽不該紐在一起。可是誰知道呢。我那混賬
父親從來就不曾好好兒干點正事,將它那些混賬種子播種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其實,當然,我爺爺,我姥姥,還有我母親,一想起他們我是很愉快的。我馬上就要見到他
們了,我是說真正地見到他們并與他們一起飄舞。我得記住我母親是住在那棵大銀杏樹下。
我爺爺剛才來見過我了,但我怎么就忘了問他呆會兒上那兒去找他呢?不過沒關系,他肯定
在大山里的一棵最大的松樹上住著。我姥姥住的房子一定是由紅土漆漆過的,那比較好找,
而且我爺爺也定和她住得不遠,找到其中一個就能找著另一個。
這時我開始犯起困來。我知道,藥在起作用了。
我停下來,將鏟子使勁推出到墓穴的外面去。可那鏟子又落了回來,邊上的土堆堆得太高且
又是斜坡,而這時我的力氣似乎已經沒有了。
我想,鏟子就讓它留在里面吧。
在我迷迷糊糊要睡著時,這鐵鏟讓我不能平靜。它對樹的成長形成了一種障礙。于是,我努
力讓自己醒過來,再一次伸出雙手,拿起鐵鏟,朝著我腳的方向,用盡所有的力氣,將它推
出去。
我再也沒能感知那鐵鏟最后的落處。
在我必須關閉的眼簾里,一團一團如霧的彩云飄了起來。被白果堵塞的耳朵里,一種多聲部
的大過八度的和聲“隆——隆——”響起。
有雨水落下,我高興地將手掌舒展開來,任雨水濕潤它。
——我聽見我的心跳聲和著雨聲在漸漸遠去。
由彩云聚集了一個浩大的空洞在空中飄浮,接著旋轉起來。我在旋窩中向著一個亮點飛去。
一種失重的、危險的快感盈滿全身。
2003年3月完稿于上苑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