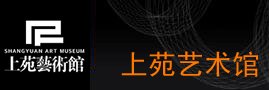|
程小蓓的小說<<你瘋了>> 十一
[2006-10-1 13:35:08]
六、我
昨天挖的那個一米寬兩米長的墓穴,實在是小了點。于是,我又加大了一圈,可能有兩米寬
三米長了。這樣工作量增多了,我更累得不行。
做人的這幾十年里,大多是在干些腦力勞動。對這體力勞動還真沒心理準備。我想這工作今
天又完不成了,何況我的肚子餓得極沒教養地亂叫起來。
于是,我放下鐵鏟,回那江邊的古鎮上去了。
遠遠地就能看到各種彩燈將寨子亮得通明,這里真是民風古樸,鄉情濃郁。我人還在祠堂外,
女店主就迎了上來。她問“大姐,要吃點什么不?有清蒸甲魚、有紅燒荷包紅鯉魚、有清蒸
草魚頭、有石雞、有粉蒸肉……。”
“好好好,都弄來。”這人間的最后一頓飯,管它的,樣樣都嘗一下。
那女店主反到傻了,剛才那么起勁地吆喝著她的菜譜,生怕沒人吃,這下子她說:“大姐,都
上么?”
“是的,是的,都上。”我有些不耐煩了,有人送錢上門來吃你的東西,還不趕緊做來。
“大姐,你吃不了那么多的。”女店主很固執也很關切地說。
“嗨,我說,有你這么做生意的嗎?你有什么花樣都使出來,吃不吃的完那是我的事。”
“哦。”
女店主不再遲疑,手腳麻利地進了廚房。我想何不利用人間最后的這點時間再學點東西帶到
另一個世界里去,人說多一門手藝就多一個飯碗。于是,就跟著女店主進了廚房。
瓷瓦罐里放著一只一斤多的甲魚,她只放了兩片姜,一點鹽,放微火上去燉。她說要一個小
時以上,上桌吃時絕對是一流的味道。
接著她做紅燒荷包紅鯉魚,說是這里的特產,與別處的鯉魚不同,是獨特的淡水魚種,釣魚
臺國宴珍品。她活鮮鮮地現殺現宰,魚兒把血甩得四處都是,拼著最后的那點點力氣,徒勞
地掙扎著。看著它,我感到我是幸運的,至少我是自己結束自己的性命,雖然活著不免也被
人牽制和被人宰割,但死是沒有被別的什么來左右。最后我還是嘗了一下這道菜,沒覺得有
什么特別之處。
最后我看好做那道石雞,其實并不是什么雞,而是青蛙,更大些的青蛙,也就是牛蛙,搞那
么些怪名字就為了吊客人的味口。像我這樣的食客,這卻是浪費!我真后悔當初想豪華一下
的想法,但為時已晚。我不得不讓她給我做幾個小菜,什么涼伴竹筍、小炒白菜、四川泡菜
等。好家伙,菜擺了一桌子,我坐在桌邊看著它們熱氣騰騰,我卻沒有了食欲。
女店主一家大小伙計,遠遠地看著我吃吃發笑,輕輕地議論著。我有些生氣,最恨有人背著
說三道四的,我也拿眼睛遠遠地看著他們。嗨!我的天!他們點亮了一盞兩百瓦的大燈泡,
燈泡下看那女店主居然是尖尖。難怪他們看著我吃吃地笑,原來都是些熟人。尖尖周圍的那
一幫子伙計原來是孫文波、沈睿、胡續冬、蔣浩、林木、冷霜、汪國精、傅維、黎二,畫家
七斗、八斗什么的,畫村長……,
我沖著尖尖說:“你不是在東帝汶的古斯芒總統手下當官員嗎?怎么跑這兒來開館子了?還能
燒這么一手好菜。”
“那是多年以后的事,我現在得練就一身武藝才能夠得上古斯芒總統對我的要求。”
“不錯,你是比原來要成熟些了。”
我干脆對著那一家子說:“你們大概還沒吃吧?吃了也再來吃一點。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大
家來幫我慶祝慶祝。”
“ 我們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所以招集大伙兒來吃你一頓。”孫文波說。
“你們沒讓木頭來是對的。不然……。嘿嘿……。”我又想起木頭從不拉下什么宴席的毛病,
不免覺得好笑。
林木和蔣浩搶著說:“你對木頭不公平。”
“木頭不是你想象的那樣。”
“哦,好好好——。老板!嗯,尖尖,咱們吃火鍋怎么樣?”我敢緊轉移話題。
“老姐,你要吃什么都可以,我馬上就給你弄來。”尖尖應聲下了廚房。
“你那破拉達車應該去處理了,嗯?早就到了報廢的年齡,留著是個麻煩。啊?”汪國精老
著臉,拖腔拖調地說。
“嗨,不就行車證上用了你的名嗎?你怕什么?反正現在一切都無所謂了,你要將它怎么著
都可以,處理權歸你。”
“怎么讓我處理呢?這是你自己的事。”汪國精要叫起勁來也真讓人難受。
“呃——,上苑村那房子你也得處理,開發商已經將那片地買了,他們將按每平米一千七補
償。”冷霜低著頭納納地說。
“啊!好事。我那房子有兩百來平米,二一得二,二七一十四,三十四萬。不錯,是個好價,
冷霜啊,你就留著這筆錢,好好找個女孩結婚,過過人間的生活。”
“這我可不能接受……。”
不等冷霜說完,蔣浩說:“我是一個漂浮不定的人,一會兒在北京、一會兒在海南,下一個時
辰在哪兒我都不知道,戶口的問題你也得去解決了。”
“哈哈哈——,你們不要我都要了。如果沒有簽那個不生娃兒的合同,連娃兒我也要,唉—
—,一條命啊,一條爛命!”孫文波笑兮兮地說著,轉過頭去問林木:“林木,你那電話號碼
是好多?”
“9717”林木說話簡練干凈。
“就這么多?”
“嗯。”
“好哩,少,我也要。”孫文波露出的收荒匠的表情。
“木頭呢?木頭誰要?”我問。
胡續冬從他上衣兜里掏出一個從衛星直接收發信號的手機出來說:“他早就失蹤了,多少年前
他去尋找你,就再也沒有回村。我對從衛星發回來的圖片做過仔細研究,地球上任何一個角
落都沒有他的蹤影。”
孫文波說:“你當然找不到他的蹤影。那年全世界鬧‘非典’的時候,他得了‘心理性非典’
死了。”
“‘心理性非典’怎么也會死呢?”一直沒說話的沈睿不解地問。
“嚇死的。曉得不?”
“不明白。”
“哪個都曉得木頭是個不講衛生的家伙,啃手指甲、搓痂痂……。那些日子電視天天講要洗
手消毒,講究衛生。不然就會咳嗽、發燒、爛肺缺氧死掉。木頭邋遢慣了,一不留神就把臟
手放嘴巴頭去咬。等他發覺,臟東西都吞進了肚子。這下子,木頭想,不得了、不得了,SARS
病毒入侵了我。好,他就開始覺得喉嚨痛了、咳嗽了,他跟到就想,我的肺要爛了。嗨,你
說怎么樣?”
“怎么樣?”眾人被孫文波的話吸引進去了。
“他就真的咳出濃痰來,還帶有血絲絲。他怕被隔離,想著反正都是一死,還是個人死得自
由自在些好,就不去醫院看病。但是他就是不發燒,別個都燒到三十八、九度,稀里糊涂的
死了。他到好,清醒白清的死了。”
“不可能。你狗日的亂說。”傅維腦袋搖晃著說,“真得了‘非典’都不得全部都死,他這種
個人想出來的‘非典’到是死了,哪個信喔——。”
“嗨,誰知道‘非典’的治愈率有多高。”八斗插話說,“我一個朋友住在火葬場附近。他說,
那些日子火葬場加班加點工作都搞不贏。”
“電視報紙上都說的很清楚,一半以上都治愈出院了。”林木在《環球青年》工作,所以他的
消息都比較官方。
黎二站起來,手上拿著筷子對著眾人指指點點地說:“哼,這些你們都信嗖?瓜娃子還差不多。
官方的東西有一半都聽不得。你們也不想一下,六零年前后中國死了好多人?哪個曉得。統
計了也不得讓我們這些老百姓曉得。文革死了好多人?我曉得我們新二村都有幾十個,全市、
全省、全國死了好多?乘法?還是開方?你們想一下會有好多?反正從電視報紙你都聽不到
真實具體的東西。就是現在電視報紙說真的了,也沒得哪個敢信。你們信……。”
沒等黎二說完,畫村長對我說:
“不管木頭是不是得‘心理性非典’死的還是失蹤的,總之我都早已經將他的名字從村民名
冊上消除了。我這次來是要注銷你的名字,好多人想頂替你的名進咱們村。那可是一片上好
的風水寶地,你想想,它屹立在皇帝的腦門心上。得,你在這文件上簽個字,你的事就算完
了。”
村長武斷地作了結論。
這些人是怎么了……?啊……?嗨!其實也沒什么,你不是要離開人世了嗎?自然你身前的
物品、包括你的名份,就得有個交待。是啊,物品都交待了,名也注銷了,還有什么要交待
的嗎?沒了,要交待的是你自己的靈魂。
……
我說:“其實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孫文波,你不過是想找借口收荒,收下最后這桌飯菜。哈
哈……,也對,也對,也可以說是生日,與人的生日反著的那個生日。”
他們開始不怎么言語了,臉上露出疑惑和不信任的表情。尖尖端著紅油火鍋放在桌子上,眼
睛看著我,好像我沒錢來付這頓宴席款似的。我不想臨離開人世前看到這些令人不愉快的表
情,先將身上所有的錢都掏出來放在桌子上,說:
“將這些錢都拿去,反正我也用不著了。哦,還你的身份證,沈睿,還給你。”
我將一張發黃的、揉得皺巴巴的身份證遞給沈睿。我看到另外那些人嘴張得老大,將我看著,
不,不是看著,是瞪著。只有尖尖走到桌前來,小心翼翼地說:“老姐呀,你先吃。吃完了,
再結賬。不忙的。要不了這么些錢。”
那兩百瓦的燈泡突然“啪”地一下——燒了。那伙人立馬又恢復了原形——沒一個是我認識
的。接著他們的臉像不斷變換,眼睛由小變大、鼻子塌變高、嘴唇由薄變厚、腮幫子上由光
溜處長出毛來……。而且他們遲遲疑疑,最后還是坐在了桌前,尖尖試探性地問:“老姐不是
有什么想不通的吧?那可不敢,你們大城市的人活得多好啊!”
我笑笑,這可不象是尖尖說話的口氣,認真一看,不是尖尖,確是女店老板。我不想回她,
只將菜一一嘗了。我說:“不錯,很好吃的。來,來,來,大家一起吃。”
大家似比前要緊張一些,與我對視著,看我只是從容不迫地笑,也覺得是自己多慮,就跟著
我一起吃了起來。一瞬間,桌上的盤碟便都空了。席間還有人想問我一大堆問題,什么你是
哪地方人?家里還有誰?干啥工作等。我都只是笑著看他們很響地咂巴著嘴,一直說兩個字:
“好吃,好吃。”
在那鎮上飽吃了一頓,又將“夫妻肺片”、涼伴三絲等打了包,用快餐盒裝上,準備明天帶上
山去吃。然后到樓上的客房洗一個澡,再美美地睡一覺。
早晨,我輕松地朝著我的墓地走去。
最后這天的工作十分順利。一個寬敞、舒服的墓穴漂亮地完成了。我看著它就如在歐典
家私城里看著那從意大利進口的雕花紅木大床般,它只能屬于一個高貴靈魂的安息處。人死
后有三個靈魂,一個與祖先匯合,一個在床上,還有一個守著他生前的身體。所以一個人有
時間的話一定要在死前好好地安頓自己的床穴與身體,讓它們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就像我現
在所做的。
我抬頭看了看多云的天空,希望它在我死后能下一場雨。這便于種子發芽。
揚子與苛多
“揚子,揚子,是不是我們都死了?你剛剛說的靜靜她媽名叫馬驪,為什么是叫馬驪?為什
么與我母親的名一樣。是不是我們都在死的臨界狀態中?你得告訴我,如果我們都死了,你
愿不愿意我們合葬在一起?”
“苛多,你是怎么了,我們早就死了。在你還遠沒有死的意圖前,我們就死了。”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揚子。”
“有些問題是不能回答的,就如你從來沒有告訴我你到哪兒去了,最后看見你是在揚子江的
浪中,你的T恤在黃濤中一起一落。但我知道你一定是在列維坦的大白樺林里,這是你最后
唯一可能去的地方。”
“不管我在哪里,揚子,你都是我唯一的親人。我愛你。就是在你殺了我母親之后,我也仍
然愛你。”
“告訴你,苛多,我沒有殺你母親。這是真的。在我的思想里絕沒有這樣的愿望。是她自己
殺了自己。我們一回到家,奶奶就告訴我們,她找到了格子的母親;還告訴我們,尖尖已經
出國,去了一個剛剛獨立出來的熱帶國家。你問這國家的名字是不是叫東帝汶,奶奶說不清
楚,但奶奶帶我們去見了格子媽。見著格子媽時,你臉色蒼白、頭腦發暈,你叫她‘媽媽’,
而我叫她‘靜靜媽——馬驪阿姨’。第二天早晨起來我就再也找不到你了。你母親瘋了,真的,
她自己在紅葡萄酒里放了藥,自己喝了下去。我們就坐在我和靜靜常坐的那個竹制的書架邊,
我還在翻看靜靜原來留下的那些書,幾乎都在那兒,整整齊齊、一塵不染,我看著那本《裴
多菲詩選》心里想,那時候多么迷戀那首《這個世界是那么大……》的情詩啊,‘……不要望
我,低下你的眼睛——/不然我的靈魂要燒毀了!/可是,你既然并不愛我,/那么就讓這可憐
的靈魂燒掉!’想想我們為這些句子怎樣地感嘆,我竟笑了起來。這時你母親也笑,刺耳的笑,
像小時候我和格子刺耳的哭。你母親手里端著一只高腳玻璃杯,將一包藥倒進去,斟上紅葡
萄酒,用一根筷子在里面攪拌,是畫著圈那樣的攪拌,一圈一圈地攪,攪一圈她的身子也跟
著搖一圈,嘴里也隨著發出一聲尖笑。后來她尖笑一聲我就讀一行詩,先是讀裴多菲,后來
讀《歐根·奧涅金》,讀了多久,我不知道,直到你母親說,人哪!人哪——。突然,她停止
搖動,一仰脖子,將葡萄酒倒進嘴里,吞下。葡萄酒太多,嘴太小,紅葡萄酒灑了她一身。
真的,很好看的,很好看。那天你媽穿著白色的連衣裙,一朵朵的牡丹花盛開來。你母親瘋
了,我沒瘋。她說,格子就是靜靜。如果她說的是真的,那格子就是我表叔的情人。而我和
我表叔殺了她,我殺了我的姐姐,表叔殺了他的外甥女,而你母親殺了她自己。這是真的嗎?
你一定得告訴我。他們為什么把我從監獄里放了出來呢?他們可不該放過一個殺人犯。”
“揚子,我知道你牽掛尖尖,我去看過她了,我也牽掛她,她也是我妹妹。她告訴我,她的
確愛過我,但她現在在古斯芒總統手下工作,她瘋狂地愛著英俊的古斯芒總統,成為東帝汶
國唯一一位外籍女官員。我告訴她,我愛你,讓她見到你的時候一定告訴你。我知道他們會
將你從監獄里放出來的,他們不會槍斃一個瘋子。真的,就是在你瘋了以后,我仍愛你。”
“我沒有瘋!如果我瘋了,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不瘋的。在你將我一個人撇在這個陌生的世界
上后,我找你,天天找你,結果找到了木頭。木頭告訴我,他就是你。那你得說他一定瘋了,
怎么可能呢?木頭是木頭,苛多是苛多,風馬牛不相及。你知道嗎?苛多,木頭對我的傷害
達到了我所不能承受的極限。有一天我回到我租住的房子里去,他在門口擋住我,要我去住
旅館。我問,為什么我不能住我自己租的房子呢?他說,內分泌在里面,他要和內分泌在這
里住。苛多,你會做出這樣的混蛋事來嗎?不會的,你決不會的。要說瘋,遇到這樣的事真
能叫人瘋。”
“揚子,人有時候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個什么東西,再純情的人也會有混蛋的時候。在發生了
這一切之后,在我知道你就是我繼母的女兒之后,我還是愛你。”
“木頭身上盤旋著你的魂魄嗎?他是你投胎所得?是不是在投胎時,你去除了祖先的某些基
因,從而發生了一些偏差?但愿木頭就是苛多,苛多就是木頭。苛多的朋友們都搬到了上苑
村,上苑村就成了藝術家村。藝術家村的人自然就成了木頭的朋友。將那些哥們,像孫文波、
林木、蔣浩、沈睿、冷霜、汪國精、胡續冬,畫村長……,這些人是真的嗎?我的確見過這
些人。你認識他們嗎?2002年10月份他們又在這兒舉辦一個‘上苑藝術家工作室開放展’,
我在所有文化藝術網站上都刊發了此消息。你一定看到了,我有意這么做的,為的是讓你能
看到。你看到了就會來找我,就會來上苑村,將我從木頭身邊帶走,或者將木頭的名字改成
苛多。我知道改名很難,派出所的人難纏。”
“揚子,當我知道你父親也就是我父親之后,我仍然愛你。不是兄妹那樣的愛,而是情人那
樣的愛。我渴望占有你,擁有你,像母親肚子里永不出生的龍飛鳳舞胎,赤裸著、緊密地、
隔絕于世地在一起。如果我們生不能在一起,那就死在一起,葬在一起,像木乃伊一樣用香
草、麻繩捆扎在一起。你愿意嗎?為什么你不回答這個問題?揚子。”
“你也沒回答我的問題。噢!這么說你真是我哥哥?你也就是木頭?”
“是的,我不但是你哥哥,還要是你的父親,你的愛人。我的心讓我去愛,去自由地行使身
體的需要。有了你之后,我的身體再也不能接受其他任何一個女人。人間任何的規則都管不
住我。”
“苛多,你還活著嗎?活在人世間?這人世間存在了千百萬年,有一套共認的道德規范,你
不能不顧及。”
“繼續活著,為誰而活著?我只為你而活著。親情、愛情,它們是我活著的唯一理由,也是
我繪畫的源泉。沒有了這些勿寧死。”
“那我們得遠離人群、遠離社會,進入植物的環境。”
“揚子,你一定要變成一棵銀杏樹嗎?”
“這是我想了很久的結果,我想不出還有比這更好的主意。你有更好的主意嗎?”
“有,你如果是一棵樹,我愿是那樹上的一只鳥。”
“嘿嘿,苛多,你怎么將舒婷蹩腳的愛情詩也拿來用上了?”
“哦,媒體將它傳播的次數太多,條件反射。總之我的意思你明白。”
“唉,苛多,你要是真這么想,你就得忘記沙發、忘記電腦、忘記汽車、忘記房子、忘記榮
辱、學術地位、工資報酬、甚至忘記尊嚴……。剩下的就只有情和愛。”
“難道我們擁有了親情和愛情就一定要失去其它一切嗎?如果沒有選擇,那就讓它們去吧。
何況這是我們自己的事,與他人無關。”
“如果你是以人的狀態活著的話,你就不會這么說了。”
查看7032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