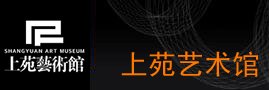秦曉宇詩(shī)話(huà)·關(guān)于馬驊《雪山短歌》及其它
馬驊的《雪山短歌》由三十余首五行詩(shī)組成,其中第二十九首《念青卡瓦格博》是一首未竟之作:
給山林冰涼泉水的,是念青卡瓦格博。
給村莊金黃玉米的,是念青卡瓦格博。
給河谷……
戛然而止。后來(lái)的事念青卡瓦格博知道:他年輕的生命,給了河谷,他已化作詩(shī)中永恒的省略號(hào)。今天,我試著把《念青卡瓦格博》續(xù)完,狗尾續(xù)貂,聊寄思念罷了。
給山林冰涼泉水的,是念青卡瓦格博。
給村莊金黃玉米的,是念青卡瓦格博。
給河谷寂靜長(zhǎng)風(fēng)的,是念青卡瓦格博。
給冰川巍峨云彩的,是念青卡瓦格博。
給信仰無(wú)限神秘的,是念青卡瓦格博。
酒與茶
這兩種飲料代表古往今來(lái)兩種不同的詩(shī)歌精神。陳繼儒在《茶董小序》中說(shuō):“熱腸如沸,茶不勝酒;幽韻如云,酒不勝茶。酒類(lèi)俠,茶類(lèi)隱。”詩(shī)人宋煒說(shuō):“酒主飛揚(yáng),茶司內(nèi)斂。”都是肯綮之言。由此我們可以籠統(tǒng)地說(shuō),1980年代的詩(shī)歌多是“酒”,豪氣干云、激情澎湃、少年意氣,如癡如狂,醉態(tài)乃常態(tài)。1989年以后,“酒”醒了。有的人干脆戒了酒(放棄寫(xiě)詩(shī)),還有的風(fēng)格開(kāi)始轉(zhuǎn)變,傾向于釀造一種更接近茶的詩(shī)歌飲料。而在一幫聲稱(chēng)寫(xiě)出了口語(yǔ)詩(shī)的詩(shī)人那里,我們看到的不是詩(shī)歌流派,而是可口可樂(lè)公司。不久前的趙麗華事件卻說(shuō)明,不買(mǎi)你帳的不是別人,正是民間本身。這是題外話(huà)了,時(shí)值歲末,我們還是別拿可樂(lè)來(lái)辭舊迎新。
馬驊喜歡喝酒,也常以酒入詩(shī)。如:
又一個(gè)晚上,又一次,對(duì)著
空洞的啤酒瓶編織虛妄的詩(shī)篇
《微笑的崔》
海濱大道,更換著
嘔吐物的垃圾箱
一瓶啤酒把海峽之間
塞滿(mǎn)憤怒。
《秋興八首》
一杯啤酒帶來(lái)遺忘,兩杯啤酒
把邁克扔回徐家匯的角落
三杯啤酒喚醒肉體的欲望,第四杯
又帶來(lái)了哀傷。
《邁克的霧月十八》
完美的一天,總是從酒精開(kāi)始
《完美的一天》
與其他嗜酒的詩(shī)人相比,馬驊之愛(ài)酒至少包含下面兩個(gè)特殊的原因。一是童年經(jīng)驗(yàn)。在一篇半自傳體小說(shuō)《逍遙游》中,他寫(xiě)到一個(gè)孔乙己式的人物,何瘋子,這是個(gè)不可救藥又有點(diǎn)神秘的酒鬼,在被酒徹底廢掉以前,能寫(xiě)一手漂亮的顏體。后來(lái)的歲月中,何瘋子逐漸成為馬驊的一部分,在小說(shuō)里,“我”一陷入潦倒的爛醉,何瘋子就會(huì)沖“我”微笑,朝“我”走來(lái)。北方的酒鬼確實(shí)像馬驊描寫(xiě)的那樣:“喝不起瓶裝酒”,“眼睛里掛滿(mǎn)血絲,胡子茬總是青青的。當(dāng)小伙計(jì)用鋁制的長(zhǎng)柄小斗將酒斟入他們自備的酒盅時(shí),他們的神情就像現(xiàn)在買(mǎi)了彩票等著電視里搖號(hào)的人們一樣。” 的確,我們北方的童年記憶,“醉”的形象與美酒佳肴無(wú)關(guān),與醇酒美人無(wú)關(guān),醉就是爛醉。第二,受武俠小說(shuō)影響。在《青春》一文中他寫(xiě)道:“對(duì)武俠小說(shuō)的愛(ài)好一直保留到了十幾年后的現(xiàn)在。一有閑暇我仍會(huì)到街頭的書(shū)攤?cè)プ馍蟽杀荆源虬l(fā)無(wú)聊的時(shí)光。我記得金庸說(shuō)過(guò)武俠小說(shuō)最大的特點(diǎn)是讀者可以代入,把自己想象為江湖上孤傲的游俠、精通易容術(shù)的大盜、令無(wú)數(shù)美女傾心的浪子。雖然多少有些滑稽,但當(dāng)時(shí)我樂(lè)此不疲,直到現(xiàn)在仍是如此。”不能說(shuō)獨(dú)行雪山的做派、“千面馬驊”的外號(hào)、“風(fēng)流天子、浪子班頭”的自況,與他對(duì)武俠小說(shuō)的喜好無(wú)關(guān)。金庸小說(shuō)中,馬驊最喜歡有著酒一樣性格的楊過(guò)與令狐沖,古龍的小說(shuō)更是塑造了一批極具魅力的酒鬼,這些酒鬼想必一直都在馬驊的內(nèi)心世界里游蕩。
懶散的黑人每天按時(shí)出現(xiàn)
坐在酒吧間漆黑的鋼琴前
隨手彈著某支老情歌
總會(huì)有異鄉(xiāng)的人默然無(wú)語(yǔ):
那是我們年少時(shí)為之?dāng)嗄c的旋律啊
馬驊《卡薩布蘭卡》
酒吧里的“異鄉(xiāng)的人”,很像《多情劍客無(wú)情劍》中在孫駝子開(kāi)的那家雞毛小店里久久寓居的李尋歡。
臨近三十歲時(shí),馬驊對(duì)酒的態(tài)度有了微妙的變化。他開(kāi)始感嘆“毒啊,毒啊/ 打磨著堅(jiān)韌的鋼腸鐵胃,消損著/ 生銹的金剛不壞身”(《邁克的冬天》),以及“一抹銳利的酒精/ 刺傷生銹的喉管”(《睦南道》)。再后來(lái)他去了梅里雪山,《雪山短歌》近40首,竟然絕無(wú)飲酒,倒是開(kāi)始喝茶了:
山溪
石頭的形狀起伏不定,雪水的起伏跟著月亮。
新剝的樹(shù)木順流而下
撞擊聲混入水里,被我一并裝入木桶。
沸騰之后,它們裹著兩片兒碧綠晶亮的茶葉
在我的身體里繼續(xù)流蕩。
用陳繼儒《茶董小序》中的話(huà)說(shuō):“悠然林澗之間,摘露芽,蒸云腴,一洗百年塵土胃”。作為生活方式,馬驊仍喜歡喝酒。戒掉酒的,是他的詩(shī)。明永的潛移默化,令一個(gè)曾浪跡于百丈紅塵的酒徒,寫(xiě)下“幽韻如云”的詩(shī)篇。
山景
馬驊《雪山短歌》中第13首《雪山上的花開(kāi)了》,很可能受到六世達(dá)賴(lài)倉(cāng)央嘉錯(cuò)的一首小詩(shī)的影響。馬驊的《雪山上的花開(kāi)了》如下:
山上的草綠了,山下的桃花粉了;
山上的桃花粉了,山下的野蘭花紫了;
山上的野蘭花紫了,山下的杜鵑黃了;
山上的杜鵑黃了,山下的玫瑰紅了。
偷睡的年輕漢子在青稞田邊醒來(lái),雪山上的花已經(jīng)開(kāi)了。
而倉(cāng)央嘉錯(cuò)那首小詩(shī)是這樣寫(xiě)的:
山上的草壩黃了
山下的樹(shù)葉落了
杜鵑若是燕子
飛向門(mén)隅多好
馬驊
還有一個(gè)名叫馬驊的詩(shī)人。筆名莫洛、林渡、林默等。浙江溫州人。生于1916年,1938年組織海燕詩(shī)歌社,主編《暴風(fēng)雨詩(shī)刊》。我在百度搜索莫洛時(shí)發(fā)現(xiàn),連馬驊復(fù)旦大學(xué)的同窗都把兩人搞混了,在馬驊遇難后寫(xiě)下:“我還記得他的筆名好象是莫洛……”
一個(gè)馬驊在梅里雪山腳下的明永村擔(dān)任義務(wù)教師,另一個(gè)曾執(zhí)教于西子湖畔的杭州大學(xué);一個(gè)英年早逝,另一個(gè)年過(guò)九十,仍精神矍鑠,八十歲時(shí)還出版了一本詩(shī)集,書(shū)名非常延年益壽,叫《生命的歌沒(méi)有年紀(jì)》。
野馬
我寫(xiě)過(guò)一則《翻譯之誤》的詩(shī)話(huà)——
“馬驊曾談起《米拉日巴道歌集》的一個(gè)漢譯錯(cuò)誤,‘我雖凝身不動(dòng),卻心猿意馬’(大意)。他覺(jué)得如此翻譯,幾近詆毀。米拉日巴是噶舉派二祖,一個(gè)卓越的苦行者,這個(gè)翻譯卻給出一副毫無(wú)定力修持的形象,馬驊覺(jué)得應(yīng)該翻譯成:‘我雖凝身不動(dòng),卻心如野馬’”。
對(duì)此唯阿反駁說(shuō):
“馬驊認(rèn)為幾近詆毀,可能是不了解佛教中‘心猿意馬’一詞的具體含義。佛教是一種詩(shī)意哲學(xué),多用意象,強(qiáng)調(diào)審美直覺(jué)。在佛經(jīng)描述的六十種心相中,最后一種為猿猴心,‘心如猿猴,游五欲樹(shù)’,謂此心如猿猴,攀援外境;心的‘意’,流注不息,一味追逐外境,猶如奔馳之馬,故稱(chēng)‘意馬’。‘心猿意馬’是成道的大障礙,因此必制伏之而后可。與此同類(lèi)的意象還有狂象(醉象、惡象)、六賊、牛等,都用來(lái)比喻為害極大的妄心。”又說(shuō):
“按我的理解,馬驊生活在高原,因此才更傾向于‘野馬’這樣的雄奇的意象。這是心造境,也是方便法門(mén)。假如他像古印度人一樣經(jīng)常能見(jiàn)到大象,他也會(huì)傾向于‘狂象’、‘惡象’這些相類(lèi)的雄奇之意象。”(《心猿和野馬》)
近日偶涉佛典,發(fā)現(xiàn)唯阿的反駁頗不能令人信服,“心如野馬”恰是標(biāo)準(zhǔn)的佛教用語(yǔ)。東漢支讖譯《屯真陀羅所問(wèn)如來(lái)三昧經(jīng)》:“其心知若幻如夢(mèng),如野馬,如山中響,如水中影已,堅(jiān)固無(wú)所希望,是則為寶。”西晉聶承遠(yuǎn)譯《超日明三昧經(jīng)》:“觀一切法如化,如幻夢(mèng)、野馬、影響,悉無(wú)所有。”竺法護(hù)譯《度世品經(jīng)》:“……猶如幻夢(mèng)、影響、芭蕉、電現(xiàn)、野馬、水中之月”,等等。
如果馬驊讀過(guò)這些典籍,那么他用漢地佛教術(shù)語(yǔ)來(lái)翻譯藏傳佛教經(jīng)典,可謂適當(dāng)。如果沒(méi)讀過(guò),那這簡(jiǎn)直是神來(lái)的譯筆,一如伽葉得如來(lái)妙諦的“微笑”。
化用
馬驊《雪山短歌》的第一首《春眠》似乎受到莎拉’克爾石(Sarah Kirsch)的《在夢(mèng)中》的影響。我是在趙霞的《小譯集》中讀到克爾石這首詩(shī)的,我想那本小冊(cè)子馬驊手頭也有。趙霞翻譯的主要是這位德國(guó)女詩(shī)人的幾首田園詩(shī),開(kāi)闊澄澈的詩(shī)風(fēng)始終與毛驢、奶牛、地平線、糞堆、“扣人心弦的星辰”、“殘暴而啰嗦的風(fēng)”、小農(nóng)莊、飼料、綿羊等鄉(xiāng)野風(fēng)物聯(lián)結(jié)在一起。關(guān)于自己的隱居生活,克爾石在《心滿(mǎn)意足》一詩(shī)中寫(xiě)道:
每隔一個(gè)禮拜,磨坊主就會(huì)在星期一開(kāi)著他的奔馳車(chē)經(jīng)過(guò),來(lái)問(wèn)我是否需要訂購(gòu)些什么。因?yàn)檫@微不足道的小農(nóng)莊是我作為一個(gè)改頭換面了的城里人,活過(guò)了半輩子后,才終于得到的,我愜意的感受可以和一個(gè)剛做過(guò)變性手術(shù)的人相比……
而馬驊去了梅里雪山之后的變化,似乎也可以跟做過(guò)變性手術(shù)的人相比。我們來(lái)比較一下《春眠》和《在夢(mèng)中》:
1、春眠
夜里,今年的新雪化成山泉,叩打木門(mén)。
噼里啪啦,比白天牛馬的喧嘩
更讓人昏聵。我做了個(gè)夢(mèng)
夢(mèng)見(jiàn)破爛的木門(mén)就是我自己
被透明的積雪和新月來(lái)回敲打。
在夢(mèng)中
迷路者徒勞地敲打著
這些傾塌的門(mén)不能
把人性給出
這兩首詩(shī)都很短,都寫(xiě)到夢(mèng)中的景象,夢(mèng)中都有破門(mén)和對(duì)它的不停敲打,那門(mén)也都被人性化了。所不同的是,對(duì)于《在夢(mèng)中》的迷路者,一扇敲不開(kāi)的門(mén)(“傾塌”,暗示里面無(wú)人)是個(gè)多么冷酷的“沒(méi)人性”的家伙。而對(duì)于馬驊,“破爛的木門(mén)”應(yīng)是他作為浪子的自況,他不遠(yuǎn)萬(wàn)里來(lái)到梅里雪山,不就是為了接受“積雪”和“新月”的再教育嗎?
借深心
韓博的組詩(shī)《借深心》是一種奇特的詩(shī)題押韻,其中每首的一字之題都是仄聲“ì”韻,如《致》、《契》、《避》、《匿》、《濟(jì)》……孤字如讖,據(jù)我所知,這種僅以一字命名的“險(xiǎn)題”,除了《詩(shī)經(jīng)》中有不多幾首之外,只有《周易》廣泛采用這種命名方式。同一的韻腳是個(gè)有力的結(jié)構(gòu),將難言的,“仄”起不“平”的隱痛收攏“深心”。這是一組極具漢字性的作品,文約而指博,言微而意深,堪稱(chēng)“字”的魔術(shù),最后一首《替》尤其極端:
飛機(jī)生鱗,他生覺(jué)悟:無(wú)憑甚飛出個(gè)有?
飛機(jī)生趾,他生酬唱:長(zhǎng)夜哪般短按摩?
飛機(jī)生角,他生相忘:亡去煩惱歸去心?
寥寥三行,卻綜合運(yùn)用了各種漢字修辭手法:有“悟:無(wú)”、“唱:長(zhǎng)”、“忘:亡”的諧音修辭;有“忘”析為“亡”、“心”(“‘亡’去煩惱歸去‘心’”)的離合修辭;有“他生”這種歧義修辭(“他生發(fā)出”的“他生”,或“他生未卜此生休”的“他生”)。這首詩(shī)用了《詩(shī)經(jīng)》當(dāng)中的《麟之趾》的典故,《麟之趾》是一首關(guān)于某位振奮有為的公子的贊美詩(shī),《替》也是如此。至于《麟之趾》的“麟”為什么變成了《替》中的“鱗”,那是因?yàn)樵谶@一偏旁部首的修辭中,隱含著一出墜江的悲劇。而韓博最深的心意還不止于此。與“他”相連的“生”字豎排下來(lái),恰好疊加成“三生”! 這絕非過(guò)度詮釋?zhuān)@里暗含了另一個(gè)對(duì)于本詩(shī)更加關(guān)鍵的典故:唐朝高僧圓澤和李源是好友,圓澤投胎轉(zhuǎn)世時(shí),和李源約定十二年后的中秋夜在杭州天竺寺相會(huì)。十二年后李源如約前往,見(jiàn)一牧童在牛背上唱歌:“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fēng)不要論。慚愧情人遠(yuǎn)相訪,此生雖異性長(zhǎng)存。”這便是“三生有幸”的由來(lái),它關(guān)乎一種空靈得風(fēng)月無(wú)邊,深厚得穿越生死的中國(guó)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