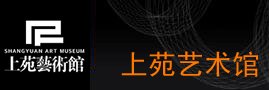|
蔣浩《海甸島》
[2012-8-6 17:39:09]
蔣浩《海甸島》
一棵樹
根須在黑色泥土里糾纏。痛苦的,發情的,腫脹的根須,一粒粒因吸滿光而表面凹塌的泥土穿行于她的纏繞。是少女的,也是老人的,他們保護自己的方式是捂住眼睛和臉:這土中一粒土也像空中一片石。根須在黑色胸膛中糾纏,吐出骨頭的枝柯,眉毛的樹葉,還有一對眼睛的水果。語言,像淚水順著脆敗的臉流回來,白色的,一咬即破。
那棵樹在空中:一只耳朵或一座小島,探測到一種光線的顫栗。他書寫藍色的詞,甚至胡須似的龐大的根須也浸泡在透明藍色的玻璃瓶里。我在樓上聽到的聲音,相似于我在院子里撫摸過他粗糙的樹干,——那是一個刻滿篆文鳥蟲的鑄鐘,里面虛空而黑,但飛鳥在上面撞出了火星。
我數著:一棵,二棵,一棵……。所有的樹都是一個詞,同一個詞。圍繞著弧形沙灘,像一截眉毛。有時候,海水吧這沙灘修飾得又細又長,那棵露出白色根須的樹傾著身體:它感到一座海的重量,但壓力來自下面和遠處。我從它身邊經過,我用一個思想交換了它的輕盈。樹冠像一掬海水濺瀉在散文的沙灘上。我聽你說:“看翠巖眉毛還在不?”(《景德傳燈錄》卷十八)
月光升起于那片樹林中的某棵樹:白色的圓口杯從漆黑的深井汲滿水,上升的軌跡像是要退回到頭頂的一朵云里。我涂抹這面窗,企圖抽出一些曲線來紋身。我摸到一些恥辱和幻想。越過它,遠處是海,我的島像一個孤獨的講臺,旋轉,在浪尖上那么緩慢地分泌著細沙。月光改變著樹冠的顏色,像一朵云的陰影正溶入它的反面。
我找到一棵樹,在一塊小小的礁石里。我向她說話,她就開一些白色的花。我砸開它,那棵樹就落下黑色的果實。我把這塊礁石埋進了沙里,它在慢慢變熱,成熟。我在另外的沙中撿到一根新斷的幼枝,像是飛鳥身上掉下的一枚羽毛。我把它埋進沙里。我向她說話,她在慢慢變冷,長大。那只鳥停進了她的樹冠,像一塊黑礁石,在慢慢睡眠。我找到這棵樹,它向我說話,用鳥語,它長出的果實是一枚枚礁石孵出的鳥蛋。我砸開它,那棵樹還在里面。
一棵樹是一棵樹。一棵另外的樹飽含激烈的情緒,它在林子里追逐另一棵樹,被視為盲目。要是飛起來,要是倒出樹冠里的海水,要是把樹干削弱,抽出里面的釣絲,要是把根須編成一張網。它追上另一棵樹,用鋒利的樹葉去詛咒和砍伐;它抱住傾倒的樹干,一起倒下,被視為和解。
帶細孔的黑色火山石
問:“如何是和尚本分?”(慶諸)師曰:“石頭還汗出么?”(《景德傳燈錄》卷十五)
雪霽辭后,地藏門送之,問云:“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物唯識。”乃指庭下片石云:“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文益)師云:“在心內。”地藏云:“行腳人,著什么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即放包依席下,求抉擇。近一月余,日呈見解說道理,地藏給之云:“佛法不恁么。”師云:“某甲詞窮理絕也。”地藏云:“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于言下大悟。(《文益語錄》)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慶諸)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么?”曰:“不會。”師曰:“賴此不會,若會即打破爾頭。”(《景德傳燈錄》卷十五)
一滴海水進入。一仄花瓣進入。一抹青草進入。一星星火進入。滿島都是帶細孔的黑色火山石,水已從里面流盡了。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子儀)師曰:“大洋海里一星火。”僧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一)
地下的宮殿。裸露的黑色石頭,吃著光線。從這些光滑細小如水泡的孔洞里,魚兒游入了海里。饑餓的石頭,它的黑色像件空蕩蕩的牧師袍,思想的煙頭燒出了上面的細孔。但你說這石頭來自地下教堂而非宮殿。——地獄?
是從恥辱柱上脫落的嗎?我燒,我燒呀!我把指頭摳進這些細孔,它像一個扭曲的面具。
是滿海的火焰雕刻成這海甸島?滿島都是帶細孔的火山石。我們用它去與海游戲:扔,像是在提問?
石頭的舞蹈。在它們排成整齊的防波堤前,大海蹲下身子,展開她巨大的白色狐貍尾巴
那只黑色的海燕停在石頭上,像她突然長出的一個欲望。她多空的表面遠比幽閉的內部深刻得多。
雷陣雨
她整個濕漉漉地被驚呆了。但她的眼睛是干的,腳板心也是干的,她看不見最好的避雨的地方是在她的眼睛里。
她被撫摸了嗎?像此刻的海面因雨鼓起了肚子。輕微的雷聲在那里顫動,雨滴長出的毛毛腳,在她身上亂跑。而我們的島夾在兩撇波浪之間,曾是一塊石頭受到雨的點化后,在波浪中輕微地搖晃,像一只慢慢成熟的芒果。她被撫摸了嗎?在兩排波浪的齒痕之間,它曾是一滴小雨而受到雷之棒喝。
雷在海邊滾動。想一想,峭壁上幽穴里一窩雷鳥蛋將裂開,長出骨頭和羽毛來。一個浪一個浪,舔著毛絨絨的雨腳,她的嘴泛出細嫩好看的泡沫。世界之寬廣,我們聽到雷聲滴進堅固的石頭里,海水煮石呢。想一想,那只鳥是雷鳥,一聲是盛唐,一聲是南宋,把一排排浪壓進環形戒指里。我叫著,叫醒她,勢必要給你戴上。
她剝一半的橘子,一半遞給光線,一半吃。濕漉漉的山脊,給她遞來的一杯水,也是海水。
她跑起來,一閃一閃的。如果她真的跑起來,是白色的,在沙灘上又變成了藍灰色。她像去撕一個傷口上的創可貼。跑起來,跑起來,她永遠是難以愈合的那一部分。如果她聽下來,也是一閃一閃的。
雷聲是一個混合物,從海面馳過來,一杯水在窗臺上,去澄清它。冰涼的液體,留下它虛無的體溫。她鉆進白色的電話線。她的手機響了。她摸到了按鍵,是一盞燈,打開,流出了水,還有一些沙。
雨水總是站在那里,伴著輕雷,求解答。
自言自語的一對,應許了諾言。輕飄飄的一對,完成了重重一擊。
為什么要憂郁呢?每一條路都到海邊。雨突然堵在門口,雨也在路上。出門就是雨,路旁小小的喇叭花倒過來就是一把傘。鋒利的草葉禮貌地雕刻你的裸足,給針細的傷口抹上新鮮的濕泥。無論你的臉看起來多么的不幸,每一粒雨都能在那里找到位置,并漸漸干涸。但你的臉絕不會因面前的海水而凋謝。
為什么不是馬蹄在空中濺出的泉水呢?有人用閃光的扳手和鐵釘補綴著發暗的天空,那塊烏云像恰好的補丁,旁邊那塊像是解釋、補充和說明。我們的頭上干干凈凈,是天花板,白色的。窗外是粗狂的棕櫚,蒼老胡須的榕樹,秀氣的檳榔……它們中突然缺少了什么?它們突然停在各自的位置上。從我們的屋子里跑出一匹馬,兩片云給它插上了翅膀。
風過耳
關好門窗。報上說,去年一場臺風帶走了一條船和船上的四個漁民,一周后,另一場臺風又把他們全部帶回了港口。那四個漁民看起來心情不錯。親人們詢問他們那幾天的經歷。他們說,滿海都是風雨,根本不知道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有記者感嘆他們為何如此的幸運。他們說,是因為后來在海上,被迫放棄了任何求生尋路的努力。
他們趕在臺風前再藍色鐵皮圓桶里翻檢垃圾,打開一個個白色的、黑色的、紅色的塑料薄膜垃圾袋,里面有來自肉鋪、理發店、小餐館、辦公桌……的遺留物,臟臟的,像天上越來越多的陰云。還有一團破布,廢鐵絲,缺頁少封面的卡通書,無墨水筆,帶細孔的衛生巾,一截大腸般皺塌的避孕套。而更多的生活垃圾袋里都是飯粒,發黑的剩肉,黃瓜的苦蒂,空心菜的黃葉,干癟的小奶瓶,長方形的牛奶紙箱……我一直都往這個垃圾桶里傾倒我的生活垃圾。有一次,我用一個干凈好看的塑料袋裝了一條褲腳有小口的褲子。還有一次,是一件只穿了一次的絳紫外套。我希望他們被領走。
臺風過后,鐵桶里積滿了水,外面是凌亂的垃圾,也被積水淺泡著,像是這只鐵桶口的嘔吐物,環繞著。
風找到些云的裂縫以及它在遠海的倒影,一起吹過來。雨直直如發,貼在頭發上橫飛,像一個人突然有了莫名的悲傷猛跑起來。如果拿這兩者和悲傷相比,悲傷原本是安靜的, 像一只狗蹲在屋里,只有當外面的風停止之后,它才出來狂吠一通。
有一次我頂風騎車往回趕,直到雨大起來時,才到路旁一棵大榕樹下躲避。已有一個人在那里,他也緊靠著他的自行車。我們沒有說話,直到雨停后分開,他離去的方向與我回家的方向正好相反。我想著他要到達的什么地方,因為那個人很面熟,實在太像我在大陸的一位朋友。后來我見到我的朋友,并向他談起這事。他竟然立刻肯定那個人就是他。他說,他曾經夢見來島上看我,騎著自行車被雨困榕樹下,他看見了我,但不敢相認。我自然不相信他的夢。他竟然出門直接就把我帶到那棵榕樹下。我醒來后,想了想,確實知道那個人不是他,但樹一定是同一棵樹。
陽光下的熱帶海洋在野蠻地成熟。每次臺風都是收割。船消失了,親密地靠在海灣看著新鮮的黝黑的波浪。風暴的聲音很大,海甸島仿佛是一塊凝固的帶尖角的石頭。風災每一處細小的裂縫里尖利地摳挖著,要鉆進去。停電、停水,使用油料的車也停進了車棚。但這是一個節日,波浪在海上變出了很多圓形劇場和角落。島下沉了一部分,可以肯定是這喧騰之海的一部分。我們也更近了,也許一出門就可以是踩上波浪的尾巴。
今天的風不帶來雨。那個翻檢垃圾的婦女傾斜著鐵皮垃圾桶,她的蛇皮口袋沉甸甸地橫亙在自行車的后架上。倒空的黑色塑料袋往天上輕盈地飛。她沒有落下任何東西,連口袋里的垃圾也是玩好的。她還要騎車去另外的垃圾桶。她的衣角向后揮動著,像她的孩子在后面用指尖不停地捻扯。她褪下手套,緊緊抓住車把。我看不見手套,只有在她要翻閱垃圾時才會出現。如果風順便帶來雨,我也許會看見那雙手上被雨洗出的藍色的靜脈。
2004年6月20日,海甸島
明月照
比如說,月光照在島上與海上并無二致。想象著這樣的情致,想象與月光照在島上與海上并無二致。當你來到海邊,像月光照在海上,你與一座島也并無二致。世界通過“我”去想象他們自身時,我對世界的想象被限制在“我”中。世界想象我,美好一夜降臨在沙灘上,無論向哪邊邁步,都進入世界的想象中。一只鳥兒停在天空于棲于樹上幽穴時,翅膀沒有拋棄它。只有在它睡眠時,翅膀才夢見它。無論在飛翔、棲息與夢之間是如何發生變易的,這只鳥像一個拳頭,沒入海水,它的凹凸皮膚上的皺紋浸漬了細沙,是海水的聲音凝固而成,是一座 。我們洗手時,他同時也帶走了原本是我們手的皮膚的聲音。我們的手光潔如月光,可以像花瓣慢慢展開,手掌是翅膀的一半。這只手飛起來,劈開波浪,一朵烏云潛艇般沖向它的胸膛。鳥兒美妙的鳴唱改變它的尖刺和方向,他變成了一截漆黑的柔軟的樹枝,波浪如嫩葉可采擷筑巢。你用舊了這只手,日日洗不過是用新的灰燼蓋住舊的廢墟。兩個手掌十根手指,對應于十次機會兩次成功?我總是先用左手給右手洗手,即使兩只手都因自我的洗滌而重新變臟。洗手不干其實是洗手不干。水也臟了,比手臟,比以前的水更臟,因為我的手帶走了它的無。我看這雙手,它把我的心變成了一個手形。我用它去捂胸口,當我的心因手受傷而隱痛時,兩顆心如此偎依在一起。我把它伸在月光下治療。月光照在手上與鳥上島上海上并無二致。想象著這樣的情致,想象與手與島與海傷害了月光。我的手要那月亮但從未得到。它靜靜地滑行,在你的子宮里。
我的耳朵有時能聽見她的吮吸,不傷害耳朵。我感到是我的一截手指在那里爬行,像一只越來越臃腫肥胖的蜜蜂投身于任何一朵不知名的花蕊里,美妙的香氣透過皮膚傳遞到耳朵里時已是低微的抽泣,不是傷心,而是感恩。我的手指有一天會粗過蛇的細腰和天鵝的曲徑。它蠕動,吐出月光般的絲絨。它嘔吐,子宮細微的振動像磁化。有時候,我把自己的手指伸在月光下,看月亮在藍色夜空因磁化而圍繞它緩緩移動。手指下的陰影從平坦窗臺爬上矮墻,再掉進地板的方格里,但沒有聲音。我把它伸進溫熱的嘴里吮吸,光是甜的,指頭是涼的。月亮是一個盛滿潔白冰糖的玻璃罐,我的手指接近它,堵住它的敞口。我用勁輕輕摁,絲絲縷縷的白云從它周圍緩慢飄出來。云是甜的。月亮是一個閃光的陶瓷開關,如果關上它,就能看見繁星。我不停地按動,我不漢子道悲哀的事物究竟隱藏在它的身后還是身邊。開關壞了,要不就是它真把我當成了一個淘氣的孩子。她以為我的手指像一串冰糖葫蘆伸到她的嘴前,她吻而不是咬,眼睛里流出細小的瀑布,每一絲水流都像潔凈的手指,梳理著他們,歸于一個水蛇盤繞的水妖的渦旋狀頭飾里。那水妖在夜里歌唱,即使用月光堵住耳朵,它可以從嘴進入,鼻子進入,那歌聲可以久居不散地貼在皮膚上變成新的皮膚。無論月光怎么洗濯,它依靠完美的反光來稀釋碰到的光的濃度和熱情。
查看30256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