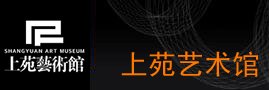|
從英譯文看中文詩、東歐詩和日本詩 (西川)
[2007-10-28 16:29:04]
從英譯文看中文詩、東歐詩和日本詩
西川
我同時讀著一堆詩集和詩選,這其中包括奚密(Michelle Yeh)翻譯和編選的《中文現代詩選》(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耶魯大學出版社,1992)、《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154期詩歌專號、格萊姆. 威爾遜(Graeme Wilson)等翻譯的《當代日本三詩人詩選》(Three Contemporary Japanese Poets,倫敦雜志出版公司,1972)、保羅. 默讀恩(Paul Muldoon)和大衛. 萊曼(David Lehman)編選的《2005年美國最佳詩選》(The Best American Poetry 2005)等等。由于是將翻譯成英文的中文現代詩與其他國家的詩歌混在一起讀,因而對于現當代中文詩歌的國際呈現略有感慨,進而加深了我對于中文詩歌本身存在的一些問題的認識。可以說,除了個別中文當代詩人的作品,絕大多數詩人的作品翻譯成外文以后完全處于失效狀態。
這種失效狀態不能歸咎于譯者。僅就奚密《中文現代詩選》而言,她所進行的雖屬學術翻譯,不是詩人翻譯(例如不是龐德式的翻譯),但其學術翻譯水平依然是可以信任的。我知道還有一些現當代中文詩歌譯本:Kai-yu Hsu編選和翻譯的《二十世紀中國詩選》(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 Doubleday & Company, Inc.)、葉維廉(Wai-lim Yip)編選和翻譯的《現代中國詩選:二十位中華民國詩人》(Modern Chinese Poetry: Twenty Poets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艾奧瓦大學出版社)、托尼. 巴恩斯通編選的《風暴之后:中國新詩選》(Out of the Howling Storm: the New Chinese Poetry,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我模糊記得還有一本王平翻譯的《當代中國新詩選》,據說張耳也翻譯了一本。與我所讀到的中文詩選英譯本相比,看得出,奚密的譯本是多年心血的成果。奚密長期任教于美國大學,對中文現當代詩歌的來龍去脈、現實處境應該說爛熟于心。其翻譯著作也不止這一本,其翻譯質量曾經得到過包括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稱贊。我在此根本不想苛求哪一本譯詩選,任何譯本都是對中文新詩傳播的貢獻。不過,按說有了這些譯本[還有一些綜合性的譯本,例如Kai-yu Hsu 編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作品選》(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Joseph S. M. Lau 與Howard Goldblatt 編選的《哥倫比亞大學版現代中國文學作品選》(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閔福德(John Minford)與白杰明(Geremie Barme)編選的《火種》(Seeds of Fire: Chinese Voices of Conscience)、Lee Yee 編選的《新現實主義: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國寫作》(The New Realism: Writings from 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ippocrene Books, Inc.)等等],中文詩歌至少應該給英語世界留下點印象了,可惜除了朦朧詩,竟然沒能給別人留下什么印象。如此看來,這就不僅僅是一個翻譯的問題了。即使翻譯有問題,我們也可以退而援引博爾赫斯的觀點:好的文學作品可以戰勝粗制濫造的翻譯。
本文的目的,在于不避偏見地約略檢討一下中文現當代詩歌寫作本身存在的幾個最基本的問題,并將視野稍微打開,看看與我們同屬東亞的日本詩歌以及與我們具有相似的現代政治歷史經驗的東歐詩歌的寫作狀況。我并不想拿翻譯成英文的中國現當代詩歌與英語詩歌作比較,我只是試著在另一種語言里為中文詩歌找兩個鄰居,這就像我們根據中譯文,比較一下尼日利亞和烏拉圭的詩歌。我相信肯定會有中國詩人不自覺地這樣做。否則我們在中文中就不敢斷定波德萊爾是比什么波德菜爾高一些的詩人。另外,既然我們可以為中國古典詩歌在翻譯成英文以后依然在某種程度上保存了中國古典詩歌的光彩而驕傲,那我們也就不妨順帶看一看我們能否為已經翻譯成英文的中文現當代詩歌而驕傲。如果你反對后一種做法,那么也請你反對前一種驕傲。我知道詩歌翻譯的問題非常復雜。沒有人敢口無遮攔地斷言存在一種標準的國際性寫作(盡管的確有人談到過當代世界詩歌的共同性),但也沒有人敢大張旗鼓地否認中文現當代詩歌已經在相當程度上現代化了。而“現代”,或許正可以被用作一個詩歌的公分母(當然不是唯一的公分母)。從翻譯的角度討論中文當代詩歌可能有違民族主義情懷——干嗎不能從中文文本入手討論?但從中文文本入手討論是另一項工作。如果我們強調各民族語言都有其獨特魅力,那么我這樣討論問題可能還有違“政治正確”的原則。不過我要說的是,無論什么樣正確的觀點都無法掩蓋大部分中文詩歌在進入英文或其他語言之后所呈現出來的缺陷或尷尬。從生成的意義上說,沒有哪一個詩人的作品可以擺脫其語言、傳統、審美、政治和道德的上下文。但事實卻是,越稱優秀的詩歌越渴望一試超越上下文。而糟糕的詩歌往往向上下文求來太多糟糕的借口。在中文環境中,我們已經聽到詩人和讀者們對翻譯問題多有抱怨,但只是一味抱怨我們沒有好的翻譯恐怕遠遠不夠。
可以從遠處說起:臺灣詩人A在中文語境中號稱后現代主義高手,又能寫詩,又能寫小說,又能搞文學評論,可他的詩歌翻譯成英文以后真的不成氣候。一些煞有介事的修辭,例如Push open the night(打開黑夜。從“打開窗戶”而來,玩的是感覺錯位),缺乏直接性,又不具彈跳力,顯得小氣巴拉。而這,還一度為讀過幾首臺灣現代詩的大陸詩人和批評家們所津津樂道,以為這就是現代或后現代了。于是 就出現了“我把你望成一座山”這類愚蠢的句子。詩人A的詩歌在進入英文以后生氣全無,既看不到寫作手法在思維意義上的創造性,也沒有顯現出良好的文學趣味(或反文學的文學趣味),也沒有價值觀上的革命(或反革命),也沒有對于世界、生活、個人存在的嶄新的發現,更別提什么稍高一點的連類歷史與文明的文學抱負。像You look but do not see it; /You listen but do not hear it; /You grab but do not touch it(意思是:你看卻沒看到;你聽卻沒聽到;你抓卻沒觸到)這樣的好象充滿現代絕望、荒誕,發現了現代生活痼疾的小排比句真情宣喻,也就將將可以哄哄高中生。
不只是詩人A的問題。進入英文以后,大陸現代詩人中人氣兒最高的詩人B的老底兒,一下子顯現出來,而且是過于顯眼地顯現出來:在英語詩歌的意義上說,B詩太19世紀末了,而且是19世紀末英詩中最要不得的那一種;在中文詩歌的意義上說,他的詩里彌漫著一種20世紀初錯把摩登當現代的習氣;B喜歡標榜自己的英國范兒,但如果將他的詩與同屬19世紀晚期的勃郎寧、史溫朋、莫利斯、羅塞蒂,甚至王爾德、吉普林的詩放在一起,其差距豈止百里!或者B的詩是中國人寫的,應該有些英國詩人不具備的中國味兒,但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喝過點洋墨水的文學青年的多愁善感。其他中國詩人好一些嗎?詩人C太象征主義了,而且是一本正經的象征主義,進入英文以后,幾乎沒有什么鮮活的東西,其所謂的詩意離抓人的詩意總好像隔著一層紙。詩人D是玩東方感覺的人,應該在英文語境中格外顯眼才對,但他的禪意缺乏驚喜,缺乏使人驚訝的力量,和美國同樣玩禪意的加里. 斯奈德、雷克思羅斯、W. S. 墨溫(有時)等詩人比起來,他的禪意竟有點像北宗神秀的禪意。E的詩歌之美屬于文學青年所理解的文學之美。F存在是存在,卻沒有任何能夠站立起來的的意象,而且高潮進入得太慢——如果有高潮的話。G太松散,可能正是這種松散導致了虛張聲勢。H有點現代主義,但把現代主義鼓搗成了從鄉下來到城里的小知識分子的小玩意兒。J還處在尋找女神的階段。H的現代主義全是詩意的核心詞,而這些核心詞卻最終沒有道出什么太核心的東西,也就是說,H始終處于詩歌的核心地帶,但缺乏對這核心的反省。臺灣詩人、大陸朦朧詩以后的詩人在其英譯文中所暴露出的問題我就不一一列舉了。也許我過于苛刻。
主要是語言問題。是透過英文看到的中文詩歌語言問題。我這樣說是把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擱置在了一邊,之所以擱置在一邊,乃是由于在這些被收入奚密《中文現代詩選》的詩人中,96%的詩人不懂這個問題。什么問題呢?寫作觀念的問題。我這里所說的寫作觀念,既是就詩歌思想性而言,也是就詩歌寫作方法論而言。當代東歐詩歌在語言上既不搞超現實主義,也不搞自由聯想,也不搞矛盾修辭,頂多弄一點口語,但在東歐詩歌里充滿強大的寫作觀念,而且其寫作觀念與詩人的存在處境緊緊地扣在一起。這一特點保證了東歐詩歌的生命延伸到東歐各語言之外。東歐老去或已死去的詩人們,波蘭的赫伯特(既有思想又有方法)、申博爾斯卡、米沃什、捷克的赫魯伯(既有思想又有方法)、塞爾維亞的伐斯科. 波帕等等,我們姑且不說。我手邊可以夠到的更年輕一代的詩人,像克羅地亞的托瑪什. 沙拉門(Tomaz Salamun,1941~)等,在寫作觀念上并不輸與老一代。從已經翻譯成英文的《為麥特卡. 卡拉碩維奇而作的謠曲》(A Ballad for Metka Krasovec)、《憂郁四問題》(The Four Questions of Melancholy)、《筵席》(Feast)、《托瑪什. 沙拉門詩選》(The Selected Poems of Tomaz Salamun)等詩集來看,沙拉門寫的是那種任你怎樣狠狠地將它們摔在地上,它們都要跳起來咬你的詩歌。也許作為一個國土面積一點點、政治上更談不上強大的克羅地亞的詩人,沙拉門就該 寫這樣的詩歌。這樣的詩歌他寫起來一點也不含糊:“每一個真詩人都是頭巨獸。/ 他毀人也毀他們說話的方式。”(《民歌》)
還是回到語言問題上。沙拉門的語言基本上是口語,是當代中國年輕詩人們所熟悉的口語。沙拉門是這樣寫的:“托瑪什. 沙拉門說,俄國人滾蛋!他們就滾蛋了。”(《箴言》)——好像俄國人退出東歐政治舞臺是沙拉門的功勞。但難道他沒有功勞嗎?在這里沙拉門喚起了語言的魔法。沙拉門又寫道:“丟/ 女人/ 比丟錢/ 更讓人/ 舒心/ 而最/ 讓人/ 舒心的是/ 丟掉/ 你自己的/ 死亡。”(《詩歌》)——在女人、金錢和死亡這三者之間,沙拉門安排下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甚至有違傳統公共道德的順序。這和“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的價值觀是滿擰的,和“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也是敵對的。在一首名為《我有一匹馬》的詩中,沙拉門列舉了他所擁有的東西:“我有一匹馬。我的馬有四條腿。/我有一臺錄音機。我趴在我的錄音機上睡覺。/……/我有火柴。我用火柴點香煙。/我有個身體。我用身體做最美麗的事。”——這是我喜歡的口語:有力,出人意料,聰明,直指生活真相,還憨憨地說廢話。沙拉門不屬于任何詩歌流派,也就是說,他不擁有任何原理性的寫法。他的長處就在他的語言。這種語言并不是克羅地亞人的專利,日本詩人也可以把詩寫得直接和機敏。與安西均(Anzai Hitoshi )和谷川俊太郎(Tanikawa Shuntaro)一起被收入《當代日本三詩人詩選》的白石嘉壽子(Shiraishi Kazuko ,1931~)寫過一首詩,名為《冷肉》(Cold Meat)。《冷肉》中有一行說:“我撒謊時根本不開玩笑。”
我找到了白石嘉壽子的兩本英譯文詩集。一本名為《神圣淫者的季節》(Seasons of Sacred Lust),由美國新方向出版社在1978年出版,另一本名為《小行星及其他詩歌》(Little Planet and Other Poems),由日本一家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白石嘉壽子在上世紀60年代后期的日本和美國暴得大名。她的早期作品擁有一種西班牙畫家霍安. 米羅的品質,但是后來她就轉向了所謂的“爵士詩”,內容以情色為主。她寫與同性戀者的雜居生活,寫同黑人的性關系,寫生殖器,寫“狗娘養的”等等,據說是暴露了戰后日本社會的暴力和丑陋。當她成為日本的所謂“地下詩人”的時候,她獲得了美國人的叫好。一個叫唐納德. 基尼(Donald Keene)的美國人稱她為“日本的艾倫. 金斯伯格”(金斯伯格因此也就加入到翻譯白石嘉壽子的諸譯者當中)。雷克思羅斯在為《神圣淫者的季節》一書所寫的序言中稱:“白石嘉壽子是美國的垮掉派、英國的‘憤怒的青年’、蘇聯的沃茲涅先斯基這一代人中最后,也是最年輕,也是最優秀的人物之一。”要是中國的“下半身”們也被雷克思羅斯這樣表揚一番,我會覺得我這個“非下半身”臉上也有光呢。白石嘉壽子是百分百的“下半身”,但比“下半身”多一點迷惘和傷感。在一首名為《街道》(Street)的詩中,白石嘉壽子寫到她和某人在一個雨夜,在一個悲傷小鎮上的一夜情:“最后我們開始走路,/我們濕濕地,緊緊地靠在一起,/我們不知道我們會有怎樣的未來。//盡管我不記得任何事情 /關于一間溫暖的旅館,關于我們分享溫暖的身體,/關于我們的許多話語、許多愛的動作。”這樣的詩歌還真讓人有些感動呢。
但總的說來,白石嘉壽子的詩,據另一位日本女詩人說,已是一個過去時代的成果,其寫作意義上的有效性,似乎不及年齡與之相仿的谷川俊太郎的作品。據說谷川俊太郎也是反知識分子的,但他的詩歌語言極其符合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老百姓所理解的詩意,其詩意的濃郁不亞于美國的馬克. 斯特蘭德。此外,谷川俊太郎還具備白石嘉壽子所不具備的形式感。日本當代文學有一個特點,西方有什么日本就有什么:西方有荒誕派,日本就也有荒誕派;西方有存在主義,日本就也有存在主義;西方有垮掉派,日本就也有垮掉派。(這樣好嗎?這樣有意義嗎?容討論。)有趣的是難道中國不是也有同樣的事情發生嗎?但日本的荒誕派、存在主義、跨掉派等是得到了西方承認與加持的。日本當代詩歌進入國際詩歌視野的時間其實并沒有比中國當代詩歌早多少。1970年4月美國國會圖書館舉辦過一次國際詩歌節,谷川俊太郎代表日本詩人亮相。那大概是美國詩人們注意到日本當代詩歌的開始。1971年8月英國倫敦《泰晤士報文學副刊》出版過一期日本專刊。在談到日本當代詩歌時,該刊說:“很明顯,要列舉出最好的(日本)青年詩人依然是困難的。但日本當代觀點傾向于相信安西均、白石嘉壽子和谷川俊太郎是最好的。”——英國人也有拿不準的時候。于是到1972年英國就出版了《當代日本三詩人詩選》,一本只有80頁的小冊子。這是日本當代詩歌第一次被介紹給英語讀者。盡管白石嘉壽子的詩沒有那么好,但她的詩,特別是谷川俊太郎的詩,在英文當中的呈現還是要比呈現在奚密《中文現代詩選》中的中國人的詩歌有效得多。
中國當代詩歌在語言上的問題經過英譯文的提醒,大致呈現為:沒有修辭,沒有寫作觀念,沒有獨在的具體性,不直接,總是擺好了架勢再進入詩歌,慢條斯理,彎彎繞,用大詞,沒有令人驚訝的意象和句式,沒有新鮮感,有新鮮感的人沒有厚度,有傷感的人過分傷感等等。當然,在奚密《中文現代詩選》中,有幾位詩人的作品還是過硬的。例如,我以前沒想到痖弦的《鹽》在英文中的效果真的不錯。
讀著翻譯成英文的《中文現代詩選》,以及東歐詩和日本詩,我又隨手拽過來一本美國Taoran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詩歌小冊子,題目是《我的村莊》(My Village),作者是一位臺灣鄉土詩人,英譯者名約翰. 巴爾科姆(John Balcom)。翻開第一頁,我讀到這樣的詩句:“Long , long ago / The people of my village / began to look up with hope / The sky on my village / is so indifferent / Indifferent blue or gray”.——對不起,一串英文,讓不懂英文的人一頭霧水,也許甚至會覺得望而生畏。可這段英文說的是什么呢,還不點標點符號?這段英文的意思是:很久很久以前,我村莊里的人們開始懷著希望抬頭仰望;覆蓋村莊的天空冷漠得要命 ,是冷漠的藍色或灰色。——無論作者懷著怎樣的鄉土情愁, 這樣寫詩都是不行的。真的是既無語言也無觀念。連一點點聰明也沒有,連一點點狡猾也沒有。這樣的詩還要翻譯成英文,還要出版,太過分了。這樣的詩不僅丟作者的臉,也丟中文當代詩歌的臉。對于那些急著要把自己的詩翻成英文或其他語言的詩人們,我要提醒一句:一定要在你自己能夠大致確定你不會丟你自己的臉,并且也不會丟用中文寫作的大家的臉之后,再進行翻譯。
查看9794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