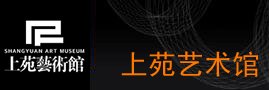六月十五日午后與文波梅丹理登首象山
三個人,膚色漸深地
配合一年比一年茂密的灌木
爬到半山腰,
脫了T恤,
迎風鼓起肌肉和巖石。
除了不健美地隔著草木
悠閑地
尿尿外,
實在是沒有什么再值得
炫耀的年輕的器官了。
其實,我也爬到了山頂,
還向南邊望了望,
今天的霧濃得有些矯情,
從一堆堆舊書里分泌出酸腐氣后,
有意留下的這個清晰山頭,
還長滿了帶刺的酸棗
和不屈的塔柏——
天生的,手載的?
知識越多越反動,
連常說的虛無也被遮掩得
富有歷史感。
一只灰雀斜插進去,
像個第四者,
一定先于我們精通現實的騰空術。
但我更看重山背后的山,
高與髖齊,
只需我足夠輕松的一跨步。
可我沒來錯地方,
那么多野花把蠟燭點進山陰的褶皺里,
等我去吹熄。
那么多紫的、白的六月雪,
一晃就在路邊開了二十年。
那時我沒想過會來到附近的城市和鄉村,
也不是這花下的一片葉。
即使再過二十年,
這里也還不是你們的俄亥俄和劍門關。
可山腳去了又來的火車,
興奮得像頭查拉斯圖拉的老白鯨。
——滿山都是燃料,都是波紋。
2009年6月18日,沙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