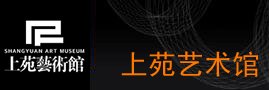|
程小蓓的記實性小說《無奈》之一、“你被捕了。”
[2009-8-11 8:50:35]
gHd&<;Ulg;cjHkGzu#zX;AawAqcEUDBh?qh2WhAD" target=_blank>程小蓓的記實性小說《無奈》之一、“你被捕了。”
1
兩個穿便服的陌生中年男人,突然在兒子奶奶家的晚餐桌上降臨。
由于沒有住房,一家人通常是今天這兒,明天那兒地過著動蕩不安的日子。我看到他們的第一眼,一種不祥的感覺就降臨了,如他們降臨在晚餐桌上。
他們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張有照片的塑料卡,在我們眼前晃了一下。那速度肯定讓你看不明白。同時說:
“我們是西域城安警局的,有點事,請你走一趟。”
我絕對不愿在兒子及家人面前讓他們聽到有關“犯罪”之類的言詞。于是,我放下手中的碗筷,立刻起身,拿上衣服就要走。這時,我兒子的感覺也是那么地敏銳,他預感到我今天晚上回不去了,問:
“我今天晚上在哪兒睡覺?”
一種居無定所、無依無靠的感覺,已深入他的骨髓。
我沒有回答兒子的問話,心中只想著,從容一點,自然一點,別增加家人心里的不安。有奶奶在,兒子會有地方住的。
出了門,我想,一定要搞清他們的身份。就要來那兩位陌生人剛才那么一晃的塑料卡來,認真看了。
這兩位陌生男人都是四十多歲的年齡,一個胖胖的姓羅,是干警;另一個有著一副精明能干長像的姓傅,上面標明是經案隊長,二級警司。前者和和氣氣,后者認真而嚴肅,像個負責的。如果就前者那種樣子,我要是逃跑,他肯定追不上我。只是我根本沒想到要跑,在我的一生中,我沒覺著自己犯了什么法?跑什么呢?跑命!?
他們把我帶到一輛“面包車”上,一左一右地把我夾在中間。汽車“嗚——”地一聲,飛快地開了起來。
從奶奶家出來到汽車上,他們始終一句話不說。這種沉默讓我特別難受,就問:
“出什么事了?”
他們看了看我,又相互對視了一下,然后各自回頭看著自己那邊窗外的街景。但在傅隊長眼里有一種隱隱的不安和困惑。對眼前這個女人將要遭遇的是什么?他了如指掌。他似有一種沖動,想用手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幾句,可終是忍住了。
大都市的夜生活正拉開序幕。一對一對的情侶,沿街而行;夜總會、餐館、咖啡館……的霓虹燈閃爍著;人聲、汽車發動機聲、歌廳的音樂聲嘈雜在一起;妓女們花枝招展地張開她們陰府般的嘴,笑迎八方來客。
我實在無法這樣不明不白地被他們傻押著,在汽車上看無聊的街景。就不耐煩地問:
“你們要把我帶到哪兒去?要干什么?”
傅隊長看到我有些激動,怕出意外,就用誠懇些的聲音對我說:
“到辦公室再說吧。前面不遠就到了。”
羅干警這時也帶著隆重外地口音說:
“剛才你不是又看了一次我們的證件嗎?我們也是在執行公務。肯定是有事要找你的啦,到了就有人會告訴你的啦。”
這樣穿街走巷地總算是進了一個安靜的大院子。車停在一個三層樓房的門廳前面。羅干警先下去站在門邊,伸手捏住我的衣袖,緊跟著我下來的傅隊長也伸手挽住我的胳膊。我立刻意識到,我是被強制監管了。可為什么?傅隊長不等我問,就說:
“你被捕了。希望你配合,不然我們就只有給你戴上手銬。”
我眼前立刻出現電影上那種:安警人破門而入,將反抗的罪犯按倒在地,一只只腳踏在身上,手銬“咔咔”作響,槍和警捧“閃閃”在眼前……。
我一下子有種感激的沖動出來,真感謝他們沒有當著我兒子及家人說這些話和做這些動作。于是,我非常順從地跟他們走進了那個門廳。
到了辦公室,他們安排我坐下。由羅干警看守我,傅隊長為避開這讓他無耐的局面出去了。這時羅干警給我倒來一杯茶,好像我是他的客人而不是他的囚。這讓我的感覺輕松了很多。我還是耐不住地問他:
“為什么事逮捕我?”
“是平莊地區來人委托我們逮捕你的。你們公司和那個地方的企業有業務往來吧?”
“是。”
“你們在合同的執行和簽署上有問題。你在這里只是暫時的,等他們來人帶你走。”
我是要被引渡出西域城?西域城安警不能審核外國安警的逮捕條件嗎?他們不能保護本國公民的合法權益嗎?也就是說,外國安警可以隨意立案而后到外國抓人,本國安警不作審查嗎?
我還想問下去的,這時來了幾個穿制服的安警。他們忙亂起來。又有幾個看來也是和我一樣的“犯罪嫌疑人”進來了。
沒人再有空閑回答我的問題。還是自己去好好想想吧。
2
揚子的腦子里開始一遍遍地過那些“合同”,想搞清楚毛病出在哪兒?
甲方(上個世紀的平莊地區產業公司、控告方)負債累累,瀕臨倒閉。其工廠多年停產,產品無人問津。
乙方(被告方即揚子所代表的經銷公司)有能力組織、培訓業務員隊伍,包裝、策劃產品并推銷出去。
丙方(客戶又是上帝)接受產品但不會立即付款,通常為三到六個月后滾動結算。
所以業務開展越大,范圍鋪得越廣,市場所壓貨款就越多。這是上個世紀具有國陸地特色的市場問題,也是唯一能救活這個企業所必須承擔的風險投資問題。何況這是一種良性的三角循環債務,不是死債。
一年之后甲方產品及甲方名不見經傳的品牌在國的陸地上廣泛地宣揚開來。各地都已良性地將部分貨款循環回到甲方。
正在這時,作為國產業公司的甲方時遇改革的浪潮,更換領導。
新上任的領導看到業務遍及大陸各國,誤認為老領導“油水”一定很足,便“招”乙方前往進見。誰知乙方“不懂事”,認為自己是甲方的“救星”及平等地位的客戶。甲方新領導無權將乙方招來招去,更沒有必要對他暗示的“油水”問題給予滿足。
于是乎這良性循環的三角債務便成了刑事案件;
于是乎乙方便遭殃了;
于是乎便有了這本《囚人說案》里的眾生像。
3
看守——匈沙先生,一只帶鐵釘的皮鞋飛了過來,芝子一聲尖叫,抱頭鼠竄。
滿號子的女囚,屏住了呼吸,盡量縮小著自己。
兩個老年的婦人,跪在號子中間。兩支手像蝴蝶一樣張開,臉上安詳的神態,如進了另一個天國,什么也驚擾不了她們似的。而她們卻是那只鞋要踢的目標。
于是,兩雙超重的手銬,將那像蝴蝶一樣飛起的手,銬了攏來。折了你的翅膀,看你還怎么飛翔?你每掙扎一次,手銬就緊一環,直到你的血脈沒了流通。
倆老婦人,這會兒睜開了眼睛。她們從容環顧了一下站在牢門口和號子里的看守,然后,相互對視,像是對了一個隱密的暗號,同時低下她們的頭,如睡了過去。
到了這牢里,你的每一睡夢都要加倍地小心。夜里叫出的每一個詞都有人給你記錄下來,成為你的呈堂供證。白天你臉上的表情都要事先做好充分的內心腹稿,不可以未經容許而笑,特別不可以哭泣。不然,以此為由,會招來耳光和辱罵。
獄霸牢頭們經常秘密策劃殘人的游戲。她們的心已被關出了繭子,殘人是她們磨繭子的方法之一。她們的生活準則是及時行樂。每天清晨醒來,不知道這是否就是最后的一個早晨,今天,是否就是生命的終點。
她們只活在今天 ,只活在當下。
看守們“咣當”,將鐵牢門關上走了。
一張潮濕而骯臟的棉被,像一張厚重的魚網,蓋了下來。將倆老婦人罩在里面。于是,有近十個囚坐上去,這個上去滑下來,另一個又上去踩。兩個老婦人成了游樂園里的梭梭板。兩小時后,她們玩累了。就用腳一踢,說:
“芝子、小蔓,把這兒收拾干凈!”
她們發這命令時,就如這里有一堆胺臟的垃圾,需要兩名清潔工。
兩個年輕的女囚,芝子和小蔓,從被子底下將兩個奄奄一息的老囚扶起來,讓她們平躺在地鋪的角落里。
小蔓將水一滴一滴地喂進這兩張嘴唇發紫的口里。一副見慣不驚、處事從容的模樣,與她的年齡和純情的眼神極不相稱。
芝子卻神經質地將兩支顫抖不已的手放進嘴里咬著,拼命想讓自己平靜下來。
所有囚的命,每時每刻都在誠惶誠恐的懸崖邊上,與死神交談著進出地獄的條件。我們只能知道昨天和前天所發生的事情,并認定它。我們無法知道明天和后天將要發生什么,去如何安排和改變它。沒有假設,不可以重新再來。面對這一切,我們無能為力。
囚們正小心翼翼地經歷著現在。
正如勞工李告訴我的:他在京都城打工,每時每刻都提心吊膽地躲避著“強者”和執政者。
可是,不管他如何地用心躲避,這一天都會到來。
他領到第一個月的薪金時,想,如果有一輛自行車,就不用這樣心驚膽顫過日子。可以騎著它迅速地從工地趕回住地,可以在傍晚時去看看自己從小就仰慕的城樓……。這么想著他就到了商場,將自己薪金的三分之一用來買了一輛紅色的自行車。
紅色吉祥。
他懷著說不出的愉快心情,吹著口哨穿梭于大街小巷中。在他從一個胡同口拐到大街上時,迎頭撞上了一個人,“哐當”一聲,人仰馬翻。
“把三證拿出來!”
還沒等他醒過神來,一個安警站在了他的面前。他感到大事不好,就結結巴巴地回問:“什么三證?”
“工作證、身份證、暫住證。”
“哦!我只有身份證和暫住證。”
說著李趕緊從地上爬起來,掏出上衣口袋里的證件遞上去。安警接過去看也沒看,將暫住證撕了,身份證還回了他。二話沒說,拽上他就往一輛汽車里走。
李喊道:“怎么了?怎么了?我的車,我的車,我今天才買的新車怎么辦?”
李的聲音漸漸地變成了哭泣聲。車里面已經有十多個和他一樣勞工著裝的人,大家都愁苦地看著他哭。沒一個人能幫得了他。
車在走走停停中又抓上來一些勞工,到裝不下時,安警們關門上鎖,將他們拉到安警所。
在安警所里他們被告知,每人一千元錢交了就可以走人,不然就會被送上火車譴送回老家。李摸了摸口袋里今天剛領的薪金,約還有四百多元,如果不買那輛車的話,也不過只有六百多元,差得遠呢。再一想,要交那么多錢還不如回去了再來,也只要一百多元的車費。只可惜了那輛新車。想到這兒他的眼淚又要出來了。
在那些勞工中有幾個真將錢交了走人的,引得勞工們一片“咂咂”的贊嘆聲。
“還有要交錢的嗎?沒有了就上火車站。”
勞工們吵吵嚷嚷起來,有說能不能少一點,身上沒那么多的;有說能不能等一等,讓家人給送錢來;有人請求打一個電話,好讓親人知道自己的去向,不然會著急死的……。
找人送錢的都讓打電話了,其它的要求便都不與答復。送錢來了的,就又走掉一部分。到后來少交一點的如900、800的便也走了。
天黑了,有500元的交了也可以走。李想,到了二百元時我就交錢。他咬著牙堅持著。可心里又不停地敲著鼓,要是下不來怎么辦?聽說會被送到一個采石場去干一個月苦力后,再被裝進悶灌箱子車(如納粹裝運猶太人那樣)送回家。回家后閑著沒事干,不得繼續受窮?并被鄉人看不起。要再回來,工頭還會要他嗎?想著想著,他就不由自主地將身上的那四百多元錢掏出來,對安警說:
“先生,你看,我今天剛發的薪金就只有這么多,能不能放了我。我在四環路上建橋,工頭是我們一個村子里的,他會找我。不信,你們可以打電話問。只是我不知道他的號碼。”
最后他真被放了。從三環路走回了四環路他的工棚。一路上都在罵自己為什么不堅持到二百元時才交錢。
人在劣勢下,總是沒有把握自己命運的力量和信心。
這是弱者與強者的較量,失敗是注定的。這里沒有什么希區柯克式的電影懸念。
4
我分別兩次為上面所說的同一件事情入獄。從西域城監獄展轉到平莊地區監獄,共被關押約一百四十多天。
不管有沒有罪,只要有人告你,且告你的人有一定的經濟地位又打著為國辦事的口號,安警局的某些人就會不管三七二十一下令先將你抓起來再說。
最后監視廳的撤案報告說:……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經本院審查查明:
……“乙方(代表:揚子)”于丙子年間四月廿二日與“甲方”簽訂為期四年的銷售合同,共計發貨物:11670件。在合同履行期間,揚子于丙子年三月以前支付貨款3283016元,后又派人代交821513元。案發后,“甲方”自收各客戶單位貨款共計:1418332元。經查證,尚在外末回籠和已被凍結的貨款共計:200559元。……
上述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足以認定:……不構成犯罪。……依照<<刑法》、《刑事訴訟法>>第……。
鋼墻鐵壁的牢獄里,裝著豆腐般脆弱的生命。
一臉茫然的小姑娘,蹲著。用兩只手緊抱自己的雙膝,下巴頦擱在膝頭上。不知所措地搖晃著她瘦小的身子。許久,有淚水從她的眼眶里流了出來。吧嗒、吧嗒,淚水滴在木板地臺上。緊跟著,更多的淚水涌了出來。漸漸有泣聲出來。
一個身材高大的囚,牢頭巴蘿,如一座山般立在小姑娘的面前。一腳踢上去,小姑娘如一個大足球,滾動起來。另一邊的囚又踢過去。號子里就開始了一場足球賽。
“好球!”
“射門!”
“這是個壞了規矩的囚(球)。”
……
直到小姑娘兩只手抱不住自己,伸展開來,不再是一個圓的“球”時,足球賽方才停止。
“芝子、小蔓,將這球場打掃了!”
芝子一個人將這“足球”抱到角落里,用松節油涂滿她紫烏的全身。她們倆是號子里的外地人,家人都不知道她們在哪兒。
5
從平莊地區前往西域城監獄提拿我的三個安警中,一個級別、年齡與傅隊長一樣的賈隊長,在傅隊長面前一付卑屈的模樣。矮胖的身材,上身穿著一件里襯洗縮了水的深藍色西服,七鼓八翹的。下身一條燙有很死的刀一樣的褲子,一雙顯然是新買的假“耐克”運動鞋,白得與上面所穿的深色衣服形成巨大的反差。有點像陳佩斯最愛扮演的滑稽角色。見著西域城經案處的女秘書,口水長流著涎笑。
“午餐我們請客,喝酒,犒勞各位。小秘書你一定要到噢。”
傅隊長幫女秘書解圍,接話過去說:
“唉,賈,案子你可要弄明確了喲。不然你們到時候會吃‘反訴’的。”
說著將眼睛瞟了一眼在另一間屋里銬著的我,用下巴對賈隊長示意說:
“那是一個不好惹的主。文化人,肚子里有東西。不是你那鄉下的愚民,由著你們關。”
“嗨!放心。什么人到了我們那兒都乖乖的。”
說完眼睛又往女秘書的身上瞟。
最后喝得醉熏熏的,嘴里七七八八地說些不連貫的語言。在我的手銬上搭一件衣服,如牽一條狗似的將我牽上了飛往平莊地區的飛機。
這樣我在一個二十平米的囚室里與另外二十多個,甚至達三十多個囚一起度過了三千多個小時。和小蔓、芝子、巴蘿、小調、阿紅、雙雙、胡靜圓------及一些不知道罪名的囚,一起度過了三千多個小時。
里面空氣污晦得令人窒息。醒著的每時每刻你都要提心吊膽地耳聽八方、眼觀六路,防止著有人襲擊過來。
有些人在這里面關上兩、三年。像一頭困獸,長久地關在籠子里,來回只有二、三步地踱來踱去。
用一分鐘、一秒鐘的速度進行著,一直到幾萬個小時踱過去。
中間不會有超過百分之一的時間,讓你到“寬敞”的天井里去,伸展一下你的胳膊腿。
度日如年!
但我度過來了。人,之所以能從遠古留存至今,肯定靠了人的忍耐力、適應力及強大的求生欲。
查看10014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