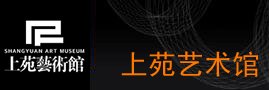|
奚密-論現代漢詩的“現代性”
[2011-8-21 7:26:22]
“《可蘭經》里沒有駱駝”——論現代漢詩的“現代性”
奚密
1951年,當博爾赫斯的作品被他的同胞指責缺乏地方色彩時,他寫了一篇名為《阿根廷作家與傳統》的文章作為回應。文中提及穆罕默德時,他說:“在《可蘭經》這部偉大的阿拉伯經典中,并沒有出現過駱駝”,因為“[穆罕默德] 知道他即使不提駱駝也依然是阿拉伯人。”他繼續道:“真正本土的東西可以——也經常是——不需要地方色彩的”。
對研究非西方的文學學者而言,半個多世紀以前博爾赫斯文章的議題再熟悉不過了。在中國文學領域里,現代漢詩史上總會出現關于文化認同或“中國性”的爭論。在小說、繪畫、電影等其他的藝術中,也存在著類似的本土化與國際化、民族化與現代化之間的張力。這個現象的關鍵在于藝術作為再現(representation)的概念。當文學主要——甚至僅僅——被理解為起源民族或文化的索引或地圖時,讀者以文學能否再現民族文化作為衡量它的標準也就順理成章了。也因此,就有了對文學的“地方色彩”的期待,有了對其“真實性”(authenticity)的要求。
類似的情況也反映在當前美國對“少數族群作家”(ethnic writers)的興趣和市場需求。大部分美國的非白人作家是根據其族群身份來歸類的,例如亞裔作家、非洲裔作家、原住民作家等。盡管有的作家認為這些標簽是狹隘的,但是族群已成為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分類原則,廣泛地應用于出版業、大學課程、學術會議,甚至文學獎、藝術節等等。每個族群都成了一個“商機”或是文學市場的一個賣點。
我用“市場”這個字眼,它廣義上也包括了學術界。強調文學之再現功能的觀念呼應了當代美國學術界文學研究的一種流行傾向,它重地方性而輕全球性,重族群性而輕普世性,重差異性而輕共同性。反諷的是,當文學被認為是一個文化或族群的再現時,它常會因為再現得“太多”或“太少”而受到批評。如果一部作品沒有充分反映它理應表現的文化或族群時,它失之“太少”;如果一部作品過于強調一個文化或族群的某個面向而忽視了其他面向,它失之“太多”。其中的悖論是:盡管這兩種態度表面上是相反的,其實它們往往導致同樣的結論,那就是作家藝術家之所以這樣做是在“迎合”外國讀者和觀眾。李安、張藝謀等導演,哈金、高行健等小說家,都曾被批評為滿足西方人的窺視癖和對異國風味的追求,或者迎合西方讀者——尤其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們——的品味。
這類批評在李銳2004年7月24日發表于《中國日報》的一篇文章中也看得到。李銳把批評的矛頭指向八十年代“迎合西方文學權威”的先鋒小說家。“他們的作品沒有一部是真正原創性的,是表達了中國人民的真精神的。但西方學界喜歡它們。”他呼吁同輩作家拒絕把西方價值作為文學創作的唯一準繩,并去“反映中國人民的精神世界和中國獨特的文化”。
李銳對中國性的擁抱包含了兩重矛盾。第一是反普遍主義和普遍主義之間的矛盾。雖然他反對把西方品味作為評價中國文學的普世標準,但是他卻把“中國文化”、“中國人民”、“中國精神”當作普世標準。當他呼吁同代作家去追求“中國特色”時,我想問的是:中國特色究竟是什么?是誰來決定什么是中國特色,什么不是呢?再者,在無數的“中國人民的生活和經驗”中,作家到底應該刻畫哪些,從而去表現“我們文化的靈魂”呢?
再回到博爾赫斯那篇文章,我們可以從中發現一個李銳似乎沒有意識到的反諷。那就是,主張“文學…必須具有民族特色的觀念是一個相對晚近…而且武斷的觀念”,它也是一種“近代歐洲的狂熱崇拜(cult)”。 我曾把這種先入為主地認為中國性應該是什么,由誰來表現,以及如何表現的心態稱為“真實性的神話”或者“純粹性的崇拜”。
李銳論述的另一重矛盾是,盡管他反對西方獨霸著世界文學仲裁者的地位,但是他卻用同樣的思維模式來證明他的觀點,那就是,如果中國作品不被西方認真看待的話,就會有嚴重的后果。文中他說:“在西方文學權威的支配下,中國文學在國際舞臺上被輕視,這意味著中國人民開始失去自尊和藝術的獨特性。” 如果李銳所言屬實,中國作家可能永遠也無法擺脫自我表現的困境,因為如果他們贏得西方的認可,他們會被認為是本土文化的“叛徒”;如果他們沒有得到西方的歡迎,他們又會失去自尊!
在我看來,任何以中國性來定義評價中國文學,并以此來和別國文學區分的做法都是有問題的。實際上,把中國性具體化是在顛倒因果。讀者對中國文學的理解應該來自他們對中國作品的閱讀經驗的累積,而不是先形成某種預設的“中國”,然后再到作品中去印證。
頗為諷刺的是,李銳對“西方文學權威”的批評和北美學界的觀點頗有雷同之處。兩者之間的共同點包括:批判西方霸權,肯定非西方的反抗立場,強調個別文化的特殊性,以及提倡各族群、民族、性別都應得到平等的再現和認同。拉丁美洲也出現過類似的現象。尼爾•拉森(Neil Larsen)曾用“反向的歐洲中心主義”(inverted Eurocentrism)一詞來形容它,并認為抗爭性的周邊文化其實和占據統治地位的歐洲中心文化是相互呼應的。
周蕾在《新教徒族群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n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書里,認為模擬(mimeticism)是“后殖民世界里跨民族表現的核心問題”。 她進一步把“模擬”分為三個層面,最進化也最復雜的第三個層面是:“白人和他們的文化不再是被摹仿、被復制的原版,原版反而是少數族群的形象或刻板印象,比如亞洲性、非洲性、阿拉伯性等等”。 在《我抵抗,所以我存在:全球資本時代的族群》一章里,周蕾認為民族再現與自我再現“緊密結合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意識形態操作中,[前者] 充滿了后者的吁求、機會和獎勵的機制”。
當我質疑文學作為文化和族群再現的觀念時,這并不表示我否定文學是我們了解文化、社會、時代的一扇窗口。實際上,在本科生課程里,我們也往往如此看待文學。但是,在我們將中國文學作為了解中國的工具向學生傳授時,我們也應教他們如何去欣賞中國文學的藝術性。當某些學生選擇深入研究中國文學時(例如專攻某個作家、文體、主題),與其說他們想要更全面地了解中國——如果僅為了這個目的,其他學科研究也可以達到——不如說他們是想不斷地體驗文學作品所帶給他們的愉悅和力量。畢竟,文學是一種特殊的話語,和其他形式的話語有根本的差別。把文學和其他話語等同起來不僅是對文學的簡化,也把文學研究的價值和合法性讓位給其他學科。
對中國性的過分關注在現代漢詩的研究中尤其普遍。 但凡與外國(尤其是西方)影響有關的東西,經常引致輕蔑和排斥。對現代漢詩的文化認同(或者文化認同的缺失)的關注,也是二十世紀多場論戰的焦點。在二十世紀的前三十年,新詩的批評者指責它是西方詩歌的模仿。不少國內外學者仍然認為新詩的出現是美國意象派影響的結果。在臺灣七十年代初的“現代詩論戰”中,現代主義由于受到了包括歐美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和精神分析在內的影響,被批評為文化殖民、自戀、頹廢。 中國大陸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地下詩歌,背離了政治抒情詩歌傳統,引領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詩歌復興,也曾讓文學權威們倍感困惑,甚至憤怒。對另類美學模式的陌生感使得地下詩歌看起來很“西化”,也給它帶來“朦朧詩”的負面名稱。九十年代初,詩人兼學者鄭敏(1920- )對她認為語言過于西化的現代詩全盤否定,并呼吁詩人重新回歸中國傳統。 1999~2000兩年間,大陸“民間詩人”和“知識分子詩人”之間的論戰也圍繞著語言的問題,將日常生活的大眾語言和過度西化的精英語言對立起來。
為什么對現代漢詩缺乏中國性的焦慮會在文學史中反復出現呢?為什么用中文書寫的現代詩無法讓批評者接受其中國認同呢?要回答這類問題,我們必須了解現代詩的歷史地位和新取向。簡言之,就是現代漢詩的“現代性”。
現代漢詩的現代性之核心是一個特定的歷史語境所造成的悖論。在提倡以現代白話作為詩歌媒介的過程中,新詩是晚清以來中國推動的現代國族建構工程的一環。這項工程旨在提高民眾的文化素養,通過推行白話來培養新國民。隨著白話在二十年代早期被正式訂定為國語,并成功地進入教育系統,新詩也在很短的時間內獲得了合法性。盡管傳統形式的古典詩詞繼續有人在寫,但至少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副刊的選詩,詩選的編輯,獎項的頒發,仍以新詩為主。
雖然現代漢詩在體制層面很早就獲得了合法性,但是它在文化界的正當性和公認價值從發軔之初就不斷地遭到質疑。別處我曾討論過20世紀中國詩歌的邊緣化問題。 當新詩起而挑戰古典詩歌時,那無異于侏儒挑戰巨人。從孔子開始到儒家的體制化,詩在中國一直享有特殊的地位。它位居文學藝術之首,是最優雅的藝術形式,最崇高的文體。今天中國人依然為他們輝煌的古典詩歌遺產深感驕傲,常常自稱是一個“詩的民族”。更重要的是,詩的意義不僅體現在文化領域里,而且它也在傳統社會里扮演著道德、教育、政治等多重角色。盡管從數量上來說,古典詩歌的作者和讀者主要是士人階級,但是它一直在文化社會里居于中心地位。
到了二十世紀,詩的地位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其主因包括:科舉制度的廢除,西式教育體系的采用,現代知識系統的結構,以及現代傳媒和出版業的興起等等。詩不再是過去那種優雅崇高的書寫形式,也不再具備過去那些公共性和體制性的功能。簡言之,詩喪失了幾千年來享有的特殊地位和擔任的多重角色。和古典詩相比,新詩被邊緣化了。
現代漢詩不僅無法恢復詩歌過去的地位和角色,它還面臨著另一個難題,一個在別的文學傳統里未必存在的難題。那就是,作為一種新的書寫形式,現代漢詩既是挑戰性的,也備受挑戰。因為,不論是內容還是形式,語言還是美學取向,它都不是古典詩。這已經構成了“現代性”與“中國性”之間的潛在矛盾。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古典詩具備了完美而穩定的美學典范,它體現在語言(正式或非正式、典雅或民間、古風或口語),意象和修辭(典故、隱喻、象征等),形式(詩、詞、曲等),以及內容方面(場合性、公共性、私人性等)。盡管古典詩決非沒有個人變化和創新的空間,但是變化和創新發生在一個不斷被效仿的歷代杰出詩人所構成的傳統框架里。換言之,古典詩所建立的典范具備超穩定性,過去千余年來基本不變。當新詩去挑戰這個典范時,它無異在對傳承的詩歌觀念進行根本的挑戰。無怪乎對于很多中國讀者而言,現代漢詩看起來不像詩,它缺乏“詩意”。其原因是,現代漢詩作為一種新的美學模式,不能符合他們對“詩”的期待,而他們的期待幾乎完全奠基于和源自古典詩。
更重要的是,古典詩不僅在傳統社會文化中扮演著多重角色并享有優越的地位,而且經過長期的發展已經深深積淀在中國的語言里,不論是口語還是書面語。對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而言,在其言談和書寫中幾乎不可能不用古典詩積淀在中文里的數不盡的成語、意象、典故、名句等等。因此,古典詩和中國的文化認同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從講座中和中國聽眾的交流經驗中我發現,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推崇古典詩,也越抗拒現代詩。二十世紀初美國詩人龐德(Ezra Pound 1885-1972)和其他意象派詩人對中國古典詩的推崇,往往使中國人更加肯定其永恒的美和價值,并且是中國對世界的獨特貢獻。
與此相反的是,現代漢詩看起來似乎“不純”,它不像“中國詩”。誕生于1917年文學革命的新詩,決絕地自別于古典詩,以致在很多中國讀者眼里它依然顯得是“外來的”。從歷史的角度觀察,現代漢詩確實和許多外國場景有關,而現代詩人也自由多元地汲取外來的文學資源。文學革命的領袖胡適(1891-1962)的新詩理念就是他在1910-1917年留美期間(尤其是1916~1917年)所形成的。在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求學期間他曾經廣泛地閱讀歐美詩歌,例如莎士比亞、譚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勃郎寧(Robert Browning 1812-1889)、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坎貝爾(Thomas Campbell 1777-1844),提斯黛爾(Sara Teasdale 1884-1933)等人的作品。胡適的例子并不鮮見。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很多詩人都曾留學國外,他們不少作品也寫于國外。諸如留學日本的周作人(1885-1967)、郭沫若(1892-1978),美國的聞一多(1899-1946)、冰心(1900-1999)、穆旦(1918-1977)、鄭敏,英國的徐志摩(1896-1931),德國的宗白華(1897-1986)、馮至(1905-1993),法國的王獨清(1898-1940)、李金發(1900-1976)、梁宗岱(1903-1983)、戴望舒(1905-1950)、羅大岡(1909-1998)、艾青(1910-1996)等,多不勝數。這是現代漢詩史上的一個普遍現象(1949-1979年間的中國大陸屬于例外)。直到今天,不少詩人留學或長期居住海外,仍繼續用中文寫作和發表。
與此相關的是,很多現代詩人也翻譯外國詩歌。這是現代漢詩有別于古典詩的一個特色。無論教育背景如何,大部分現代詩人都熱切地閱讀外國詩歌,不論是透過原文還是中譯本。 對世界文學的廣泛接觸給他們的作品提供了很多非本土的詞語、意象、象征、神話、典故等,這也使得它們明顯地有別于古典詩歌。在此背景下,本土與外國、原文與譯文的糅合是無法避免的,也具備深遠的意義。我們可以說,現代漢詩從一開始就是中國和非中國元素的結合,它是一個“混血兒”。
文化混血本身并不值得擔憂。畢竟,物質文化的西化不僅被中國人欣然接受,而且被中國人熱切地追求。舉凡日常生活里,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是如此。甚至在非物質文化的范疇里,現代小說和話劇所引起的有關的中國性的爭議也明顯比現代詩要少得多。由于古典詩不但和“中國”密不可分,而且具有標桿性的意義,因此很多讀者會認為現代詩是對中國認同的一種挑戰,一種偏離。這點構成現代漢詩的另一個歷史悖論:它既是“合法的”——因為它是現代中國,詩這個文類的代表——也是“非法的”——因為它是古典詩不稱職的繼承者,或者說得重一點,它是古典詩的“不孝子”。和悠久輝煌的古典經典相比,作為混血兒的現代漢詩顯得那么黯淡無光。
一旦我們明白,古典詩是作為文化認同的象征,民族自豪的載體,而被狂熱地崇拜,就會發現“中國性”這個問題顯得錯位,甚至沒有意義,而對中國性的聚焦就成了全面理解現代漢詩的一道障礙。畢竟,沒有人會去質疑美國現代詩是否具備“美國性”,或者法國現代詩是否表現了“法國性”。更甚者,我們不會因為美國詩法國詩受到其他的文學傳統的影響就去質疑其文化認同。因此,與其去問:“現代漢詩的中國性在哪里?”我們還不如問一個更有意義和建設性的問題:“現代漢詩的現代性在哪里?”
前面的討論凸顯了現代漢詩之現代性的兩個重要層面:第一,它的世界性和糅合性;第二,它的反傳統和實驗精神。第一個層面暗示自我革新的新模式的建立。傳統詩人往往參照模仿前代的某個大師、詩派或風格。雖然每隔一段時間總有詩人起而反抗這類新古典主義或復古主義,并刻意強調個性和性靈,但是從宋代到晚清的主流取向一直是從本土傳統中尋找革新的資源。現代漢詩的第二個特點同時體現在內容和形式、美學取向和藝術探索上。我曾經討論過,現代漢詩對詩的本體論思考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問題:什么是詩?詩為誰而做?為什么用詩寫?
如果我們只能用一個詞來形容現代漢詩,我會選擇“革命”。“革命”這個詞第一次和詩歌聯結在一起是十九世紀末梁啟超(1873-1929)倡導的“詩界革命”,包括引進“新語句”,創造“新意境”,以及復興“舊風格”。前面兩個目標給詩歌帶來了例如“議會”(巴力門)和“種姓制度”(喀私德)這類新詞語,地心引力和電力這類新概念。這些創新反映了新知識的引介和文化的轉型,代表了中國(自愿或非自愿地)接觸歐美日本文化之過程的一面。“詩界革命”和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與“文界革命”都與他對政治社會改革的理念分不開來。但是,雖然它引入了新詞句和新概念,卻未能挑戰古典詩的形式。“詩界革命”甚至可說是儒家詩學的延續,因為它仍然把詩當作一個重要的社會和政治工具。
梁啟超所倡導的“詩界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有二。首先,梁啟超鼓吹“舊風格”的做法并沒有超越古典詩傳統中的新古典主義或復古主義。在這個傳統模式里,詩人僅僅通過復興過去某個時期的某種風格或詩派來改變當下的詩風,他們依然在傳統的坐標系統內運作。第二點,也是更重要的一點,“詩界革命”最后只是曇花一現的原因固然不僅限于文學的層面,但是梁啟超所設想的新詩依然束縛于傳統形式之中,不脫傳統的格律。它被后人記住的原因是其歷史意義,而不是基于其詩歌作品。
真正的詩界革命要到1917年才爆發。相對于此前梁啟超的革新,胡適一方面呼吁用現代白話來做詩歌的書寫媒介,另一方面提倡“詩體大解放”。在實踐上,現代漢詩的現代性最主要就體現在這兩方面:語言和形式。
從十九世紀晚期開始,就不斷出現了倡導用現代白話做書面語的運動,進步的報章雜志也開始白話文言雜用。胡適的“文學革命”的創新處在于他建構了文言和白話之間的二元對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他把文言定位為“死的語言”,這顯然是夸大偏頗之辭。但是,他所建構的二元對立為胡適宣傳白話和提倡新詩的努力提供了極大的助力。實際上,現代漢詩是一個包容了多種語言維度的混血兒,包括文言、古代白話、現代白話、日本歐洲的外來語、新造的詞語、中國方言、翻譯詞和短語、歐化句法以及西方現代標點符號。有時候,一首新詩甚至直接引用外國文字。這種糅合不僅給現代詩帶來古典詩所不具備的資源,也是造成現代詩讀者閱讀困難的原因之一。
由于現代詩人擁有非常豐富的可供利用的語言,加上形式的自由,本土與外來的意象和思想寶庫,他們得以進行大膽的藝術實驗。現代詩既可以表現古典詩的高密度,也可以有意地散文化或使用復雜的語法。現代詩既可以是意象派式的“表意符號”(ideogram),也可以表現高度的抽象。無怪乎有些現代詩人——例如不同風格的羅智成(1955- )、鄭愁予(1933- )、于堅(1954- )——都把現代詩稱為語言的“魔術”。
為了說明作為“混血兒”的現代漢詩所體現的語法、語意、語調、節奏的新的可能,我們先來看兩首早期的作品。第一首是王獨清二十年代的《我從Café中出來》:
我從Café中出來,
身上添了
中酒的
疲乏,
我不知道
向哪一處走去,才是我底
暫時的住家……
啊,冷靜的街衢,
黃昏,細雨!
我從Café中出來,
在帶著醉
無言地
獨走,
我底心內
感著一種,要失了故園的
浪人底哀愁……
啊,冷靜的街衢,
黃昏,細雨!
有幾個很容易注意到的特征使這首詩明顯有別于古典詩。詩中的每個句子都以第一人稱代詞“我”開始,而“我”在古典詩中常常可以省略。其他特征包括:詩行的長短變化;現代標點的使用;詩行的分行排列;題目和正文中的法語。這些特征結合起來,構成一種現代感的節奏,雖然整首詩并非沒有規律的結構和押韻。
這首詩的分行造成一種停頓的感覺,既是行動的也是心理的停頓。每節最短詩行的尤其帶著戲劇性:它們被不成比例的巨大空白包圍著,暗示孤獨和凄涼。古典詩基本不存在分行和空白的問題。現代漢詩可能是中國詩歌史上第一次顯示,分行和空白具有表義作用。與此類似的是標點符號的表意作用。以西方標點為基礎的現代中文標點,1918-1920年間開始廣泛使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它也具有藝術的潛能。每一節的第5~6行里的逗號其實是多余的,并不符合標準的標點用法,但是它暗示一種欲言又止的情景。除了逗號以外,第7行的省略號表示未完成的想法或難以言說的意思,它和每節最后一行的感嘆號都有意義。它們加強了這首詩想要表達的那份茫然和哀怨。最后,所有這些技巧都有助于放緩詩的節奏,隱射敘述者的精神狀態。緩慢的拍子使得讀者得以深入體會詩中重復出現的“冷靜”。“冷靜”本是一個極為平常的詞,但是這里的“冷”和“靜”可以拆開來描述詩中的情景:對于這個孤獨的流浪者而言,黑夜細雨的街道既“冷”又“靜”。
如果王獨清的《我從Café中出來》運用了某些外國資源(分行、現代標點、外語),那么下面這首戴望舒的作品則表現出中國古典資源同樣也可以在現代漢詩中發揮新的作用。這是寫于1937年3月的《我思想》: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萬年后小花的輕呼
透過無夢無醒的云霧,
來振撼我斑斕的彩翼。
不少批評家都注意到詩中蝴蝶的意象是來自《莊子》的典故,他們也注意到第一行脫胎于法國哲學家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名言“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最值得注意的是,戴望舒雖然用了笛卡兒的句式,卻在后半句意外地填入同樣有名的莊子典故。在《莊子》的原文里,蝴蝶象征生命無止盡的幻化,寓示二元對立觀念的互換性(例如“夢境”和“現實”,“自我”與“他者”)。透過兩個典故的結合,戴望舒創造了一個新的語境。從結構上來說,詩的第一行是由八個字組成的一個完整句,也是一個靜態的句子,用系動詞“是”來表示一種存在狀態。相對于此,詩的其余三行也構成一個完整句,但是它卻充滿了動感。“輕呼”、“透過”、“震撼”三個及物動詞都是動態而非靜態的,它們體現了句子中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密切互動。從第一行簡潔的箴言句型,到后三行組成的一個動態的長句,這首詩為我們打開了一個內在視野,一只小小的蝴蝶引導我們穿越一段奇妙的時空之旅。其中悖論是,蝴蝶的聯想本來是美的脆弱和短暫,這里卻恰恰相反。蝴蝶飛越過永恒時間的無限空間,只為了回應一朵小花的輕呼。蝴蝶絲毫沒有被濃密的“無夢無醒的云霧”所阻隔,它輕快地超越了時空,和美再度相遇。
莊子物化和超然物外的觀念在戴望舒這首四行詩里有了新的涵義。透過蝴蝶這個意象,短暫與永恒、脆弱與不朽之間的二元對立被消解了。蝴蝶與小花之間的互動象征著想象力與美之間的關系。美的事物不管是多么的微小,多么的無足輕重,都會得到詩人想象力的感知和回應。在這樣一首極簡式的小詩里,戴望舒對想象力,對詩的力量的信念,具體而微地再現在這只雖然脆弱卻堅定、短暫卻終究無法摧毀的蝴蝶上。對戴望舒和其他動亂年代里的詩人而言,《我思想》也是藝術創造的持久之美的最好見證。
沒有現代的形式,現代漢詩無法發掘新的詩歌媒介。盡管胡適發起詩歌語言的革命,他把白話和文言截然分開的確是一種偏頗和誤導。在我看來,胡適最大的成就還是在詩歌形式的革命。如果不從格律嚴謹的傳統詩歌形式中解放出來,現代白話作為詩歌媒介的潛力是很難得到實現的。
形式的革命體現了現代漢詩“日日新”的實驗精神。胡適1920年出版的現代漢詩史上的首部詩集,極具深意地命名為《嘗試集》。五四時期的詩歌比其他文類更在文壇中扮演著先鋒的角色。戰后的臺灣,隨著紀弦(1913- )1954~1956年創立的《現代詩季刊》和“現代派”,是詩發出臺灣文學現代主義運動的先聲。1972-1974年的“現代詩論戰”無異是1977-1979年“鄉土文學運動”的前哨戰;后者深刻改變了此后幾十年的臺灣文學面貌。最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地下詩歌和朦朧詩引領了中國新時期的文藝復興,也是八十年代中期尋根文學的先行者。
由于現代詩人在形式上擁有充分的自由,他們也開始從理論的角度來探討內容和形式之間的關系。例如,詩人用四行詩節而不用兩行的理由是什么?為什么要把一首詩分成若干節?還有那個無法圓滿解答的問題:如何對待散文詩?它到底是詩還是散文?從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末,許多外國詩的形式被引進中國。陸志韋(1874-1970)和朱湘(1904-1933)是最早進行形式實驗的兩位先鋒。聞一多主張“相體裁衣”,也是要給詩一個貼切的形式,讓形式和內容可以有機地結合起來。除了聞一多領導的新月詩派以外,其他詩人,如卞之琳(1910-2000)、林庚(1910-2006)、吳興華(1921-1966)等,也嘗試過他們自己新創的格律詩。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臺灣的現代派也提倡“內容決定形式”的觀念。
隨著那些限定平仄、韻腳、行數、字數的傳統規則一一被揚棄,現代詩人得以發揮現代白話作為詩歌媒介的巨大潛力。雖然自由體是現代詩最通行的形式,但是詩人也廣泛地運用各種其他形式,從新的格律體到散文詩,以至具象詩(concrete poetry)。格律詩有的借自國外,比如十四行,有的由傳統中國詩改造而來,比如“現代絕句”。盡管西方十四行詩的形式約束并不比中國古典詩寬松多少,但是在中國詩人手里它被改造得相當自由。散文詩和具象詩無疑是現代常用的形式,前者在現代漢詩中已經形成了一個不可忽視的小傳統。這個傳統包括魯迅(1881-1936)、商禽(1930-2010)、蘇紹連(1949- )、劉克襄(1957- )等多家。 至于具象詩,現代漢詩最早的個例子可能是香港詩人鷗外鷗(1911-1995)的《第二回世界訃聞》。該詩的頭六行是這樣排列的:
戰爭!
戰爭!
戰爭!
戰爭!
戰爭!
戰爭!戰爭!
通過第4~6行字體的不斷變大以及第六行“戰爭”一詞的重復,詩人不僅創造了戰爭越來越近的視覺效果,而且惟妙惟肖地模仿了街頭報童叫賣外號的聲音。這首寫于1937年的詩似乎預示著不久后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
當代具象詩的杰作當推陳黎(1954- )1995年7月寫的《戰爭交響曲》: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乒兵兵兵兵兵兵兵乓兵兵兵兵兵兵兵乒
兵兵兵乓兵兵乒兵兵兵乒乒兵兵乒乓兵兵乒乓兵兵乓乓
乒乒兵兵兵兵乓乓乓乓兵兵乒乒乓乓乒乓兵乓兵兵乓乓
兵乒兵乒乒乒乓乓兵兵乒乒乓乓乓乓乒乒乓乓乒兵乓乓
乒兵乓乓乒兵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
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
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
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
乒乓乒乓乒乒乓乓乒乓乒乓乒乒乓乓乒乓乒乓乒乒乓乓
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乓乓乓乓乓乓乓乓乒乒 乒乒乒 乒
乓乓 乒乓乒乒 乒 乓 乒乒 乒乒 乓乓
乒乒 乓乒 乒 乓 乒 乓 乒乒乒 乓 乒
乒乒 乓 乓乓 乒 乒 乓 乒 乓 乒
乒 乓乓 乓 乒 乓
乒 乓 乒 乓 乓
乒 乓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如同一首交響曲的典型結構,這首詩共分為三節,每節都有384格(長24,寬16)。第一節由384個“兵”字組成,整齊的長方形圖示一支雄赳赳氣昂昂的龐大隊伍。第二節除了“兵”,開始出現“乒”和“乓”兩個字,整節的結構也開始變得不規則起來。“乒”和“乓”兩個擬聲字模擬戰爭中炮火的聲音,它們與“兵”字的區別在于它們都少了一撇,這使得它們看起來好像一些缺胳膊少腿的兵士。同時,第二節最后七行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空白格子,意味著有些兵士不見了。第一節雄偉壯觀的隊伍在第二節里漸漸支離破碎,意味著隨著戰爭的進行,越來越多的兵士受傷了,陣亡了。第三節又回復了一個整齊無缺的長方形,但是所有的“兵”都被“丘”所代替。作為象形字,“丘”圖示陣亡士兵一排排的墳墓。
與一般的具象詩相比,《戰爭交響曲》最突出的地方在于視覺與聽覺效果的巧妙結合,相互強化。整首詩只有兵、乒、乓、丘四個字,它們不僅在視覺上再現了戰爭的全程,而且它們的聲音也是全詩結構和意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一節384個“兵”字發出的是一長串響亮昂揚的聲音(朗誦這節詩需要充沛的力氣!),仿佛召喚整軍待發的一隊雄師。第二節,當我們從上往下念時,乒乒乓乓的槍炮聲變越來越稀落,聲音的空白——也就是沉默——越來越長。它暗示戰場上士兵的傷亡增加,戰斗力的減弱。
兵、乒、乓三個字都是一聲字,而且都是開放響亮的音。相對于與此,丘雖然也是一聲字,但是它是閉合的送氣音,發音要比前面三個字來得長,而且慢。除了作為一個象形字,丘也是“秋”的諧音字。秋天這個季節在中國文學文化中往往象征著衰微和結束之將至,在詩詞中它往往隱射傷感和悲涼。在陳黎的錄音光碟里,當他讀到此詩的最后一節時,他的速度明顯地慢下來,而且相當夸張地,用呼氣來拉長丘的聲音,變成“丘丘丘丘……”,仿佛在模擬秋風瑟瑟的聲音。因此,最后一節詩不僅在視覺上再現了一排排的將士墳墓,聽覺上也呼喚著秋風吹過墓園。這首詩表達的是戰爭的殘酷,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里人”,是“一將功成萬骨枯”。雖然古典詩不乏偉大的反戰詩,但是此詩運用視覺和聽覺意象的排列,只用四個簡單的漢字就呈現出戰爭從頭到尾的完整過程。它的震撼力只有透過現代的語言和形式才得以凸顯。
現代漢詩提供了有別于古典詩的新美學模式,它的現代性源自多種內在和外
在因素的結合。從外在角度觀之,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社會文化的轉型實導致了詩的邊緣化。現代詩已不再享有古典詩的傳統地位,而主要是個人性的藝術創造。古典詩面向的是一個具有類似教育背景和整齊文化素養的文人階級,他們具有相近的經驗和共同的品味。這種同質性隨著教育、政治、文化結構的改變而消失了。現代詩的歷史語境是詩人必須通過現代出版體制來出版原創性的作品,面向他們的是不熟悉新詩,背景多元的現代讀者。這種情況可能也促使現代詩普遍地接受一個詩人乞靈于“詩神”或“繆斯”的新傳統。這在古典詩里是看不到的,
誕生于1917年文學革命的現代漢詩是詩人對古典詩現狀不滿的產物,也是19世紀末以來革新古詩的努力的進一步發展。胡適所建構的新詩理論超越了此前的嘗試,不僅試圖革新語言,也革新形式。然而,讀者從前面幾個例子可以看到,現代詩雖然有意地與古典詩有所區分,但是它并沒有拋棄傳統所提供的資源。它從中外傳統中得到啟發,自如地吸取理論和創作的寶貴資源。在實踐上,現代詩人的寫作并非抗拒傳統(against tradition),而是透過傳統(through tradition)。他們運用各種富有想象力的方式,重新改造著傳統,并從中尋找新的意義,表達新的理解。在這個意義上,現代詩人是沒有選擇的,他們必須和傳統對話,因為現代白話已經融合了各種古典文學的元素。沒有對古典詩的深入理解,我們很難深入理解現代詩的美和創造性。現代與古典之間存在的是互相界定,互相照亮的關系。
如果讀者問我為什么喜歡現代漢詩,簡單的答案是:因為它不是古典詩。這決不意味著我不欣賞古典詩。但是套句西方的諺語,我們應該把“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拿現代詩來和古典詩比,無異于拿蘋果來和橘子比。我們讀現代詩并不是為了在其中找出一個李白或杜甫來,因為二十一世紀不可能出現李白和杜甫,這就像唐詩不可能出現戴望舒和陳黎一樣。讀者在閱讀現代漢詩時遇到的困難,主要來自他們對“詩”根深蒂固,先入為主的某些期待。這些期待來自他們從小到大所熟悉的古典詩,例如押韻、對仗、形式的對稱、意象的濃縮、重復出現的主題、意象與情境。對于很多中國讀者而言,適應和接受現代漢詩的過程還遠遠談不上大功告成。但是,隨著現代漢詩逐漸深入教育系統,隨著優秀作品對日常語言的影響不斷擴大,頻繁出現在互聯網及其他大眾傳媒中,我們有理由對現代漢詩的未來感到樂觀。
從歷史的角度看,現代漢詩是作為中國詩歌的一個分支出現的。它與古典詩中的各個分支是平行的關系,而不是競爭的關系。即使在現代,古典詩詞的創作從不曾停止過。新時期以來,古典詩歌社團和期刊在中國大陸涌現,古典詩的創作頗為蓬勃。或許有些現代詩人和研究者擔心這種趨勢會使現代漢詩更加邊緣化。但是,作為現代漢詩的長期學生,我對此并不擔憂。相反的,我認同胡適八十多年前所提出的觀點: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現代漢詩有著無窮盡的表達能量,它使用當代的語言和自由的形式來刻畫豐富多面的人類經驗,無疑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生動的“活文學”。
(李章斌譯)
注釋:
Jorge Luis Borges, “The Argentine Writers and Tradition,” in Eliot Weinberger, ed., Selected Non-Fiction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99), 423.
Li Rui, “Forget Joyce, What about Lu Xun?” China Daily, July 24, 2004.
Jorge Luis Borges, “The Argentine Writers and Tradition,” ibid., 423.
Michelle Yeh,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ransnational Critic: Chinese Studies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in Rey Chow,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ge of Theory: Reimagining a Field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51-80.
Li Rui, “Forget Joyce, What about Lu Xun?”
Neil Larsen, Reading North by Sou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134.
Rey Chow, The Protestant Ethn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103.
Ibid., 107.
Ibid., 48.
這里的“現代詩”和“現代漢詩”指的是用現代白話和非傳統形式寫的詩,而“古典詩歌”指的是用文言和傳統形式寫的詩。這些術語標示的是體裁而不是時代,因為古典詩歌一直有人在寫。
奚密:《臺灣現代詩論戰:再論〈一場未完成的革命〉》,《國文天地》13卷10期(1998年3月),頁72-81。
Michelle Yeh, “A New Orientation to Poetry: The Transition form Traditional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 12 (1991): 71-94.
Maghiel Van Crevel, “The Intellectual vs. the Popular—a Polemic in Chinese Poetry,” in Raoul Findeisen, Bernhard Fuhrer, and Maghiel van Crevel, eds., Chinese Text, People and Procedure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7), 59-113.
Michelle Yeh, “From the Margin: An Introductio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xxiii-l.
當然,不僅是中國的詩人對翻譯文學感興趣,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都對翻譯文學有濃厚的興趣。直到今天,翻譯作品仍然是中文文學雜志和報紙副刊的常設欄目。與北美和歐洲形成顯著對比的是,翻譯在文學界占有重要的分量,也常榮登中文世界的暢銷書單。
Michelle Yeh, “A New Orientation to Poetry: The Transition form Traditional to Modern,” ibid.
張曼儀編:《現代中國詩選:1917-1949》(第1冊),香港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頁281-82。
梁仁編:《戴望舒詩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頁126。
有趣的是,古希臘也把蝴蝶看作是人類靈魂的表征。這里不排除有這種可能,即戴望舒融合了道家和古希臘兩者的蝴蝶意象的意義。
Michelle Yeh, “From Surrealism to Nature Poetics: A Study of Prose Poetry from Taiwa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3.2 (January 2000): 119-56.
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鑒編:《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1927-1941)》香港天地圖書1998年版,頁57。
陳黎,《島嶼邊緣》,臺北九歌出版社2003年版,頁102-04。
作者簡介: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教授
查看6325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