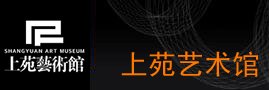|
建筑創新對城市建設有貢獻嗎
[2013-3-19 17:14:26]
建筑創新對城市建設有貢獻嗎
“建筑創新”話題實際包含了這個時代頗為引人關注的幾個問題:第一、何謂建筑創新?或者說建筑該如何創新?第二、作為社會公共藝術的建筑及創新是立足于大眾還是立足于精英?第三、建筑與城市的關系問題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影響?第四、建筑創新主要依賴于藝術還是技術?而這些問題都在一個共同的層面上顯示自身,這個共同的層面就是當今中國社會的基本狀況與國情,這些探討與思考不但是關乎國家文化戰略的重大問題,而且有著民眾公共藝術審美導向的實際意義。
反思:作為社會性符號的地標建筑
劉軍平(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博士)
符號學家迪南·索緒爾認為,符號是社會動作的文化性暗示及其背后所承載的概念;格列馬斯(Greimas)也認為,符號化的意識形態先于都市空間中的指意而存在。就都市符號學而言,建筑物質是承載與傳播社會意識形態系統的媒體,因此,地標性建筑具備高度精神的象征和文化標志性的意義,其代表了一定時代社會性意識與地域造物文明的“心象圖”(mental mapping)。隨著時間的推移,作為地標性建筑理所當然成為該城市耀眼的文化遺產,就如同悉尼歌劇院一樣人們一提起它就會想到這座城市,同樣,一談起這個城市也會想到這件作品。地標建筑具有強迫民眾去欣賞、時時刻刻傳達美育思想的社會性藝術品,其不但可以提升城市的形象,而且其設計者和組織建造者都會為此也會獲得極高的榮譽;相反,如果城市地標建筑作品格調不高,這樣會影響城市的名聲和公眾胸襟、情操的孕育。因此,地標建筑的建設是少而精的社會公共藝術品,應該慎重地將其建設成為一個傳承城市文化、歷史風貌的公眾審美象征,在一流大城市的地標建筑更是一個國家和時代精神的社會性符號。
縱觀我國當前城市的地標建筑,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問題:第一,其基本上是西方設計師藝術游戲和賺錢的“試驗品”,許多設計師根本沒有考慮該建筑所在城市的文化、審美精神需求,其建筑的語意指向、語匯形成、本土語境沒有形成高度的統一,甚至一些作品成為推行西方全球主義與文化霸權主義的工具。在投標競選中,往往一些有著國際化視野而又具有中國地緣性的作品被淘汰,長此以往,再過百年或千年以后,世界各地來中國的人們只能局限性地參觀已讓時間塵封的中國古代建筑,這個時代中國的地標建筑藝術由于同質化將會成為城市文化的空白或歷史斷層。第二,目前的地標建筑常常在已經過時的設計理念下推行“二高一怪”:建筑高度、費用高額、求新求怪。這樣的建筑物除了會造成大量資金和人力的浪費外,還會造成民眾視覺上的污染,不管當前倡導環境美學與生活美學的西方,還是倡導節約型社會和生態美學的東方,這些設計理念只能滋生項目負責者腐敗的“溫床”。第三,地標建筑是一件被敞開博物館性質的社會藝術品,所以它涉及大眾的民主和權力問題,民眾有權來選擇這個長期充斥其視覺的公共藝術品。但是,目前的地標建筑從招標、設計、施工等階段幾乎未經過媒體公示與民眾層面的聽證會,在物質賄賂與政績追求的雙重驅使下匆匆“拍板”而迅速建設起來,這是造成地標建筑長期呼喊提升而又毫無改觀的根本原因之一。
總之,隨著人類社會、生活不斷發展,不僅客觀存在的“自在之物”越來越多地成為“人為之物”,從而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地標建筑作為社會性符號的藝術品是人類精神高度集中的體現,它們也隨著人們生活實踐的不斷發展而越來越復雜多樣,我們堅決反對單一化,應該倡導通過地標建筑來凸現城市特色、探索多元性的歷史文化與現代文化融合的方式。
聆聽大眾的聲音
——地標建筑與公民社會隨想
周博 (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講師,博士)
國家大劇院的“巨蛋”設計出爐的時候,罵聲鋪天蓋地,說它光污染、高耗能、“土蛋”(因北京風沙大)、不環保等等,讀起來都很有道理。蓋起來之后,筆者進去過幾次,又覺得這座建筑的確是美侖美奐,雖然國家花了許多錢,自己一個普通公民,一年也進不去幾次,但有那么一座美麗的建筑在那里,作為一個帶人參觀的去處,又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自豪感。不得不承認,保羅·安德魯很有想象力。北京南站的設計一公布,罵聲也是鋪天蓋地,主要是說它尺度太大、大而無當等等,似乎也有道理。可現在高鐵的路線這么多,北京南站是中心樞紐,每次去都覺的客流量很大,可謂人來人往,一點也不覺得“空曠”,且功能良好,說明尺度是合適的,設計是合理的。想起首都機場T3航站樓,不得不承認,諾曼·福斯特做這類大型公共建筑的確夠格。
這兩個經驗使我發現,當一個地標建筑設計方案出臺或剛建成的時候,拿起“批評”的武器,在美學、功能以及社會學的意義上進行一般性的判斷是容易的,因為這種判斷基于評判者本身對于形式和功能的理解,基于他的品味、知識和立場,而這些往往是先于被評判的對象而形成的。所以,當新的設計出現時,拿起既有的“尺子”去量,而不問“尺子”自身的問題,這也是很正常的現象。不過,建筑問題總是復雜的,批評者一般會循常理意氣用事,可是,建筑師也不能苛責批評者,因為批評是批評家的責任和義務,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公眾的聲音。問題是,圍繞一個話題性的建筑,在幾乎總是分不清孰是孰非的爭議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種宿命般的隔閡:它首先橫亙在建筑師的建筑理想與公眾對于建筑的理解之間。
對于城市設計而言,建筑師的理想往往被描述為實現公眾的“夢想”,可是這個“夢想”在很多時候只是建筑師和決策者的“夢想”。比如,現代主義者把建筑當作平民生存的烏托邦,把人的需求標準化,試圖讓人們按照他們的理性狂想生活,可事實上人的需求千差萬別,方格化、水泥森林城市空間并不是人類的夢想。于是古典的后現代主義者抓住形式問題大做文章,他們強調裝飾主義的傳統和“文脈”意識,把人類的懷舊和美化意識放大。問題是反對文脈主義的建筑師可以說,講求“文脈”是歷史主義、折中主義的附庸,是創造力貧乏的一套托詞,并聲稱“我要用標新立異來創造新的文脈!”所以,1960年代以來,所謂“后現代建筑”,在新古典主義、解構主義、后解構主義、生態主義、高技派等現象紛呈中,早就成了一種多樣化的建筑語言實驗的集貿市場,決策者認同哪一種就會去支持、購買那種“夢想”,而不具備那些建筑前沿的專業素養、對于分享那些“夢想”也缺乏積極性的公眾則越發顯得無所適從。同時,這種隔閡也體現為建筑師、決策層以及公眾在對設計相關信息掌握上的巨大差距。事實上,當代建筑設計的工作方法決定了建筑設計早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形式問題,建筑師在做設計時一定會圍繞項目進行大量的數據收集和分析研究,甲方也會盡可能的提供建筑師所需要的相關資料和背景知識以供參酌,這些最終都會體現在設計中。但是,出于種種考慮,這些數據和分析對于公眾而言一般是神秘的,比如公眾對北京南站“大而無當”的批評其實就是在不掌握數據的情況下的做出的。如果溝通充分,在建筑設計和公眾之間的矛盾和隔閡,有些本來是不應該那么大的。
在蕪雜紛繁的議題中,我以為有些問題可能更為根本:到底是誰擁有城市?誰有權利定義我們的公共場所?這決定了我們如何定義建筑設計的利益相關方,進而也會影響到設計者的態度以及想關信息的溝通效率。在當今社會,這便牽扯到建筑與公民社會的議題。事實上,以地標建筑為代表的公共建筑其實是規模最大的公共藝術,它是市民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承擔著社會責任和公共義務,而建筑師必須完成的工作之一就是建立地標建筑與公民社會與之間的信任關系。關于地標建筑的爭論,本質上則是不同的文化與社會力量爭奪公共空間話語權的聲音。而建筑批評和建筑設計一樣,都應該尋找公民社會的立場。
菲利普·約翰遜說建筑師都是娼妓,只要有房子蓋,做什么都行。賴特的說法文雅一些,他說建筑師應該知道三件事情:第一,如何得到項目;第二,如何得到項目;第三,如何得到項目。顯然,建筑天生是不民主的,因為設計的實現完全依賴物權的所有者和出資建造者,這一點中外皆然。近來,也有一種“獨裁建筑”的言論,一些人認為對于建筑而言,只有“獨裁”才能產生杰作。這話聽起來很唬人,其實是經不起推敲的,不過是在為當代中國的長官意志決定論找托詞、唱頌歌而已。事實上,獨裁政體下產生的華而不實、虛張聲勢的建筑遠比比皆是。關鍵是“獨裁建筑”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并不符合公民社會的精神。但是,“民主”與“參與”卻是過去一個世紀推動現代設計發展的兩個重要動因,因為“大眾的世紀”到來了,建筑師和設計師也逐漸明確了“客戶”(Client)和“用戶”(User)的利益關聯與區分。盡管建筑師的利益來自“客戶”,而“客戶”的利益最終卻往往取決于“用戶”,后者既是消費者、納稅人,也是選民、公民。無疑,“民主”的概念推動了威廉·莫里斯之后的先鋒設計運動,而讓以用戶為主體的相關利益者“參與”設計的過程,這在后現代設計觀念中則比任何“主義”都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那么,地標建筑是否適用于公民社會中的參與設計原則呢?事實上,“地標建筑”是一個描述性的詞匯,它既可以是商業場所,如商場、寫字樓、旗艦店,也可以是社會或文化場所,如政府大樓、博物館、美術館、音樂廳等。前者最終訴諸的用戶是消費者,而后者的最終用戶是納稅人和公民。當然,現在這兩種空間場所有融合的趨勢:大型商場中可能“鑲嵌”著博物館和文化紀念地,而博物館和美術館則把餐飲和休閑當做維持經營的手段。不過,無論人以何種角色在其中出現,他們都是建筑的“用戶”,但是他們的意愿又一定會符合“客戶”的利益訴求,無論這個客戶是商家,還是政客。因而,地標建筑,無論物權歸誰所有,都適用于參與設計的原則。
因此,盡管我們可以把地標建筑比一個城市的珠寶首飾,承認它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燦爛奪目,但是,這個首飾的存在價值卻在于建構一個有意義的公共空間,而非盲目的自我炫耀。雖然我們要承認,建筑師卓爾不群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以及挑戰世俗成見之心永遠是一個奇幻的異數,但是建筑設計不是在編造神話,建筑師一定要聆聽大眾的聲音。要知道,只有公民社會的意志才能夠最終決定我們的公共空間。誠如丹尼爾·李布斯金所言:
“建筑存在于這個世界之中,為人而存在。合作的意義在于傾聽別人,從別人身上學習,讓他們從你身上學習。沒有人能自己一個人興建一個大項目。”
我一直認為,建筑和設計與中國當代公民社會的成長有密切的關系。如果我們相信當代中國應該且正在朝著公民社會的方向邁進,公民參與必然是一個重要的設計方法。如果我們普遍認同當代社會的豐富性和多元化的價值,那么任何一種價值都不能攜帶先天的合理性。“參與”會給人帶來快樂與幸福,參與也是構成普通人在公民社會中尊嚴的一部分。我認為,在平民建筑中,公民參與最好從設計的起點就開始,而在地標建筑中,公民參與要充分的體現在建筑的競標過程中。要讓各個相關利益方充分的辯論,這是一個相互了解、相互溝通的過程,其意義恰在于消弭“宿命般的隔閡”,我相信這個過程一定會充滿想象力的冒險和智慧的交鋒,這也是優秀的地標建筑在破土之前應該接受的洗禮。
建筑個性如何在城市中展現
李星星(中南大學建筑與藝術學院教師,博士)
建筑創新對城市建設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對于我國目前城市建設的建筑創新而言,其貢獻確實值得懷疑的。
“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將權力轉化為形式,將能量轉換成文化,將無趣的轉換成鮮活的藝術符號。” (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正是由于建筑師們和城市建設者站在自己的立場強化了“形式”、“文化”、“藝術符號”,才導致城市建設現狀:沒有從國家、城市的整體文脈入手;而是強調了建筑的單體藝術個性。
就扎哈·哈迪德的單體建筑而言,很有個性和高科技氣息,很具有形式美感(我不稱其為現代氣息,是因為她的建筑是否代表現代還須拭目以待)。建筑設計有它的符號性,而她的建筑符號已在中國大地處處開花;如果在世界各大都市都矗立有扎哈的建筑,創新之后仍趨于雷同;各大城市被外在的形式建筑所包圍,忽視了城市之間的文脈差異,這有悖于建筑本體論。建筑師的個性,是其自身文化的體現,是其認識世界和再創造世界的物化。“個性以不同的形式呈現——定制的方法、語言游戲、使用者參與或宗教主義等等。由于個性缺乏常規的拘束,因而有極其豐富的含義,顯得很不尋常。”(克里斯·亞伯《建筑與個性——對文化和技術變化的回應》)。個性表達的主體是人,個性物化的客體是物(本文的客體只針對建筑物),人的多面性賦予了客體個性的豐富表現。所以說,建筑一開始就強調文化和社會心理存在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建筑師的個性和建筑空間營造的個性是互為表里的。建筑師本人的文化底蘊和對建筑的認識,以及對現代科學技術的研究應用,決定了建筑空間營造的個性,同時,建筑的個性還受到政治、權力、經濟、文化、宗教和場地氣候的影響。但扎哈·哈迪德的建筑在中國落成,其建筑個性是凌駕于中國文脈之上的。以長沙梅溪湖扎哈設計的國際文化中心為例,其建筑個性與當地文脈、地理環境的氣場是相悖的。但是,這種局面的形成與權力部門有相當的關聯;在這種現狀下,討論建筑創新對城市建設是否有貢獻,似乎是紙上談兵。
另外,創新型建筑師丹尼爾·里伯斯金在其德累斯頓軍事博物館開幕時坦言道:“我希望創造一個大膽的結構,一次徹底的混亂,他要穿透歷史的殿堂,營造出全新的體驗。建筑將使大眾更加深刻地感受暴力、軍事和城市命運之間的糾結。”他的這種個體思想影響了博物館的建成及其建筑個性的強烈展現。如他所說,要穿透歷史的殿堂,營造出全新的體驗;但這種體驗值得深究。從建筑藝術的角度看,他是在建筑與藝術之間玩邊界,更強調其藝術性,忽視了建筑的本體意義。
從文化的角度看,城市的出現是人類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標志,是人類群居生活的高級形式。要想建筑創新對城市建設有真正的貢獻,不能讓城市建筑只強調藝術的形式和大腕建筑的單體個性,必須根據不同國家、不同城市的文脈和地域因素來整體規劃城市建筑設計。
建筑創新應是城市生長的良性變異
許凱明 (安徽大學建筑學院講師、博士)
在共同國情之下,建筑創新與城市建設從來都不是截然割裂的,而是同一系統中指向同一問題的微觀與宏觀視角。這種視角的差異除了橫向覆蓋面的不同,還是把這個時代作為縱向時間軸上的片段來看待的歷史眼光——城市類似于一個生命體,她有著自身的發展過程和特殊規律。而建筑作為一個城市的基本元素和功能單元,構成了一個特定區域網絡的局部和節點。不論是作為歷史片段還是局部節點,建筑和城市都烙上了深深的時代印記和地域特征。建筑的創新和城市的更新之間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關系,是共同的時空流變體系中的局部與整體關系的顯現。
那么,建筑創新與城市建設的關聯到底關涉哪些重大的問題呢?
首先,創新絕不是空前絕后。建筑創新應該是城市生長的良性變異,是建筑在特定環境中的合理延伸。如何適應一個時代的發展需求和特定地域的有限資源,是建筑創新者尤其需要關注的問題。我們這個時代并不缺少創新,缺少的是合乎科學和藝術標準的創新。在這個高速發展的時代,過剩與匱乏是并列而行的,過剩的是商業和功利目的的絕對膨脹,匱乏的是社會關懷與審美能力的極度萎縮。在過度功利欲的壓力之下,創新更像是商業炫奇或政治作秀,因為它們顯現的價值標準不會超越利潤和政績的有限維度。歷史符號和西洋風的泛濫就是這種炫奇和作秀的典型,它們共同的特征是錯把肉麻當成有趣的文化低俗和對藝術風格毫無邏輯的時空大挪移。
其次,建筑需要科學創新。作為人類的生存環境,建筑和城市是自然界最不自然和最脆弱的物體。在各種天災人禍之下,各個時代的人類文明最終都歸結為層層相疊的地質斷層。在有限的時空條件下,需要我們理性和科學地對待這個人類的庇護所——這是建筑創新與城市建設的內在邏輯關系,任何拋棄了這種關聯的標新立異都是對自然規律和科學精神的曲解與背離。
再次,建筑創新應該包括環境貢獻。作為造型藝術,建筑不同于繪畫的特點是,建筑總要扎根于特定的環境。不管這個環境是城市還是鄉村,建筑總是嵌入這個現實環境的一種人為的局部。建筑的任何變異都會導致環境的改變,合乎邏輯的建筑創新應該是環境機體良性與有序地發展。令人遺憾的是,當今我們城市的惡性膨脹和環境、交通的驚人無序等等弊端,恰恰反映出非邏輯和非理性因素的強大。雖然這種惡性變異并非建筑創新使然,但建筑無視環境地變換形態也同樣是對環境的一種傷害。這種無視環境的改變并沒有給城市帶來特色,而是讓這種無序狀態更加廣泛,它給當代城市形態帶來的顯著影響是城市地域特征的普遍消失——千城一面,就像雜音蓋過主旋律后剩下的只有嘈雜。
有人說,從一座城市可以看出一個時代的心聲,那么從一座建筑也同樣可以把握一座城市的脈搏。建筑創新就是讓我們去抓住這座城市的心聲和脈搏,在具備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征與品質的同時,它也需要一顆善于傾聽的敏感心靈和勇于擔當的社會責任感。
技術也是一種文化
朱力(中央美術學院建筑學院博士生)
從被民眾稱為“鳥蛋”的國家大劇院、被稱為“鳥巢”的國家體育場,進而被稱為“鳥腿”的CCTV新大樓等地標性建筑,其在體現權利與資本的同時也成為媒體大眾關注的焦點。每一個標志性建筑的調侃命名不但給建筑師一種無形的批評,而且給建筑主管部門莫大的壓力。學者河清曾以“應當絞死建筑師?——中央電視臺新大樓中標建筑方案質疑”為題,對CCTV新大樓的設計進行了抨擊,認為其“最大程度的抵觸了中國文化的審美價值標準。”而當CCTV大樓的設計師雷姆·庫哈斯在其出版的Content一書附錄中出現以CCTV大樓和色情女星的拼貼封面海報時,媒體大眾被徹底激怒并紛紛加以討伐。一時間,“文化性與民族性”成為評價地標建筑的核心標準。
誠然,地標建筑應具備文化的承載功能,但其創新性不應僅僅局限于審美文化的價值尺度之中。法國的埃菲爾鐵塔,初建成時也曾一片嘩然,在文化意識上不被接受,而最終它卻以代表工業文明的先進建造技術為依托,成就了它的法國標志性。同樣,中國國家體育場的建筑學意義也不應局限于“鳥巢”的文化含義,其建造帶動了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Q460鋼材的研發和110毫米壁厚的鋼板的應用,材料的創新與先進的技術造就了新的地標建筑;CCTV新大樓空中連接的懸挑60米的桁架結構加以鋼外包混凝土的防火結構,在高層建筑設計上達到世界領先水平,其技術創新更是毋容置疑。
建筑的價值不僅訴求于美學,更在于功能,在于使用是否合理。而建筑師始終在形式與功能之間尋求平衡,優秀的建筑師更是把感性和理性完美結合,在藝術與技術的交互中造就了悉尼歌劇院、香港中銀大廈等地標建筑。在這些優秀案例的背后,先進的建造技術是其立足的根基。建筑設計如同產品設計,在近代早期的西學東漸和洋務運動中,對待現代產品設計上同樣遇到過審美的差異和文化的尷尬。國人對于鐘表、家電等工業產品的理解從最初的“奇技淫巧”到后來的全盤接受,這并不是因為中國人民文化審美的改變,而是由于現代技術的不可阻擋,繼發國家的現代文明之路也正是從對工業技術的學習和創新中開始的。
由于建造技術的落后,我們在建筑設計上與世界對話的失語狀態是客觀存在的,這不能用強調民族文化的“策略”來搪塞。建筑形式的文化表征固然重要,但技術的創新才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核心。對于擁有深厚歷史文化的繼發國家,地標建筑在文化性上的反思應該建立在先進的建造技術與現代的功能基礎之上,在當下高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中,我們只有先多一份技術才能多一份文化。
(以上文章均發表于2013年3期《美術觀察》,文章由劉軍平組稿和編輯)
查看5945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