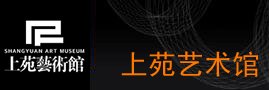Ԋ(sh��)����â�ڡ���Էˇ�g(sh��)�^��Մ����һ�NԊ(sh��)�衷
�r(sh��) �g��2008��8��21��
�� �c(di��n)����Էˇ�g(sh��)�^�D���^
����(zh��)�ˣ��� â
�� �T�� �ײ������U�ɸ����h���A����С�������ʺɡ��S�o�h(yu��n)���S�ɳ���Y �ơ��� ������־ƽ�������䡢�� �ԡ�����⡭���ȣ�������ƴ���ţ�
Ԋ(sh��)�ˡ��W(xu��)�ߣ���â
���(ji��n)�v��
�����S�������1983-1993���ڱ�����W(xu��)����ϵ�Ⱥ�@���Ї�(gu��)�ČW(xu��)�W(xu��)ʿ���Tʿ�Ͳ�ʿ�W(xu��)λ��1993���ƾ�����(gu��)��2001��@������(gu��)���ݴ�W(xu��)��ɼ����У���^�ČW(xu��)��ʿ�W(xu��)λ����2000���������ν�������(gu��)���W(xu��)Ժ��Connecticut College)�|��ϵ���о����v���Ї�(gu��)�F(xi��n)��(d��ng)���ČW(xu��)�ͱ��^�ČW(xu��)���F(xi��n)�θ����ڣ�ϵ���Ρ�����Ӣ�ČW(xu��)�g(sh��)�о��͕��u(p��ng)�l(f��)���ڸ��N����(gu��)�W(xu��)�g(sh��)�ڿ����������ǡ���(d��ng)���Ї�(gu��)�ČW(xu��)�����Ļ��������δ����(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Future)(�~�s��Palgrave Macmillan, 2007)�����ڶ�ʮ���o(j��)��ʮ�������â�������ڱ���У��(n��i)��Į�(d��ng)��Ԋ(sh��)�ˣ��ƾӺ���֮���^�m(x��)�����ĺ�Ӣ���p�Z(y��)��(chu��ng)�������g�����b����������Ԋ(sh��)�����ӽ�äĿ������Ӣ���p�Z(y��)Ԋ(sh��)����ʯ������
�� â���Ҹ���С���͌O�IJ����Ƿdz��õ��������ˣ��ұ����nj�Ԋ(sh��)�ģ�����ϲ�g��ˇ�g(sh��)�ҽ����ѣ���(du��)�L������(du��)ˇ�g(sh��)���dz����dȤ���Y�ơ�С�����f��â���^���vһ�Σ����X���v��̫�m���@�N�h(hu��n)�����ټ��ϴ�ҵČ��I(y��)�н��棬����džη�����v����ݔ�������Ҷ�����(hu��)ϲ�g���������Y�Ə����ĽǶȽo�҂��fһ�£������҂�����о���һ�Kϣ��ӑՓһ��(g��)ʲô���}��
�Y �ƣ���âǰ���Á��^ˇ�g(sh��)�^�������������M��һ��(g��)�}Ŀ����������죬���˰���Ҳ�]�����(g��)�}Ŀ��ǰ�������ڱ�������һ��(g��)�v�����vǣ���푺ܺá��@��Ո(q��ng)������Ҳ���vЩԊ(sh��)�跽��ģ�����һ���������Ԋ(sh��)�������^�P(gu��n)עˇ�g(sh��)����Ć��}�ͬF(xi��n)�����ڿ��W(xu��)Ժ��Ҳ��ˇ�g(sh��)ϵ���Ƿ����Մ?w��)���Ҋ���ġ����|��������(gu��)��һЩ�W(xu��)Ժ��ˇ�g(sh��)�һ���ˇ�g(sh��)ϵ�W(xu��)���Ġ�r��
�� â����Ҵ��Ǯ����ģ�����Ԋ(sh��)�ͮ���ˇ�g(sh��)֮�g�϶�����ͬ�ĵط����ҵ��ǜ�(zh��n)����һ��(g��)�}Ŀ���С���һ�NԊ(sh��)�衱��
�Ҍ��|�����^�磬��ʮ������_ʼ���������Լ�����һ��(g��)��ã�1986��ĕr(sh��)���Լ��ͽ�äĿ���x�ߣ�����â�����f����һ��(g��)äĿ���x��Ԋ(sh��)�ˣ���äĿ���x��Ԋ(sh��)�衣��(d��ng)�r(sh��)���кܶ��ˣ������ҵ�һЩ���ѣ������f�馣��͆���â���@��(g��)äĿ���x��ʲô��˼�����ܲ����U��һ�¡��Ǖr(sh��)��Ҷ�֪�����L(f��ng)����ӿ�ĕr(sh��)���Ҿ͌���һƪ���ĽС�ՓäĿ�����l(f��)�ڱ�������ϵ�Ŀ�������ǡ��ϡ����߀��һ�N��Ԋ(sh��)ՓԊ(sh��)�ķ�ʽ���^ͬ���}Ŀ��Ԋ(sh��)����(d��ng)�r(sh��)�Ҿ��f�ҵ��@�N�����Լ���(du��)Ԋ(sh��)��Ŀ�����һ�N��äĿ�Ŀ����������@�NäĿ�������Ҫ�r(sh��)�g���o�����壬���f�@��(g��)�|���^��ʮ�����f����(d��ng)�r(sh��)�X�ö�ʮ�����b���ɼ��ġ����Ƕ�ʮ�����^ȥ�ˣ����@�λ������������f�㌑һ��(g��)���Ԋ(sh��)Փ����Ҳһֱ�����@��(g��)���}�������f���Ү�(d��ng)�����猑�|���ĕr(sh��)�ͱ����Լ�Ҫ���e�˲�һ�ӵđB(t��i)�ȣ�Ҳ�����ǂ�(g��)�˵��Ը�Ҳ�����ǂ�(g��)�ˌ�(du��)���W(xu��)��һ�N��(b��o)ؓ(f��)������һֱҪ������һ�N�|������һ�NԊ(sh��)�衣�@��һ�N�|���������������Ŀ��ܶ���(hu��)���룬��һ����Ԋ(sh��)�裬Ҳ������һ�N���ˇ�g(sh��)����������ָʲô���@��(g��)���}Ҳ����һֱ����ġ������1993�����(gu��)����ȥҲ��ʮ�������ˣ��ڇ�(gu��)��Ҳ���|�˺ܶ࣬����Ӣ�Z(y��)Ԋ(sh��)�ˣ�������Ҳ�ܶ࣬�Ї�(gu��)�Ļ���������(gu��)�ģ����кܶ�Ľ��|���҂����鮔(d��ng)����һ��(g��)Ⱥ�w��һ��(g��)�������ҵ�һ�N�|����һ�N��λҲ�ã�һ�N����Ҳ�ã���ô������ʲô�|���܉���҂��^(q��)�e�_�����c��ͬ�r(sh��)���@�N������܉���һ�Nʲô��ʽ���҂���(du��)ˇ�g(sh��)��(du��)Ԋ(sh��)�茦(du��)�ČW(xu��)��(du��)�����Ŀ�����չ�Եؼ����ݣ�Ҳ�����f���@�N����ЃɷN��һ�N���ų��Ե�����Բ���ʲô���b������ʲô��߀��һ�N�t�ǣ��@��(g��)�Ҹ��dȤ��������߀���dȤ����ģ������@��(g��)����Ҳ�������ǂ�(g��)���@��һ�N����ǰ����Եġ�
�����µ������³��ڕ��귭Ҋ�����궼�����ġ����(gu��)��ˇ���ڿ���������һ�������Ђ�(g��)���g��÷���ѣ��x�g�˲��mԊ(sh��)������ʲ�����һ��Ԋ(sh��)�����ˡ�����������Ԋ(sh��)�С��t���Ĵ��졷����(d��ng)�r(sh��)�ܴ��(d��ng)�ң��ҽo�����ǰ���䣺������졣ֱ�������ʮ/�ҲŸе������_�˵��T����̤��/�峿�������������@ô���䣬�ܺ�(ji��n)�Σ������ʵĿ���߀�ں��棬���@�ѽ�(j��ng)���ܴ��(d��ng)�ҡ��ܴ��(d��ng)�ҵ���˼�����f����һ��(g��)ˇ�g(sh��)�ң�����һ��(g��)Ԋ(sh��)�ˣ������ǽ�(j��ng)�v������(g��)20���o(j��)�Ěvʷ����ij�N���x���f�ǚW�ޚvʷҲ������vʷ���@ôһ��(g��)Ԋ(sh��)�ˣ���������ĕr(sh��)���ٷ��^�^�����@�r(sh��)������Ė|��������һ��(g��)��(f��)�s�Ė|��������һ�N�܆μ��ģ������Ǻ������Ė|����Ҳ�����f���������ĺܶཛ(j��ng)�(y��n)���^�V�ˣ������@�Nʹ�࣬�@�N�n�]�������к�ؓ(f��)��Ė|�����������˷��ˡ����֪��������ʲ��������Zؐ����(ji��ng)����������(gu��)�ĵ�λ��һ��(g��)�dz����صĵ�λ������ʲ���x��ȺҲ�S���Ǻܴ������ij��������Һ�Ԍ���ľ��Dz�ͬ�Ʉe��һЩԊ(sh��)�˻����u(p��ng)�ң�ƽ�r(sh��)������ˮ�����ݵ��@Щ��Մ�����ĕr(sh��)�ܷ��⡣��������֮̎���ڣ��mȻ���ǚw��������(gu��)�����Ǻܶ��˲�֪��������ô�k�������f��������(gu��)Ԋ(sh��)���һ���֣����@��(g��)�˺����@������(gu��)Ԋ(sh��)��������һ��(g��)���(gu��)�ˡ��Ђ�(g��)�����W(xu��)�Ľ��ں�Ԋ(sh��)�u(p��ng)�Һ������ص�������(j��ng)�f�^������(gu��)Ԋ(sh��)���x����ʲ���]ʲô�ɌW(xu��)�ģ���W(xu��)���ˣ���?y��n)����?gu��)Ԋ(sh��)�˛]�н�(j��ng)�v�^�ǘӵĚvʷ�����Ǟ�ʲô�҂�߀��(y��ng)ԓ�x���أ��ص��՛]�м�(x��)�f�������҂�(g��)�˵Ŀ���������ʲ����������һ�Ԋ(sh��)�裬�����IJ���������(gu��)������Ԋ(sh��)�裬����һ��(g��)����������ښW�ޣ��������������һ�Εr(sh��)�g������һ�ε��c(di��n)���棬�����ܕ�(hu��)���Ė|�������@��(g��)��������ʲ�����x�������ر��@�����ˡ�
����ʲ������ĕr(sh��)���^һ��Ԋ(sh��)���С���������֮���������������������ąs�nj�(du��)��������ϲ�g�İ����ڃ�(n��i)���Ї�(gu��)�Ŵ�Ԋ(sh��)�˵�һ�N��������������ʲ�ĺ�����_ʼ���g�Ї�(gu��)Ԋ(sh��)�裬�Ї�(gu��)�Ŵ�Ԋ(sh��)�茦(du��)�������fͬ������һ�Ԋ(sh��)�衣�҂����Կ������ܶ�����(gu��)Ԋ(sh��)�˺��wĽ����ʲ���f����ʲ�@��(g��)�������\(y��n)����?y��n)����?j��ng)�v����ô���vʷ������ʲ��1911������2004��ȥ������ӛ�·dz��磬�������ӛ��֮�о�����1913���S��ĸ������܇ȥ���������Ľ�(j��ng)�v���Ǖr(sh��)���һ��������(zh��n)߀�]���l(f��)�����f���Ǖr(sh��)���_ʼ�����M(j��n)���˚vʷ������������ĕr(sh��)��e�ˆ����@һ݅����ʲô�z���ģ�����ʲ�ͽo�@��(g��)���pԊ(sh��)�˄���f�@һ݅��ǧ�f��Ҫ������Ԋ(sh��)���f���@һ݅�Ӿ��@ô���ˣ���ȫ��ij�N�vʷ��Ū���ұ����ȳ����@��һ��(g��)Ԋ(sh��)�ˣ��䌍(sh��)�Ҹ�Ը�⌑����һЩ��(ji��n)�εģ������Ė|��������ʲ�������ς�(g��)���o(j��)�ԁ�������(g��)����Ԋ(sh��)���������(f��)�s��һ��(g��)Ԋ(sh��)�ˣ�����Ԋ(sh��)�����䌍(sh��)��M�˷��S����������һ��(g��)����20���o(j��)�ښvʷ֮�д��ڵČ��εă����ԡ�һ���������J(r��n)�@�N�����ԣ��@�N�μ��ԣ��@�N�����T������һ�������ֲ��ܷ��J(r��n)�F(xi��n)��(sh��)���挍(sh��)�ԣ��������ǘ�һ�N���Ǻ����ģ��ܼ��J�ģ�ij�N�̶��ώ��������ԵĬF(xi��n)��(sh��)��(du��)����ײ�������]�лر��^ȥ������ʲ�@��(g��)Ԋ(sh��)����һ��(g��)�܂���ĵط��������������ڽ̂��y(t��ng)������������ͽ���mȻ�������ǂ�(g��)�R��˼���x�ߣ�������ǂ�(g��)��Ҋ���ӣ��������f��ӛ������������Լ������ڽ����ﳪ�����ĕr(sh��)�̣��ǷN�|��һ݅������������(sh��)�H������ʲ�ǰ���������Ƶ��@ôһ���K��Ť�Y(ji��)��һ���������ƵĖ|��ȥ�˷������֮�g��ì�ܣ��@��һ��(g��)�dz���ijɾ͡�
Մ������ʲ�����ӌ�(du��)�҂���ʲô�P(gu��n)(li��n)�أ��҂�(g��)��һֱ�@���J(r��n)�飬�mȻ�Ї�(gu��)��80����Ժ�һֱ����һ�N��(sh��)�(y��n)�ԵĖ|����һ�N���J�ԵĖ|����һ�N���h�ԵĖ|���������X���Ї�(gu��)Ԋ(sh��)���ߵ�߀��һ�N�η����ͻ�M(j��n)��߀��ȱ��һ�N�C�ϵ�������һ�N�����V���Z(y��)������Մ�@��(g��)��Ŀ�Č�(sh��)�H�����fҪ���҂����R(sh��)�ĵ�ƽ��չ�_��һ�����@��(g��)��ƽ������ʧ���ˣ��]���ˣ��҂���̎����һ��(g��)����(du��)��y�ģ������W���@ôһ��(g��)�r(sh��)��������һ�����@��(g��)��ƽ����(du��)��ijЩ�ˁ��f��һֱ���ڵģ����Q������(sh��)�`�ķ��Q��������ʲô�ط��ߡ�������]���۾��f�Ҳ����J(r��n)�@��(g��)��ƽ���Ĵ��ڣ��Ҳ��J(r��n)���@��(g��)�����ԵĻ��ڽ��ԵĖ|�����vʷ�ԵĖ|�����Ļ��ԵĖ|����(du��)�����κε����x��Ԓ��������Է��J(r��n)��������ä�������@�ӵ�Ԣ���������ģ��@��(g��)��̫���ˣ����Ըɴ��]�������҂�ֻ���������w���ȣ����ӣ����䣬����������������Q�@�������ҿ����ø��N��Փȥ�C���@һ�С��@һ�Џ�ij�N�����f����Ч�֟oЧ����Ч���f�҂��F(xi��n)�ڵ���Փ��ij�N�̶����f�Ƿdz��İl(f��)�_(d��)���������κ�һ�����鶼���������C���������q�ס�����һ������ʲôҲ�]�C���ˣ���?y��n)�ˇ�g(sh��)��Ҫ��������Ľ�����(sh��)�H�ϲ��]����ͬһ��(g��)���棬��ͬһ��(g��)��ƽ����չ�_���҂�(g��)�˵Ŀ������ǣ��Ї�(gu��)��(d��ng)���Ļ�����ˇ�g(sh��)�ĵ�ƽ�������Ǵ��_�ˣ�����ijһ���棬ʼ�K��һ���T�Ǜ]�д��_�ġ�
�f�@ô����Փ����Ҳ�]ʲô�ã��Ҿͽo����xһ��Ԋ(sh��)���@��Ԋ(sh��)����2000��5��9̖(h��o)����ɼ�����ġ�2000����һ��(g��)�µ����o(j��)���_�ˣ��������ĽǶ��f�@�Ƕ�ʮһ���o(j��)���_�ˣ���һ��(g��)�^��֮�꣬��(du��)�҂�(g��)�ˁ��fҲ��һЩ�������x���кÎ����x���ҾͲ����ጣ���Ը����@Щ������Ԋ(sh��)���档��(d��ng)�r(sh��)��������(gu��)Ҫ�������������|����ȥ���Y(ji��)���ڼ��������������ڱ�������һ��(g��)��ʿ��������(gu��)������һ��(g��)��ʿ���ڱ������������õģ�������(gu��)�䌍(sh��)��Ҳ�������õġ����ǚvʷ�r(sh��)�g���������־���D(zhu��n)�ƣ����X����߀�����棬��(sh��)�H�ϵ�����׃��Ҫ�J(r��n)����ˡ���ǰ�t��һ�N���혷���|(zh��)�ģ���ؓ(f��)؟(z��)�ε����M(f��i)�r(sh��)�g�������M(f��i)���پ����M(f��i)���١����������������(gu��)�̌W(xu��)�������@�ӣ����������ώ�����W(xu��)���I(y��)�Ժ�ĵ�һ�꣬���߀�]�й������ґ�(y��ng)ԓ����ȥ�����f���һ��ʲôҲ���øɣ�������]����s�oȥ�棬���������ȥ�档������W(xu��)�����ģ���Ҳ���õ��Ї�(gu��)ȥ���㵽�����������κεط������ԣ�����@һ�����^ȥ����?y��n)����Լ�߀��֪����(y��ng)ԓ��ʲô�����ώ����V����ʲô�@���Ǐ�(qi��ng)������Ҫ�Լ�ȥ�ҡ����ǻص�2000�꣬�Ǖr(sh��)��Ҫ�x�_��ɼ������̫ƽ������������|���Ժ�����Ҫ�ı�����ꑵ������������|����ȥ�������ҬF(xi��n)�����ڵĿ����Ҹ��ݣ��dz�Ư����Ҳ���ں�߅�ϣ����Լ����룬�@��(ji��n)ֱ������(j��)��һ�ӡ������@��һ�������f��õ���ʲô�|���������p�ĕr(sh��)����ˇ�g(sh��)������õ�ʲô�|������Ҫ��ȡʲô�|������Ҫץ��ʲô�|���������㵽��ijһ��(g��)�A�εĕr(sh��)��͕�(hu��)�l(f��)�F(xi��n)����һ��(g��)��������õ����ٖ|������͕�(hu��)ʧȥ���ٖ|�����@��һ��(g��)��͵��Α�Ҳ�����f�����������õ���һ�е��I(l��ng)����ˇ�g(sh��)�ϵõ��ijɾͣ�����Ҫ�ô��r(ji��)ȥ�Q�ġ��Ҍ��@��Ԋ(sh��)�ĕr(sh��)��ͺ������@�N���X���@Ԋ(sh��)�����Ї�(gu��)�ā�]�Ю�(d��ng)���x�^��ֻ��ȥ���ڡ��ɽ���s־�ϰl(f��)���^�����nj�������ɼ������һֻϲ�o������(y��ng)ԓ���d������Ԋ(sh��)���}Ŀ�s�С��Ҷ���@ൣ��挦(du��)ϲ�o��������
����������;
��ֹһ��
�Ҷ���
�@�
�挦(du��)ϲ�o
����(y��ng)�ɞ���
������
�s�ɞ���
��
����(y��ng)�ɞ��
���Ǒ���
�s�ɞ���
��
����(y��ng)�ɞ����
���ǿ�����
�Ҿ�
�s�ɞ���
�_ͻ��
���c���۵�
��
������x��
�����B��
�S��
���b
Ҳ�����
ͻȻ
��(ji��n)Ӳ
����(y��ng)�ɞ���l(xi��ng)
�����٘�
�s�ɞ���
��Ĭ������
����
����
Ԋ(sh��)���䌍(sh��)��̎�����˵�ʣ����Ϳ��x���ܲ����x������
��С���� ���xԊ(sh��)�뵽�ϴ��҂��v�^ˇ�g(sh��)�҂�?c��)�һ�KҲ�x��Ԋ(sh��)���xԊ(sh��)������Ҳ�xԊ(sh��)�����Լ��x�Լ���Ԋ(sh��),Ҳ���x�e��Ԋ(sh��)�ģ�ÿ��(g��)�˸���(j��)�Լ��������ڰl(f��)���������xԊ(sh��)�ĕr(sh��)���Ҹ��X�������xԊ(sh��)��һ���ă�(y��u)��(sh��),�֓P(y��ng)�D�졣���놖���ʲô�ɂ�(g��)������(g��)��һͣ�D�����e�˲�һ�ӣ���ᘌ�(du��)�@��Ԋ(sh��)߀�������е�Ԋ(sh��)���@�ӣ�
�� â�������е�Ԋ(sh��)�����@���x�ġ��@Ҳ���ܸ����L(zh��ng)�ڽ�����(gu��)�W(xu��)���h�Z(y��)���P(gu��n)ϵ��߀�У����X��Ԋ(sh��)��һ��(g��)�r(sh��)�g��ˇ�g(sh��)�����ڕr(sh��)�g��(d��ng)��Ҫռ��(j��)һ���Ŀ��g�����x��̫���@Ԋ(sh��)��ɽ������܇һ��ಾ��^ȥ�ˡ����X�Ï��҂�(g��)�˵�Ȥζ���f�@������һ��(g��)����ì�ܰɣ���?y��n)�ƽ�r(sh��)�������fԒ���ڷ���ʽ����r�£����dz��������fԒ�죬��С����ܵľ����@���档���⣬��ƽ�r(sh��)��һ���(ch��ng)�ϲ�Ը�x�Լ���Ԋ(sh��)����������һ��(g��)����
����⣺ ���xԊ(sh��)�ķ�ʽ�ܹٷ�����o�˵ĸ��X���njW(xu��)Ժ�ģ��҄����ھW(w��ng)�Ͽ�����Ľ�(j��ng)�v�����x�^�ܶ��������������^�ܶ��W(xu��)λ���ǂ�(g��)�ÌW(xu��)λ��(du��)����Ԋ(sh��)�����҂�(g��)���J(r��n)���Ҳ�֪����ʲô̫����̎�����x��ʿ��(du��)����Ԋ(sh��)��ʲô��̎������ֻ�������ҫ�������@ô���W(xu��)�v����(gu��)��(n��i)�ć�(gu��)���һЩ�õ����ƴ�W(xu��)�Ҷ��У����ҹ��������Л]��һ��(g��)�ܬF(xi��n)��(sh��)���뷨�������x����Ŀ���Ǟ��˸��õ���������Ǟ�������Ԋ(sh��)��ȥ��Ԋ(sh��)��
�� â����Ć��}��÷dz��ã��@��(g��)���}�Ү�(d��ng)��Ҫ����ʿ�ĕr(sh��)��Ҳ���^�Լ����҂���ʮ������Ǖr(sh��)���X�ò�ʿ���������о������^ɵ����ţ�ľ����҂������������ұ����k�s־�k����M��һ�еĻ��(d��ng)��Ҫ���DZ����������Ҷ����҂����߾��_ʼ����һ���˶��������@��(j��)���Ìö��зdz��͵��ˡ��ҿ��Tʿ������ʿ���DZ�����ȥ�ģ���(d��ng)�r(sh��)����Ը�⿼����(d��ng)�r(sh��)���Tʿ����?y��n)������W(xu��)���I(y��)��Ҫ���䵽�C(j��)�P(gu��n)�������Ҳ�Ը��ȥ�C(j��)�P(gu��n)���Ҿ�Ը���ڱ����ٻ����꣬��Ҳ�����g��(y��u)��(sh��)�����ԻΡ�����ʿ�ĕr(sh��)����Ҳͬ�ӷdz�ʹ�࣬������Ը�⿼���Ү�(d��ng)�r(sh��)���ҹ����ˡ�������1990�꣬��һ��ĴTʿ����dz��y���ҵ��Ĺ�����Ҳ����ϲ�g���ǽ̕��Ĺ������ڇ�(gu��)���ϵڶ���(g��)��ʿ�����Ҳ���Ը�ģ���?y��n)��Ү?d��ng)�r(sh��)�ǡ���ޡ���ȥ�ģ�������ȥ�ġ���(d��ng)�r(sh��)�����ʮ���ĩ�Ѓ��ɣ��ɂ�(g��)���h�����ɺ����ɣ�һ��(g��)���и���һ��(g��)���錢�ɣ��҃ɂ�(g��)�����ǣ��������ɣ�̖(h��o)�Q�^��(du��)�����и�Ҳ�ܵ�����(gu��)ȥ����ȥ���Ժ���һ��(g��)�F(xi��n)��(sh��)�Ć��}�����ܸ�ʲô���Ү�(d��ng)�r(sh��)һ��(zh��n)��������(g��)�x��һ��(g��)���ϲ�ʿ����һ��(g��)���ǿ���ʿ��������(g��)���ǿ���һ��(g��)�����ώ����Y���C���֛]�W(xu��)Ӌ(j��)��C(j��)���ܸ��������?y��n)��@��(g��)��Ӌ(j��)�Ć��}����������һ��(g��)��ʿ���������(hu��)�l(f��)�F(xi��n)�҄����x���@��Ԋ(sh��)�����кܶ��|�������f����(y��ng)ԓ��ô�ӡ���������ǰ�ϱ���ĕr(sh��)����һ��(g��)�dz���ؓ(f��)���ˣ��X���Լ�ʲô�����ԡ��Ǖr(sh��)���ҵĴTʿ��(d��o)�����f��â����Ը�(y��ng)ԓ������߅�����ѣ���ӛ�ߣ���(du��)������ϲ�ʿ��Ҳ���c(di��n)�����⡣�㱾������ȥ�^��һ�N�����������ĵ�·ꎲ��(y��ng)�e(cu��)�ؾ͔D���@һ�l���ˡ�
����������f�ģ��x��ʿʲô���Л]�н����ҫ�����|(zh��)�أ���������_ʼ�Ǜ]�еģ���?y��n)����p�ĕr(sh��)��������]����ô��(sh��)���������Ѿ��f�^��â���ڱ����^�ˌ���ʮ������w����������ƣ��Ⱦƣ����裬���壬�����ȫ�����@Щ��������һ���棬�@�N��ʽ�ČW(xu��)λ�������м�(x��)һ��Ҳ�Ĵ_���ҵĺܶ�涼?j��)���ס�ˣ������ҬF(xi��n)�ں��ゃ�fԒ���c(di��n)��ƈ��Ц�����c(di��n)�dz��ij���(w��n)���@Щ�|�������Լ���֪���X�γɵģ������ټ���������̕���������Ҫ����(w��n)�������@����Ҳ��һ��(g��)�ܺõď���������������̎̎�����⣬�ܶ��r(sh��)�����Ҫ�������һ�Kĥ��ʯ��ĥ���������Ͼ�������ʯ��ĥ�����Ї�(gu��)��(d��ng)��ˇ�g(sh��)���棬�����f���Ї�(gu��)�Ŵ����F(xi��n)����һ�ӣ�һֱ���@ôһ��(g��)�`�^(q��)�������˿�����ʲô�أ��Ҋ�ķQ�������f�ゃ�@Щ���Dz��ӣ��ڱ���Ҳ���@�ӣ�һՄ���DZ������ʲô�ġ������ҵĺ����Ѳ̺�ƽ��Ҳ�������z���������J(r��n)����һ��(g��)���͵IJ��ӣ����Լ��s�m���f�҂������J(r��n)����һ�f���҂���ʮ�����Մ�@��(g��)����ʮ���ֻ���f�l�Ė|�����ú��҂��ͷ��l������һՄ���Ї�(gu��)�F(xi��n)��Ԋ(sh��)���Մ����־Ħ��ͨ�^ͨ���Ļ��İ��b����������һ��(g��)���ӵĸ�����X���@���ڮ�(d��ng)��ˇ�g(sh��)�����ČW(xu��)�����������һ��(g��)�ܿ�Ц�ĸ���䌍(sh��)���f�������Dz���һ��(g��)���ӣ����϶��ǂ�(g��)��ţ�������һ������һ��(g��)�����đB(t��i)�ȣ�Ҳ��һ��(g��)��(y��n)֔(j��n)?sh��)đB(t��i)�ȡ�
��֮����(du��)�҂�(g��)�˶��ԣ��@һ��ȡ���ʧ��֪���Ǻ�߀�ljģ����ǚvʷҲ���@ôһ��һ�����^���ˡ����Լ��X������һ��(g��)��ì�ܺܛ_ͻ���ˡ����^���f�����@��(g��)�˵İ�����Ҳ���^��(qi��ng)����(du��)�ڸ��ɵĿ����Ҷ����w��(hu��)�������f�ČW(xu��)Ժ����Ҳ���w�(y��n)���W(xu��)Ժ����������ʲô���������^�����g����Ұ��һ�N�����͵�ˇ�g(sh��)����Ҳ�����ף��dz����ס����Է�����(d��o)�������ԷQ��һ��(g��)äĿ���x�ߣ������Լ������壬ÿһ����·�п����Ѓɲ��������������x��Ė|����
�Y �ƣ���â���x�ã���С�Ϳ��M(j��n)����߅��͌W(xu��)��(x��)�ܺã������ҵȶ��DZ�����ɽ�ϴ�W(xu��)�������f����һֱ���ڸ��Լ��Ը�ɵ��£��̕�ʲô�ġ���Ѫ������һ�N�����ׁ����������˵Ļ�Ѫ���䌍(sh��)�Ǻܲ����m���ˎ����ġ��㿴�����������^�֮����ϴ���Ҋ�����X������ȫ��һ��(g��)��Ƥ���@���ܷ�����һ�Ԋ(sh��)�˵Ġ�B(t��i)��������һ������������ǘӵ�Ԋ(sh��)�ˡ�������â�v������ʲ�ͽ�������}����һ�NԊ(sh��)�衱������҂����¼���ˇ�g(sh��)�]���P(gu��n)ϵ����(sh��)�H���҂�(g��)���X���Ǻ��Ў����ģ���?y��n)�����Լ��Ľ?j��ng)�(y��n)���ڏ���һ�Tˇ�g(sh��)�����r(sh��)������r(sh��)�g�������M(j��n)�����^�Į�(d��ng)����B(t��i)���F(xi��n)�ڵ��YӍ�ܰl(f��)�_(d��)�������f�̇�(gu��)��(qi��ng)��ʲô�������ʲô��������ϲ�g��ˇ�g(sh��)����ʲô����ܿ��܉�ľW(w��ng)�ϻ�����ý�w���˽����(d��ng)���˽�ĕr(sh��)�����ѽ�(j��ng)�ɞ������е�һ��(g��)���֣��ѽ�(j��ng)��֪���X�ؽ��뵽���^��(d��ng)��ˇ�g(sh��)�С��䌍(sh��)����ʲ��һ��(g��)������Ľ�(j��ng)�v��������20���o(j��)һ���֚vʷ�Ļʯ����(j��ng)�v�˶���(zh��n)���IJ��m�����������W�����ĵ؎������������(gu��)����(j��ng)�v�˺ܶ���������ġ��Z(y��)�Ե�������Ŀ����20���o(j��)һϵ���|Ŀ�@�ĵ�׃��������(g��)��(j��ng)�v�����Ͼ���һ��(g��)�Ļ�����20���o(j��)��һ�N������B(t��i)�ĿsӰ�������x��Ԋ(sh��)�裬�����Z(y��)�ԣ��o�Լ���һ��(g��)��λ�����Z(y��)��ӛ䛺����ȣ�Ҳ���^�����Һ������ĕr(sh��)�����@������â�����v���ĺ��ģ��ͮ�(d��ng)�����ˇ�g(sh��)��һ���A�εĕr(sh��)�����ѽ�(j��ng)���M���ڮ�(d��ng)�������M�����˽�ˇ�g(sh��)������Ը����@�ɂ�(g��)�|�����鹤�ߣ���(du��)�Լ��������͕r(sh��)�������^�����H�H���������С�������â�v������ʲ�Ѓ��c(di��n)ֵ��ע�⣺һ��������Ը������һ��(g��)20���o(j��)׃����ӛ��ߣ�����(n��i)�ĸ�ϣ�����Ї�(gu��)�Ŵ�Ԋ(sh��)��һ�ӌ��ǷN���ġ��P(gu��n)��������һЩ���������F(xi��n)��(sh��)�ֱ��������u�W�����Ă��y(t��ng)�����Ų����_(d��)���������x����(sh��)�H����һֱ���@�NĦ����(d��ng)���������Լ���һ���������������Ԋ(sh��)���ĺ��嵭��̹Ȼ�������f�����^�д�����һ��Ԋ(sh��)��60���q���ġ����x�����е�Ҳ�g�ɡ��Y���������Ժ������ɻ���X���@�ǿ옷��һ�죬���X�������ѽ�(j��ng)�]��̫��Ҫ�õ��ģ�Ҳ�]��̫��Ҫʧȥ�ģ����c���Ҷ���ӛ�ˣ����wҲ�]������ʹ��ֱ������߀�����{(l��n)ɫ�ĴͰ������������Ԋ(sh��)���ú�����������vʷ����С���鶼ҪՄ?w��)�����â�v����ʲ�����^��һ�NԊ(sh��)�裬�䌍(sh��)���ڸ��ߵĠ�B(t��i)��ȥҪ���҂���ˇ�g(sh��)��
��С�������������ǂ�(g��)���}�Ҳ�֪����ش��˛]�У�����˼��������ô���W(xu��)λ��(du��)��Ԋ(sh��)�Л]�����ã�Ҫ�ҁ��ش��@��(g��)���}���W(xu��)λ��(du��)��Ԋ(sh��)�϶�һ�c(di��n)���Û]�У����@�N��(j��ng)�v��(du��)��Ԋ(sh��)����(du��)ˇ�g(sh��)���b�p��һ�������á��ͮ�(d��ng)��F(xi��n)������P��Ҫ���ĕr(sh��)��(d��ng)�҂�����P��Ҫ���ĕr(sh��)����Ҫ��ʲô����Ҫ��ʲô�����醚v�����֪�R(sh��)���N(y��n)���㽛(j��ng)�v���^�̌�(du��)�㌑Ԋ(sh��)��(du��)����Pһ�������ã��������÷Ƿ���
����⣺��(du��)�����P(gu��n)�I���ҵ���˼���f������x������һ�N��ʽ��һ����Ҫ�x��W(xu��)Ժ���@�N��ʽ���W(xu��)Ժ�����Dz��܉���Ӗ(x��n)ˇ�g(sh��)�ң�ˇ�g(sh��)�Ҳ��DZ����B(y��ng)�����ģ���ֻ�ܽ̕�(hu��)������Ė|�������������@�ӵĖ|����
�� â���W(xu��)Ժ���@Щ�|�����f���������������㣬߀�����Լ�ȥ���^�@ôһ��������eһ��(g��)���ӣ���������(gu��)��(j��ng)���ͮ�(d��ng)?sh��)ص�һȺˇ�g(sh��)���ھư���Ⱦƣ��ҵ�һ��(g��)�炃����ʮ���q�ˣ���(du��)���f��������һ��(ch��ng)�Ӱ����������߀�ǿ����������Ҫ��������ġ��㽛(j��ng)�^���@һ�Ж|�������^���ǂ�(g��)��(j��ng)�v�T�ˣ���ĕr(sh��)�g���M(f��i)���ă��������M(f��i)�����܇Ҳ�����M(f��i)�����ڌW(xu��)Ժ��Ҳ�����M(f��i)���������湤��������ȥ̽�U(xi��n)ȥ���У�����������죬�Ⱦƣ�����һ�N��ʽ���ѡ�����fһ��(g��)ˇ�g(sh��)����ô���ͱ��h(hu��n)������ס���������f��ȥ�����@��(g��)�h(hu��n)����Ԓ���Ǿͷ��^���f��ˇ�g(sh��)�ұ���ijЩ���涨�������ǣ��������@��(g��)�W(xu��)Ժ���W(xu��)λ�����ǂ�(g��)�Α��������棬����f�_(d��)���@ô��(g��)�����Ԓ����ô�όW(xu��)���ÌW(xu��)λ��һ������ô��������飬�@�ǵ�һ��(g��)���ڶ���(g��)����Ҳ�ܷ���(du��)��һ��(g��)�^�c(di��n)����(d��ng)�r(sh��)�ڱ���ĕr(sh��)�ܶ��˾��fУ�@Ԋ(sh��)��ʲô�ģ����fʲô��У�@Ԋ(sh��)�ˣ��������Ԋ(sh��)���}Ŀ�С��ӽ�äĿ����1987����ģ���ЩԊ(sh��)��]��һ���P(gu��n)��У�@�Ė|�����Ǖr(sh��)���Ҍ�Ԋ(sh��)���÷dz�����ֵֹģ������������P(gu��n)���������ڵ�Ԋ(sh��)���W(xu��)λ�@��(g��)�|���ܶ��˶��Ђ�(g��)�e(cu��)�X���X�ÌW(xu��)Ժ�Ǖ�(hu��)���`��ġ����ų�С���f�÷dz���(du��)���W(xu��)λ��(du��)��һ�c(di��n)������Ҫ�����Լ��Į��I(y��)��Y�ҏā����]�����^��
����⣺�����f�����@��(g��)��(j��ng)�v��(du��)������Ӱ푣���(du��)������Ԋ(sh��)�˵�Ӱ��ж��
�� â���dz�������қ]���õ��@�ɂ�(g��)��ʿ����Ҳ�S��(hu��)�X���Լ��ʵǵĺ�Ų��㣬����ǰ�ĵ�ƽ���͛]�б����_���P(gu��n)�I�����f��W(xu��)�����ٖ|�����P(gu��n)�I�����ҕҰ���_�Ժ���߀�ж��ٖ|��߀��֪�����@��(g��)�Ƿdz���Ҫ�ġ�
�� ������������⣩����˼���f�Q��ɣ�~���³��Q�z�����DZ����f�ԗ���~�³�����߀�����Q�z�
�� â����Ѹ�����f�ҳԵ��DzݔD������ţ�̰������X���㑪(y��ng)ԓ�q�C�����@��(g��)�|�������ٽo���e�@ô��(g��)���ӣ�ʮ��ǰ���Sͤ�Ӿư�һȺ����Ԋ(sh��)�����Ѿە�(hu��)���Һ�����һλ�����壬��һλ���ѣ�һ߅�Ⱦ�һ߅���壬�f��������һλ�]���^ʲô���������r(n��ng)���S�˿���ſ��ꃱ�ij��(g��)ɽ��ĸG�����挑������������Ї�(gu��)�F(xi��n)��Ԋ(sh��)�����Ү�(d��ng)�r(sh��)��һ߅����һ߅��ʾ���h���f���@Ԓ�e(cu��)�ˣ��F(xi��n)��Ԋ(sh��)������ҪӖ(x��n)������Ҫ�W(xu��)�B(y��ng)�ġ��ҿ�����һ���۽z�������Ƴ�Ŀ��܂�(c��)������â���������ؙM���ߵ��@��(g��)�š����ǣ���һ��������@��(g��)�ط��Ƿdz��v���x���ġ������f�峯��܊������(gu��)���������ģ�����Ԋ(sh��)���˼ң����f�x����(du��)�����@�ӵ����Ƿ��K߀�Dz��Ƿ��K���@��(g��)���ܸ����y(t��ng)���P(gu��n)ϵ����?y��n)��҂��Ǻ���W(xu��)�ɣ������ˏ�С��������@ô��(g��)��(x��)�T���W(xu��)�����á��W(xu��)��(x��)����Ŀ�ĵ������회W(xu��)��(x��)���W(xu��)��ʲô�|���Ժ����ˌW(xu��)Ҳ���ԡ������ˣ�����Ҫ�@��(g��)�|���ˣ��Ҳ���Ҫ�@��(g��)�����ˣ����ˣ����ԡ���eđ�Ӳ������fһ�����ȣ��㲻������(d��ng)���ȣ��������(d��ng)���E��(d��ng)���Ӳ���ȥ���ݣ��Dz����������@Щ��(j��ng)�v��(du��)���ҁ��f�зdz���Ď��������²�����֪����̫�������֪���ò��ࡣ�҂�(g��)���J(r��n)��ˇ�g(sh��)��������һ�N��(du��)Ԓ��Ԋ(sh��)����������һ�N��(du��)Ԓ������ʲ��Ԋ(sh��)�������Ҳ��һ�N��(du��)Ԓ�������Ǹ��e�ˌ�(du��)Ԓ���Ǹ��Լ���(du��)Ԓ��ˇ�g(sh��)�Ĺ��ܲ���ˇ�g(sh��)�ҹª�(d��)������ˇ�g(sh��)���܉�����е��ˌ�(du��)Ԓ��
��С���� ᘌ�(du��)�㣨����⣩������Ć��}���fһ���ҵ��뷨����ˇ�g(sh��)��(chu��ng)��������f���W(xu��)λ�C���dz�����Ҫ����â�����p��ʿ���O�IJ��B�����đ{���]�У����njO�IJ���Ȼ�ǂ�(g��)���˲����Ԋ(sh��)�ˣ��������O�IJ����ā�]��ֹͣ�^�x�����҂���ʲô��ȱ���Dz�ȱ�����O�IJ��ě]��ֹͣ�^��x�����ⲿ�����ȡ֪�R(sh��)����ȡ��Ϣ�����ĹPӛ����X��������߀��Ҫ��ÿ��Pӛ����X���_���B�ό����M�������������Ҫ�������@�N������Ϣ�Ĕzȡ������䌍(sh��)�����Č����r(sh��)����Ҫ�ˣ���(hu��)�S��
��ٝͬ��â�f�Č�(du��)Ԓ���}�����B���Լ����]����(du��)Ԓ����֪����α��_(d��)���@��Ҫ��̝�ġ��Ҳ�ٝͬ����ӑՓ�r(sh��)�����D(zhu��n)����һ����f���Z(y��)�ԣ���ҕ�Xˇ�g(sh��)�Dz���Ҫ���Z(y��)��ȥ���_(d��)�ģ����۾��������ˡ������J(r��n)�鲻���@�ӣ����f��������Ĵ�(j��)������ߣ��������ġ��H�۵���W�������������ܵܵ�ͨ�������α��_(d��)�Լ����U���Լ����^�c(di��n)�ġ�һ��(g��)��(y��u)��ˇ�g(sh��)������a���Լ��ڌ�(du��)Ԓ�^�������U���Լ�����Ʒ�����ùP�����r(sh��)��������Լ�Ҫ�Ɇᣡ�҂����X���놖�}�r(sh��)���܃H�H�LjD��(g��u)�ɣ�һ��Ҳ��(hu��)���F(xi��n)�Z(y��)�ԡ�����֪�R(sh��)�����(j��ng)�(y��n)��ͯ����롭��Ȼ��˼�룬���@Щ�C�ϲŕ�(hu��)���F(xi��n)һ��(g��)�õ���Ʒ��������ì�ܡ�
����⣺ ���f�IJ����@��(g��)��˼�������@�ǂ�(g��)��Ԫ�������磬�����f��һ��(g��)�Ƕ������M(j��n)ȥ�����h(yu��n)�����@�ӣ������@�ӣ����ĽǶȿ��Էdz��Č��V���F(xi��n)��ˇ�g(sh��)����Ҳ�ǰ��@��(g��)����Խ�ӔU(ku��)����ǰ���^��ˇ�g(sh��)�]���@ô�V韣��F(xi��n)��ˇ�g(sh��)ʹ�ø��ӵ��_韣����Ƿdz���(f��)�s�ģ������Dz����A(y��)֪�ģ�����(hu��)�f����һ��(g��)�̶��ķ�ʽ������ijһ��(g��)���}���Z(y��)�ԵĆ��}��(sh��)�H�����Z(y��)�Ե���ȥ��Q������ҕ�Xˇ�g(sh��)���㲻���ܽ�Q�ıȌ��T���Z(y��)�Եĸ��ã���(d��ng)Ȼ�������һ����(hu��)׃��Ԋ(sh��)�ˣ�Ҳ����׃��Ԋ(sh��)�ˣ�������K���Q�Z(y��)�Ԇ��}�϶����猣�T���Z(y��)�Ե��˽�Q�ĺá���(du��)�҂����f���_(d��)�ķ�ʽ���_(d��)����˾Ϳ����ˡ�߀��һ�N��ʽ��������_(d��)���@��(g��)Ԓ�Ƿ������(n��i)���挍(sh��)�ķ���(y��ng)��߀��һ�N�ҿ�����̓�ٵĖ|��������(y��ng)�@��Ԓ��������J(r��n)�������ķdz��ĺã�����(sh��)�H��������(n��i)���Ǻ�̓�ٵģ��]�����x�ġ�
�� â�����f����ȫ��(du��)����(du��)Ԓ������ҫԒ�Z(y��)�����������f��һ��Ҫ�Ж|���������f�������˼��܉����ף������f��(du��)���a(ch��n)���dȤ������������������������f��һ��Ҫ��һ��(g��)�|�����V���磬�@�Ǻ���Ҫ�ġ����ڌW(xu��)Ժ�@��(g��)���i����Ը�ⱳ��ͱ������܉���@��(g��)���i��ҵ�������͌��ң����]��Ҫ?ji��ng)��؞��Ρ����f����������ǰ߅�f�ģ��Ҍ��ҵ�����һ�NԊ(sh��)�裬�㌤�ҵĿ�������һ�N�L������һ�Nˇ�g(sh��)����һ�N�Z(y��)�ԣ���һ�N���߰����ԵĖ|������?y��n)����ЏV韵ĵ�ƽ�����������Пo�Ŀ����ԡ�������ˇ�g(sh��)����һ��(g��)��(du��)Ԓ���҂�(g��)���J(r��n)���@��һ��(g��)��������?y��n)��������һ��(g��)��(du��)Ԓ���@��(g��)ˇ�g(sh��)����һ��(g��)�����Ԝ�Ė|����
�� �������X�Ö|��Ԋ(sh��)�˺�����Ԋ(sh��)����ʲô��һ�ӵģ�
�� â����(d��ng)����߀�ǏĹŵ������ԣ�
�� ��������Ŀ�е�ӡ����ǹŴ�Ԋ(sh��)�ˣ���(du��)��(d��ng)��Ԋ(sh��)��߀�����m(x��)�ǷNӡ���Ҳ�֪�������@�N�]ʲôҊ�R(sh��)���˿��|�������������c(di��n)��һ�ӣ�
�� â�����Ҿ��fһ��(g��)���Ǻ܌W(xu��)Ժ�ĽY(ji��)Փ�ɣ����X�Ö|��Ԋ(sh��)�˺�����Ԋ(sh��)����ijһ�c(di��n)���DZ��^һ�µģ������f��Ԋ(sh��)��Ŀ�������C��һ��(g��)�|����һ��(g��)�����C���������^����һ�����(y��n)�C�^�Ė|����������(y��n)�ˣ������C�ˣ��@һ݅���������@һ�c(di��n)�Ϳ����ˡ�
�� ������Ԋ(sh��)�nj����߀�Dz�����𰸣�
�� â��Ԋ(sh��)����Ҫ���Ҵ𰸵ģ����Ǹ���Ҫ�������܆���ʲô�ӵĆ��}���㆖��ʲô�ӵĆ��}������܉�?q��)���һ�N���õĴ𰸡�
�ײ��������X���Ї�(gu��)Ԋ(sh��)����δ����ʮ�����ʮ���(hu��)����(hu��)��һЩͻ�ƣ������ͻ�ƕ�(hu��)���Ă�(g��)�����ͻ�ƣ�
�� â���Ї�(gu��)Ԋ(sh��)��϶���(hu��)��ͻ�ơ������Ă�(g��)����Ȼ��ͻ�ƿ϶���ȫ��λ��ͻ�ƣ�����һ��(g��)�ӴΣ�һ��(g��)�_(t��i)�A��ȫ��ȥ���@��(g��)��(sh��)�^�Ǔ���ס�ġ���(sh��)�^�����ǃ��������w����һ������ʲô�ط����@��(g��)�����f���@��������C(j��)�����صĖ|����߀�У��@��(g��)ͻ�Ƶ��_(t��i)�A���τt�ѣ�һ�ϱ�Ȼ��ȫ��λ�ġ�ˇ�g(sh��)�^��(du��)�ǾC���Եģ��κκ����nj��T��ˇ�g(sh��)�䌍(sh��)�������һ�N�C���Ե�ˇ�g(sh��)��
��С���� ǰ���쵽�^�����_(t��i)��ˇ�g(sh��)���_����(du��)�̇�(gu��)��(qi��ng)������Щ���h���䌍(sh��)���@�ο����W�\(y��n)��(hu��)�_Ļʽ�ϲ̇�(gu��)��(qi��ng)����ǂ�(g��)�����ܺá�
�Y �ƣ������_�ࣩ�X�ò̇�(gu��)��(qi��ng)�柟���DZ��_(d��)�˟��������Ěg�c�����õĸ���]�б��F(xi��n)����ˎ����������Ѫ�ȣ����Ĵݚ��ԡ������Ե�һ�档�_����վ���@��(g��)�Ƕȿ��ģ���Щˇ�g(sh��)�����ṩ���ģ�ٝ��ʽ�ģ���Щˇ�g(sh��)�����ṩ����һ�N�|��������������Եġ��䌍(sh��)�@�ֻص���âՄ��һ�NԊ(sh��)��Ć��}����(sh��)�H��߀�nj�(du��)�Ї�(gu��)��(d��ng)��Ԋ(sh��)������f�������|��ˇ�g(sh��)�IJ��M�㣬������һ��(g��)������������Ҳ߀������һ�NԊ(sh��)�裬��ʲô�ӵ���߀��֪�������ѽ�(j��ng)��һ��(g��)�����ˣ��ǂ�(g��)���Ӿ�������ʲ��������ʲ���Dz����Գ��u�ģ���?y��n)����Ľ?j��ng)�v�䌍(sh��)�����и��]���p�ˣ��ゃ���������@��ȥ����ゃ���ܽ�(j��ng)�v���������҂���ϣ����������ã��M(j��n)��һ�N�����M(j��n)��һ�N���Ԯ�(d��ng)�У��Ϳ��Բ�ȥ���ǷNҊ�C�Ե�Ѫ�ȵĖ|������ϣ���ゃ?n��i)����������ǷNƽ�o�Ė|����������һ��(g��)�����؏�(f��)�ģ���Ҳ�Ќ�(du��)������Ψ��������Ҳ���ǷN��܌�?k��)o���Ї�(gu��)�ŵ�ʽ���ľ���B(t��i)�����@ǡǡ���������������IJ��֡��䌍(sh��)���@��(g��)�Ƕ��Ͽ���һ��(g��)Ԋ(sh��)�ˣ��Dz�������һ��(g��)ˇ�g(sh��)�Ҳ���Ҫ�ˣ��҂�Ҫ��һ��(g��)��Խˇ�g(sh��)���۹�ȥ����ˇ�g(sh��)����âҪ��(qi��ng)�{(di��o)��Ҳ���@��(g��)�|��������Ԋ(sh��)�����ݵ��ǷN���O(sh��)������Ը����һ��(g��)��������ȥ����������Ԋ(sh��)��ֻ��һ��(g��)żȻ�IJ��ۡ����ܵĠ�B(t��i)��ǡǡ��żȻ�ԲŴ��_ˇ�g(sh��)�ĸ��ര����Ҳ���Ǿ�����â�f�ĵ�ƽ���ĸ��o��չ�_��
�� â���҂�����һ��������һ��(g��)Ԋ(sh��)�˻��߮��ң�Ԋ(sh��)�˺ͮ������㵽һ���q��(sh��)�ĕr(sh��)��ŕ�(hu��)�x���һ��(g��)�|����Ҳ��һ��(g��)���ݵĖ|���������҂�(g��)�ˁ��v�����������_�W(xu��)�g(sh��)��(hu��)�h�ĕr(sh��)��Ͳ�Ը���f���Լ���Ԋ(sh��)�ˣ�ֻ�f��һ��(g��)�ČW(xu��)���ڡ����^���ڸ������_��(hu��)ӑՓ�Еr(sh��)Ҳ��(hu��)�^�τš��������˾ͷdz���(qi��ng)�{(di��o)�ı���(x��)�x�����~���䣬�����ٟ�������Ҿ��f����ȫ�����@��(g��)�ı�����Մ����ȫ����һ��(g��)��ˇ�Ć��}���Еr(sh��)��]ʲô��Մ�ģ���?y��n)��@Щ������һ��(g��)���w������Ԋ(sh��)���䌍(sh��)����߀���ס����҂���ͨ���䌍(sh��)��������һ��(g��)��ķ��档���X��������ˇ�g(sh��)��Ԋ(sh��)�衢�Ļ���Ԓ�}��K����(y��ng)ԓ������һ��(g��)����Ė|����һ�N�܉�˴˹�ͨ�Ė|���������f��ۺ�ʲô����ϲ�g��ʲô���㆖ʲô���}������ʲô��(m��ng)�룬Մ�@��(g��)���X�ø���Ҫ����?y��n)�����?sh��)�������Ć��}Ҳ��Մ�ˡ��@��������K��һ��(g��)����������
�Y(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