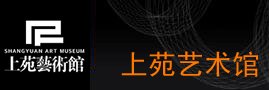|
哈金演講稿:為外語腔調辯護
[2008-9-28 7:38:11]
哈金演講稿:為外語腔調辯護
(明迪 譯)
英語的一個獨特榮耀是其相當數量的文學作品是由英語為后天習得而非先天所得語的作家所創作的。這些移民作家獨自進入這個語言,他們不同于身在原殖民地國家或來自原殖民地國家的作家,如印度和奈及利亞等,在那些國家英語是官方語言,民族文學也是以英文寫就的。這些非母語作家在這個語言中的掙扎、生存、取得的成就大多是個體的——其創作努力在短期內對集體的意義不大。然而,這并不等于否認他們和母語作家之間有相似之處和共同利益。
可以說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這一文學傳統的奠基人,而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則代表它的高峰。康拉德在這個移居國語言中的掙扎已眾所周知;即使在他的晚期小說里,盡管他語言凝練、文筆優美,我們仍然會偶爾碰到筆誤。相比之下,納博科夫一直被推崇為語言冒險家和技巧嫻熟的風格家。同樣眾所周知的是,他在閱讀俄語之前就學會了閱讀英語,他是在三種語言環境中長大的。環繞在這位大師頭上的光環容易掩蓋一個事實,即納博科夫類似于康拉德,在停止用俄語寫小說之后曾經不得不努力地掌握英文。 納博科夫對自己的掙扎相當坦誠,正如他在那篇著名隨筆《關于一本名為《洛麗塔》的書》中所述:“我不得不放棄我的自然語言——我那未經馴化的、豐富的、學無止境的俄羅斯語,而接受二流品牌的英語。”[1] 他在另一個場合坦白:“自然語匯的缺失”是他在英語里“作為一個作家的秘密缺陷”。[2] 即便如此,我們很少有人似乎愿意反思一下這位偉大的語言魔術師所經歷過的艱苦歷程。
 Joseph Conrad Joseph Conrad
不過,他的傳記作者布賴恩•博伊德(Brian Boyd)記錄下他最初幾年用這個語言寫作時的語言掙扎。納博科夫抵達美國兩年后寫下他最好的英文詩——《發現》。這首詩的靈感來自于他偶然發現自己捕到一只“大峽谷”,這只蝴蝶已作為此類物種的標本陳列在紐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里。盡管詩里充滿了自信而富有詩性的聲音和說話者的蓬勃精神,他的傳記作者仍然不得不評價道:“但此詩的謄清稿痛苦地顯示了他時而薄弱的英文。”[3] 這個“薄弱”可以在以下幾行里感覺到:“我發現它,并為之命名,精通/可分類的拉丁文;因而成為/一種昆蟲的教父和它的第一個/描述者——我不求其它名分。”博伊德還提到納博科夫和愛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之間就納博科夫的英文所作的早期溝通。威爾遜指責他的朋友過于大膽地使用移居國的語言。這位美國著名文人對這位剛開始在英語里探索的俄羅斯新移民的能力心存疑慮,并對納博科夫的雙關語和錯誤不斷挑刺。他們之間的摩擦最終發展為全面爆發的論戰——1965年威爾遜發表了他的長篇文章《普希金和納博科夫的奇怪案例》指出納博科夫翻譯《尤金•奧涅金》時所使用的“非標準語句”;作為回應,納博科夫寫下他的著名雜文《對批評者的答復》。此時,移居美國二十五年后的納博科夫已駕馭了這門語言,完全有能力與舊友辯論。他在這次辯論中勝出威爾遜。
然而,在他們早期有關納博科夫使用英語的私人交流中,威爾遜總是占上風,尤其是在納博科夫剛來美國的頭幾年。對于納博科夫而言,從俄語轉換到英語真是痛苦不堪;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像“在爆炸中失去七、八個手指后重新學會拿東西。”[4] 他還在巴黎時就開始撰寫他的第一部英文小說《塞巴斯蒂安•奈特正傳》。到美國后不久,他又繼續寫此書。當時,他對自己的英語還不夠自信,盡管他那華麗而細致的風格標志已體現在他的文筆中。威爾遜讀了小說樣稿之后,不禁稱好,甚至為書背寫了贊語。但他一如既往地對書中的某些小錯誤和奇言怪語吹毛求疵。他在1941年10月20日給納博科夫的信中寫道:“我希望你在威爾斯利學院找個人閱讀校樣——因為有些英文錯誤,雖然不多。”他接著指出了幾個。納博科夫在答復中遺憾地表示已將樣稿寄回出版社,無法再作更正了,但他也爭辯道,敘述者應該是“很吃力地寫英文。”[5] 換言之,語言上的缺陷帶有小說人物的特征,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合理的。事實上,小說的敘述者也承認了這一弱點:“同外國語言的枯燥搏斗以及對文學經驗的完全缺乏并不容易產生過于自信的感覺。”[6] 盡管作了技術上的辯護,納博科夫后來還是糾正了威爾遜提及的那些失誤。顯然,納博科夫對自己的英語能力感到憂慮,還得走很長的路才能成為英語寫作大師。反思這一點,很難想象從《塞巴斯蒂安•奈特正傳》中相對簡單的文筆,發展到《洛麗塔》中豐富而含蓄的語言風格,再發展到《普寧》中充滿信心的玩耍、對英語的故意誤用和蓄意歪曲,他下了多大功夫。
 Vladimir Nabokov Vladimir Nabokov
盡管威爾遜對他的朋友納博科夫慷慨大方,但他同時也使納博科夫頭痛。無論私下或公開他都不愿停止告誡納博科夫避免使用雙關語。所幸的是,納博科夫忽略他的不滿,繼續玩文字游戲,這種方式逐漸演變成他的天才標志。威爾遜在《紐約客》上發表了一篇對納博科夫的《尼古拉•果戈理》(1944年)毀譽參半的評論,他說:“[納博科夫的]雙關語極其可怕。”[7] 從他們之間友誼的一開始,威爾遜就把納博科夫同康拉德相比,他在1941年10月20日的同一封信中寫到,“你和康拉德恐怕是僅有的在英語和這個領域中取得成功的外國人。”納博科夫對這個比較不滿意,但我們不清楚他最初是以怎樣的措辭和方式來反對的。威爾遜當然知道如何激怒他的朋友。很多年以后,威爾遜把原《紐約客》評論縮短成《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對果戈理的研究》以納入文集《經典與商業之作》(1950年)時,在該文章結尾加上這樣一句:“盡管有些失誤,納博科夫先生對英語的精通幾乎超過了約瑟夫•康拉德。” 納博科夫覺得受到羞辱,回擊道:“我抗議最后一句話。康拉德處理現成英語比我在行;但我在另一方面比他強。他在使用非傳統句法方面沒有我陷得深,但也沒有達到我的語言高峰。”[8] 納博科夫所說的“現成”是指常規。在1964年的一個采訪中,他對此闡述得更加明確:“我不能忍受康拉德的紀念品商店式的風格、以及瓶裝船和蜆殼項鏈式的浪漫主義陳詞濫調。”[9]
我舉出納博科夫對康拉德的英語所作的負面言論,以期說明兩位大師對移居國語言所采取的不同對策。在康拉德的小說中,我們可以感覺到一種由英語字典所界定的語言邊界——他不會創造那種會使英語耳朵感到陌生的文字和詞句。除在極少數的海洋故事里, 如《“水仙號”船上的黑水手》和《吉姆爺》,有些船員的對話偶爾是不規范的英語,總的來說康拉德始終維系在標準英語的邊界內。我這么說并不意味著貶低康拉德的成就。即使在這樣一個邊界內,他設法寫出了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外,他把一種明晰的、外國人的敏銳帶入他那具有力度而優雅的行文中。他把自己看作是在英格蘭“避難”的外國人,這一點在當時不是什么秘密。“避難”這個詞——指他自己的狀況——幾乎成為他書信中的口頭禪。當他拒絕英國政府授予的騎士頭銜以及劍橋和耶魯等幾所大學授予的名譽學位時,他甚至聲稱英國文學不是他的傳統。晚年時他常常渴望回到波蘭,但他的突然去世使這一愿望未能實現。[10] 我們可以推測,康拉德對英語的嚴格遵守和他對自己在英格蘭是一個外來者的感覺——盡管這是他熱愛的國家,這兩者結合起來是他痛苦的根源。
類似于康拉德,納博科夫也嚴重地依賴詞典。當他成為一個風格大師時,他的英語變得更為藝術性的彬彬有禮和書卷氣。然而,他從不把自己局限在標準英語里,而是經常把這個語言的邊界向外推移。勒蘭•德•拉•杜蘭塔耶(Leland de la Durantaye)對納博科夫為什么采取這種方式的原因總結如下:
納博科夫喜歡用生僻詞來代替已經被發明的代名詞。對他來說,只有在真的沒有文字去為某件事命名、而且他花了足夠時間去證實之后,才允許發明詞匯。但這種保守主義是有限度的。對于現存的詞匯,納博科夫尊重它——但他為將其置于不同的詞語搭配而不遺余力,從這方面來說他遠非保守……納巴克夫與他筆下的人物塞巴斯蒂安趣味一致[從不信任簡易的表達形式]……他和塞巴斯蒂安一樣,“不使用現成的詞組因為他想說的事情是特殊材料建成的,而且他知道,除非有專門量體裁身而定制的詞匯來描述,真正的思想不可能說是存在的。”納博科夫的語匯衣裳是用他發現的語言布料制作的——但總是需要特別裁剪。[11]
以上引文的第二要點意味著“尋找新的詞語組合。”這是納博科夫的原則,他在整個寫作生涯中,無論是在俄語還是英語里,都照此實踐,而發明新詞則是一個更為謹慎的舉動,前提是對整個英語詞匯的認知。納博科夫是公認的“詞典狂”——他可能會愉快地接受這一稱呼,他對自己鉆研詞典所取得的學問感到自豪。那張有著他和他那本快翻爛了的巨象大的韋氏詞典的著名照片見證了他為精通英語所下的苦功。[12] 事實上,即使是韋氏詞典也沒有對他構成一個邊界,而更像是一幅地圖,因為他會毫不遲疑地創造新字和新的表達方式,如果詞典里沒有的話。舉例來說,在他的小說《普寧》里我們遇到這樣一些詞:“收音機迷(radiophile)”、“心理蠢貨(psychoasinine)”、“腳注麻醉狂”(footnote-drugged maniac)。就連他的第一本英語小說里都包含了發明的詞匯,如“愛的余燼(love-embers)”、“性管樂字條(a sexophone note)”、“朝傾斜的方向(tipwards)”、“思維形象(thought-image)”。 除了詞匯創造以外,也偶然有一些英語、法語和俄語之間的互換,這發生在英語的邊界之外。有時候《普寧》的敘述者干脆講俄語,普寧前妻麗莎的感傷詩以俄語出現,然后譯成英文。[13] 顯然,納博科夫與康拉德不同,他在英語語言的周邊寫作,其前沿延伸到外語領域。
《普寧》是一部重要的移民小說。也許因為主人公是一個白俄流亡者,讀者可能會忽略普寧也是一個移民,而且,同成千上萬的移民一樣,他面臨同樣的挑戰——在這個國家尋找家園。故事結尾時,他逃離威戴爾學院,消失在美國的荒野之中,那里似乎仍有一些希望,正如這個美麗的句子所提示:“[普寧的]小轎車肆無忌憚地沖上了閃光的道路,可以隱約看出這條漸漸變窄的路在薄霧中成為一條金線,連著綿綿群山,美化著距離,根本沒法預料那邊會發生什么奇跡。”(同上,191頁)。美國希望,雖然幾乎被小說里的悲傷和諷刺所打破,仍然在遠方土地上的自由空間里徘徊不去。確實,不同于少數族裔作家所寫的小說,《普寧》沒有涉及主要的美國主題之一——種族,但類似于歐洲移民所寫的小說,它描繪了新來者在這個國家所經歷的折磨和沮喪。此外,這部小說抓住了移民經驗中的根本問題,即語言。不管普寧如何努力,一旦他可以流利自如地甩出習慣用語,比如“一廂情愿”、“好吧,好吧”、“長話短說”,他那不完美的英語就無法再提高了。在使用移居國語言時他顯得那么傻、怪異,以至于他的一些同事認為他不應該有權利在校園附近走動;但當他說俄語和跟俄國同胞來往時,他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博學、語言流暢、甚至強壯有力。他的困境是第一語言并非英語的移民所遭遇的典型困境。
從技術上來說,納博科夫面臨著大部分有移民經驗的作家都必須面對的兩項挑戰。第一是如何呈現非母語族群的各種不同的英語,第二是如何用英語來表現他們的母語。在實踐中,第一項挑戰通常有經驗基礎,因為大多數時候作者可以模仿某個人物的口音和不合文法的話語。在這方面納博科夫處理得非常老道。普寧請托馬斯•韋恩教授去他家參加喬遷之喜聚會,他這么給他指路:“托德路999號,非常簡單!在路的最最末端,和克里夫大道交接處,一座小磚房,一個很大的黑色的峭壁。(It is nine hundred ninety nine, Todd Rodd, very simple! At the very very end of the rodd, where it unites with Cleef Ahvnue. A leetle breek house and a beeg blahk cleef.)”(同上,151頁 )。從語法上講他說的話無可挑剔,與普寧的書卷氣個性相吻合,但口音很重,因為他發不準某些元音。他說話和大多數同時又有語法毛病的移民不同,那些移民中有些人連一個復雜的句子都幾乎表達不出來。在小說寫作中,盡管有實際經驗的基礎,作者在表現英語為非母語人物用英語講話時不可能完全是自然的,但對話必須處理得好,給人以真實的印象。如果一個男人,如《上帝吹動的羽毛》中的瓦迪姆,對他心愛的人說:“當你把頭放在我胸口時,我的心跑出來了。”[14] 我們可以看出他是個外國人,因為他獨特的習慣用語使他的身份真實化了。這一技術上的要求排除了標準英語,因為標準英語不適合用來表現這么多被英語為非母語者所使用的各式英文。
第二個技術性挑戰更為復雜——如何用英語來表現外語。首先,一旦用英語寫,這種表現是沒有什么經驗基礎的,因為英語不可能和外語原來的發音相似。第二,敘述語言和對話語言是有區別的;從理論上講,前者可以像正式翻譯那樣只限于標準英語。從本質上看,作者面對的是英語和一門外語之間的相互作用;理想的話,英語在這種情況下應該一定程度地反映另一門語言。就對話部分而言,我相信很少小說家反對這個原則。因此,如果《水泥基督》中的新寡婦感嘆道:“我的孩子們應該尋求誰呢?誰現在會把食物放進我那些小鳥兒張開的口中?——因為他們必須活下去,在這片吞噬了他們父親的土地上長成高高的梁柱——我必須活著,他們才能活下去!”[15] 我們知道她說的是意大利語。這種不尋常的詞匯和別扭句法是為了使英語陌生化一點,以適應人物和劇情。實際上,這種做法是強迫英語接近另一個外語,使對話更加有特色。結果,英語不得不變得有些異化。不過,在美國移民小說中,這是一種常規技巧。而敘述語言則使兩種語言之間的相互關系更加復雜化。
正如我以上所述,從理論上講有可能將敘述語言限制在標準英語內,但在實踐中許多非母語作家不這樣做。這主要是由于兩個原因:第一,作家的母語和外語敏感性影響其英語,使本土讀者讀起來感覺不一樣;第二,標準英語不夠用于表現作者描述的經驗和想法。納博科夫知道這些不利因素,但有利地使用了它們。在《普寧》里,敘述者講笑話、故意扭曲英語單詞和成語,把“簡潔的履歷表(a curriculum vitae in a nutshell)”稱為“椰子殼(a coconut shell)”,在狀語詞組“另一方面(on the other hand)”后面跟了一個“第三手(on the third hand)”。敘述者這么做等于是突出了他的外語腔調,因為帶著兒童眼光看待英語的外國人更容易對移居國語言的大多數習以為常的特征產生這樣的奇思怪想。在美國小說中,甚至有些非人物化的敘述者在以第三人稱敘述時也不得不在語言中保留一些外語腔。舉例來說,《水泥基督》的敘述語言大量地依賴被動語態,這恐怕是用來反映意大利移民的說話方式。再舉一個例子,敘述者這么描述從浴室里傳出的噪音:“樓上的衛生間咆哮如雷地沖著水,在通暢的管道里噼里啪啦地咕嚕下來,在空洞的金屬喉嚨管里滴滴嗒嗒”(同上,42頁)。我們可以看出他說的不是母語。
 Ha Jin Ha Jin
去年冬天當我的小說《自由生活》出版后,約翰•厄普代克在《紐約客》上作了評論,并列舉了一些語句作為“小違規例子”。[16] 中文媒體廣泛報道了這篇評論,因為厄普代克在中國被尊為美國著名文人。互聯網上有一些關于厄普代克列舉的詞語的討論,但懂英文的中國人看不出那些用法有什么不妥。人們提供不同的解釋,但都沒有說服力。事實上,如果你每到一處都遇上對官場和職位極度關注的人,你怎能說用“官迷(emplomaniac)”這個詞不恰當呢?這樣的詞語也許使英文耳朵覺得陌生,但在中國語境中它是唯一合適的詞語。輕微一點的詞可能是“職位追求者(office seeker)”,但它未表達出過分在意和瘋狂。
一旦我們在小說中進入外國領土,標準英語可能不得不延伸以便覆蓋新的版圖。最終,這是一種擴充語言能量的方式。
中國人里面也有一些對我使用英語方式的誤解。人們常常說我直接翻譯漢語成語。這是不真實的。我確實使用了相當數量的漢語成語,因為我的人物大部分講漢語,但我在每一處都把成語作了些改變,有時候改動很大,以適應語境、劇情、和敘述的流暢。中國成語說一個男人自不量力地夢想一位漂亮女人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我在小說里至少用了兩次這個成語,但我是這樣表達的:“癩蛤蟆夢想擒天鵝”。“肉包子打狗”是一個漢語成語,指沒有好結果的冒險,我把它這樣變成英文:“用肉丸子打狗——沒有回報”。大多數時候我根據故事的上下文來剪裁成語。
另一項批評是,我的英語太貧乏、太簡單。用一位英語教授的話來說是“四級”, 也就是本科水平。在這個例子里,那些中國人把標準英語看為準繩——50美金的字你用得越多,你的英文就越好。他們未能理解像我這類的作家不是在字典的范圍內寫作。我們在英語的邊緣地帶、在語言和語言之間的空隙中寫作,因此,我們的能力和成就不能只以對標準英語的掌握來衡量。
除了技術上需要一種獨特的英語之外,還有對身份的關注。我經常強調,一個作家的身份應該是靠寫作獲得的。事實上,身份的一部分也可能是賦予的,超出了作者的控制。就在幾年前,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中有一種普遍的共識,認為離散作家中用漢語寫作的屬于中國文學,用其它語言寫作的屬于外國文學。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世界文學中的一部分作家有雙重國籍。康拉德既屬于英國文學也屬于波蘭文學,雖然他從未用母語寫作過。納博科夫也是一個俄羅斯作家,盡管他堅稱自己是美國作家。不過,最近有中國學者已經開始談論如何將那些用移居國語言寫作的離散作家納入中國文學經典。對于個體作家來說,分類可能不那么重要——最多就像在另一個大樓里有一個額外的房間,因為在世界文學史中,沒有一個有份量的作家是沒有歸宿的。但大多數寫過有分量作品的移民作家,其命運是被一個以上的國家承認,因為他們存在于國與國之間的空間,那里是不同語言和文化交織并互相滲透的地帶。在這個邊緣地區出現的任何有價值的作品很可能會被一個以上的國家認可,用來提高該國的軟實力。
大多數處于邊緣地帶的作家都清楚自己身份的雙重性。甚至連出生于美國、英語為第一語言的湯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都認為自己的作品是中國文學的延續,正像《女戰士》中的主人公在書的結尾處贊美的那樣:“[蔡琰]從野蠻之地帶回歌曲,流傳下來的三首之一是‘胡笳十八拍’,這是一首中國人用自己樂器伴奏所唱的歌,可以譯來譯去。”[17] 在一次訪談中,湯亭亭告訴詩人陳美玲(Marilyn Chin)她遇到一些中國作家的情景:“我在美國這里,有自由言論和出版自由。我用一輩子的時間寫我的根。所以他們[中國作家]說我是他們的延續。他們希望幫助搞清楚往哪里去……哎呀,我感覺真不錯。因為他們告訴我,我是中國經典的一部分。而我在這里是用英語寫作的。”[18] 湯亭亭雖然忽略了中國作家的外交辭令和政治頭腦,但對于被祖先土地上的人們接納而表達了由衷的興奮。跨越語言邊界、返祖歸根的愿望在美國少數族裔作家群體中很常見,但恐怕并沒有回歸之路。如果我們對此保持理性,就可以看到,大部分處于中間地帶的作家已或多或少被疏離或排斥。他們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充分利用他們的不利條件和邊緣化,而不應該死抱著回歸的夢想。他們什么也不應該依靠,只依賴可以給自己定位的有價值的作品就行了。由此而來,只要寫出有分量的作品來,身份這個概念也許就毫無意義。
在移居作家看來,邊緣是他們的工作空間,這對于他們的存在來說比其他區域更加重要。他們不應該努力去加入主流或在一個民族的文化中心占一席之地。他們必須保持他們的邊緣化,獲取各種資源,包括外國的資源,充分利用自己的損失。他們應該接受自己的邊緣化,正是這個邊緣化使他們區別于本土作家,成就他們獨特的抱負。
T.S.艾略特(T. S. Eliot)在《小吉丁》一詩中這樣界定詩人的使命:“由于我們關注的是話語,而話語促使我們/凈化本部族的方言”(第二部分,第126至127行) 。不過這是本土詩人的使命,正如艾略特住在倫敦一樣,他們可以呆在英語的中心,并努力完善母語。但是這種設想對外來作家是不合理的,也不適用于許多其它種類的作家。前英國殖民地的大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當地方言,盡管他們把英語作為民族語言。大多數美國移民不得不在家里說外來語或者不規范的英語。因此,讓外來作家抱有T.S.艾略特宣告的那種雄心是行不通的。實際上,過多的凈化會弱化一種語言的生命力。眾所周知,英語的活力和流行主要取決于它的非純潔性和混雜狀態。
 Salman Rushdie Salman Rushdie
同移民作家一樣,前英國殖民地作家以及寫美國移民經驗的作家都很敏銳地知道如何使用不同的英語,以區別于本土作家。薩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他的《想象的家園》一文中大篇幅地談到印度作家同語言的搏斗:“我們這些使用英語的人,盡管對其含糊不清,還是使用,或者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我們能夠在語言掙扎里找到反映我們自身其它掙扎的一種折射,以及作品對社會的影響。征服英語的過程可能是自我解放、獲得自由的過程。” [19]拉什迪把使用英語描繪成既是內在也是外在的斗爭,斗爭的勝利將把作家從殖民地遺產的局限中解放出來。很顯然,他設想了一種英語,它不是傳統用法而是能夠用來表達殖民地經驗、地方性,和印度生活的特殊性。所以,這樣的語言還尚待發明。
在美國出生的移民作家中,尋找一個新的英語似乎是與自我發現和個人身份認同有關的個人努力,也許是因為有這么多的移民族群,不可能形成一個統一的力量。大衛•村(David Mura)對此的評論體現了這些作家通常所持的立場:“那么,訣竅就是寫出我的雙重感,或者多元性,而不是去盲目模仿歐洲傳統而是利用它并把它同我自身背景的其它元素結合起來,盡力去達到一種艱難的平衡。為了解我是誰以及我想成為誰,我不得不聽從我父親、T.S.艾略特或羅伯特•羅威爾不曾夢想過的聲音,這些聲音來自我的家庭、或日本、或我自己任性而未同化的過去。在傳統世界中,我是沒有被想象的。我得把我自己想象出來。”[20]
這是一種對待英語的個體方式,但也可能代表了其他許多人所共有的見識,尤其是被這樣一些作家所認同——他們出生于這個國家、書寫美國化的經歷、不得不尋求一個不同于在學校里所學的語言。
 Chinua Achebe Chinua Achebe
我個人認為奇努阿•阿切貝(Chinua Achebe)對這個問題的立場是明智而更為可行的。六十年代初期,《崩潰》出版后,非洲作家中關于英語的使用發生了激烈的辯論。阿切貝是辯論的主要參與者,并寫下數篇文章討論這一問題。以下這一段概述了他的立場:
對于一個非洲人來說,用英語寫作不是沒有其嚴重挫折的。他經常發現自己描述的情形或思維模式在英文生活方式里找不到直接的對等之處。處于這種困境中,他可以在以下二者中選擇其一。他可以嘗試把自己想說的東西限制在傳統英語之內,或者嘗試推開這些界限以創造條件來表達自己的思想。第一種方法產生技巧嫻熟、但缺乏創意并且乏味的作品。第二種方法產生一些新穎的、對英語語言以及試圖呈現的新材料都有價值的東西。但也有可能無法駕馭,可能導致糟糕的英語被接受并被辯護為非洲英語或奈及利亞英語。我提議那些能夠擴大英語的邊界以容納非洲思維模式的作家必須通過對英語的精通而非出于無知才這么做。[21]
阿切貝所說的至關重要,不僅對非洲作家如此,對于獨自來到這個語言的移民作家以及那些有美國移民經歷并尋找一種語言來表現出筆下人物的情緒和思想的作家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基本上來說,阿切貝描述的第一種方法類似于康拉德的做法,而他建議的第二種方法接近于納博科夫的做法。阿切貝的“擴大英語的邊界”、“通過對英語的精通”等用詞指出了一個邊緣地帶,我們在其中寫作,并清楚其邊界以推動和擴大英語的界限。事實上,他還提倡責任意識,即豐富我們共享和使用的語言。
的確,英語的邊界臨近外國領域,所以對母語者來說,我們不可避免地聽起來有外語腔,但邊界是我們唯一可以生存并對這個語言作出貢獻的地方。
(本文為2008年4月4日哈金在布朗大學“全球化時代重估外語教學大綱”研討會上的主題演講,明迪 譯。)
注釋:
[1]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洛麗塔》(紐約:伯克利圖書,1977),第288頁。
[2]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強烈觀點》(紐約:馬格洛-休斯出版社,1973),第106頁。
[3] 布萊恩•博伊德,《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美國歲月》(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1),第53頁。
[4]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強烈觀點》,第54頁。
[5] 《親愛的班尼兔,親愛的沃洛迪亞:納博科夫—威爾遜通信集(1940-1971)》,塞門•卡爾林斯基編(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2001),第56-57頁。
[6]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塞巴斯蒂安騎士的真實生活》(紐約:新方向出版社,1941),第101頁。
[7] 博伊德,《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美國歲月》,第78頁。
[8] 《納博科夫—威爾遜通信集》,第282-283頁。
[9] 《強烈觀點》,第42頁。
[10]茲德茲斯洛•內達爾,《約瑟夫•康拉德:編年記》(羅格斯大學出版社,1893),第489頁。
[11]《風格即實質》(康奈爾大學出版社,2007),第142頁。
[12]博伊德,第562-563頁。
[13]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普寧》(紐約:溫特紀圖書出版社,1981),第56和181頁。
[14]思格里德•紐餒茲,《上帝吹動的羽毛》(紐約:哈珀科林斯出版社,1995),第147頁。
[15]皮耶特羅•迪•多納妥,《水泥基督》(紐約:斯格奈經典出版社,1993),第42頁。
[16]《紐約客》,2007年12月3日,第101頁。
[17]湯亭亭,《女戰士》(紐約:溫特記出版社,1976),第209頁。
[18]《與湯亭亭對話》,保羅•斯肯澤和特拉•馬丁編(密西西比大學出版社,1998),第94頁。
[19]薩曼•拉什迪,《想像的家園》(倫敦:格拉塔圖書,1991),第17頁。
[20]大衛•村《變成日本人:一個第三代日裔的回憶錄》(紐約:大西洋月刊出版社,1991),第77頁。
[21]卡魯•歐格巴引用于《理解“崩潰”》(康州西港:格林伍德出版社,1999),第193頁。
(原載《中國圖書評論》2008年第9期)
查看9512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