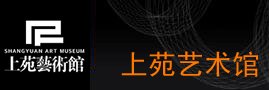蕭開愚詩二首
《這不是一首詩》
這不是一首詩。
我不愿工人和農民讀我的詩,
尤其不愿下崗工人和沒錢看病的農民讀我的詩,
我的漂亮的語言會迷惑他們,耽誤他們,
他們得趕緊去什么地方要求幾塊錢的福利。
我深知,現在,越美麗越可恥。
極少數人心曠神怡(包括頹廢和倦怠)不是出自狂妄地搶劫他人和公眾,
就是出自殘忍地搜刮自身(什么呢?)。
我寫過詩,還在寫,但不為老實人、君子、尤其不為農民兄弟,
他們得趕緊去什么地方要求幾塊錢的保障。
我羨慕聰明人的聰明、勤快人的勤快,
我也神往笨人的笨、懶人的懶、酒鬼的長醉
和夢游人的大夢不醒,
我不能再用我的笨和懶、醉意和夢境
更不能用我的痛苦或神來之快去拘絆他們,
他們得趕緊去什么地方要求幾塊錢的權利。
他們的當然的最低福利、最低保障、最低權利。
真的,還不是什么選舉權,而是那些“知識精英”千方百計要悶死
在窮人們的腦子里的一個社會:他們可以去要求幾塊錢。
所以這么多人絕望地讀詩,在詩里搜找。
這不是一首詩。
我不為不享受社會保障的人寫詩。
我請求所有非法地衣食無著的人不讀我的詩。
但是,為權貴和暴發戶,那些私分銀行、國土和房屋的大爺,
為那些為可能由這些大爺資本湯換而來的什么民主制烹調什么理由的“知識精英”,
我獻上我的--不是不屑,而是詛咒。
《跟隨者》
1
我在房間里枯坐著,
卻從一個城市到了另一個,
我已經在四個鎮、三個城
贊頌過臥室和女人。
那些油污的市政工人
在街頭奔忙、奔忙了一生,
卻只是從一條街回到
下水道相連的另一條。
我的鄰居熟悉我的命運;
在一個小房間里奔波。
他們在兩公里以內生活
靜而又靜,像一把鐵釘。
2
元旦夜,干燥的空氣閃亮著禮花。
我指揮滴水抹布,把貼身文件
(報復性睡眠的那些理由)搬進新家。
衛生間,廚房,小書桌,大臥室
收拾成習慣的樣子;文件放進書柜;
壇壇罐罐如同海軍在甲板上站好,
整齊而困倦。出門時
我發現,我不僅帶來了
老鄰居,還帶來了廢話和不衛生習慣
帶來了一群市政工人。
半夜時分,天空停止了嘔吐,
新村樓房像是一堆堆嘔吐物,
我回家和幾個淺色襯衣的夜游人
從一個街頭角走向另一個
街心花園里
白色龐大的肉蟲遲緩地蠕動,
他們翻身,打呼嚕,講夢話。
街燈以它零星悲哀的光線
裝扮他們(美夢的寵兒們),
突出他們中間新人可笑的催眠的數字。
我感到這次搬家又不成功。
3
是老關系來到了新地址。
告訴我暴雨的消息,他們說
買了新雨衣,而下水道
不會在天空大怒的時候進行抵抗。
但是夏天,他們認為,應該
盡量呆在二樓,離窗戶遠點兒,坐著。
把昨天和今天的交易繼續。
4
于是有了一些理由
搬家,搬呵,搬呵,
頻繁欣賞身體的病態
津津有味地沉默。
而且唱小曲回報這個社會,
帶著一群市政工人。
他們不憤怒但是說下流話,
他們就是他們的標準。
他們就在最近的小街上,
轟鳴著:電鉆刺進城市的水泥皮膚,
鐵锨啃城市的水泥骨頭。
城市又聾又啞,
地下管道挽留腐爛的一切,
地下管道的秀美的狹小
就像血管硬化的栓塞
召喚市政工人的手術刀
他們切斷鐵管,鋼管,水泥管
迫使它們讓位于大一號的管道。
他們迫使整個街區停水,停氣
停止洗澡和喝茶,
他們迫使我們注意他們,
回想他們,半年前
他們才迫使我們繞道而行,
迫使我們想起他們的兒子已經接班,
他們是市政工人。
而我們的出路就是搬家,
搬啊!搬啊!
當我們拋棄多余的東西
木椅,字典,摯愛,
生命好像有了一點意義。
當我們拋棄身體的時候,
(我們乘過的飛機都腐爛了)
也許有人會點一點頭。
而市政工人還在街頭上
挖啊,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