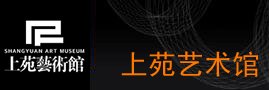由Paint Thru Gallery(新加坡)、北京尚愛藝術中心主辦,北京金螳螂藝術中心協辦的“第四屆復活節藝術展”,將于2009年4月12日和4月18日分別在二十一世紀劇院(北京國際教會)和金螳螂藝術中心舉辦, 此展由來自中國、德國、美國、泰國、 韓國等國家的藝術家參加,共展出油畫、水墨畫、裝置、雕塑、影視、圖片、書法藝術作品140多件,藝術家結合自身對生命、環境、真理的理解與感受;從不同的視角,運用不同的藝術語言 摒棄當代藝術中邪情私欲對人的束縛與捆綁;讓藝術從屬世的敗壞、污穢、邪情私欲的捆綁中分別出來;重塑當代人對“崇高感”和“精神價值感”的認知;將生命的更新與蛻變,破殼與飛翔的精神實質,用藝術形式展現出來;促使人們從有限的“人文關懷”,轉化并提升為對“終極關懷”的關注;倡導真、善、美的“圣藝術”理念,以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為果實;弘揚愛與和平,建造和諧、潔凈的藝術環境。
白野夫 曹原銘 常磊 陳均 陳克 陳勇 島子 丹楠 恩伯 范撲 付山丁 付瑤 格瑞德 郭超 郭詠紅 韓勇 韓濤 何金陽 何綺蘭 黃河 賈宇然 姜筱蓉 金春鶴金龍杰 金錫煥 李春光 李亞松 李瑩 李營 李洵求 李正在 李燕玉 李育勤 梁瑞華 劉彬 劉鴻良 劉美萍 盧仕洋 呂巖 羅必武 羅菲 羅華江 麥志雄 寧遠樸成哲 齊求實 秦嵐 冉勁松 阮藍慶 撒母耳 卲偉良 斯蒂夫 蘇碧蓮 唐子硯 田悅 汪楚雄 王愛琴 王華祥 王連鄭 王賽 王思丁 王曉宏 王興文 王彥芹 王玉山 王增瑞 王志友 旺忘望 衛林 楊飛云 楊光濤 葉芳芳 禹相浩 夏喜智 夏雨 徐敏 英德 臧純 朱春林 張聰 張帆 張煬 張家瑞 張建波 張立君 鄭壽卿 章暄晗 趙樂琳 趙麗仙 趙燕峰
中國當代基督宗教藝術的復興
島 子
廣義的基督教(Christianity)傳入中國,始于唐貞觀九年,即公元635年,于公元781年于長安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留下以十字架為屬靈標志的書法碑刻作品,現存西安碑林博物館。斷續而在13世紀“也里可溫教”作為“景教之維緒”在元朝傳播,耶穌會士先后于14世紀明代萬歷年間和17—18世紀(清)來華傳教,以及1807年倫敦傳教協會的馬禮遜教士將新教傳入,形成了基督教中國傳教歷史時斷時續的四次高潮。不幸被圣約翰所言中,“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卻不接受光。”【1】明清兩代的耶穌會傳教士只能以文化適應主義和宗教雜糅主義曲折傳道,如利瑪竇、湯若望、艾儒略、南懷仁等,而清宮傳教士畫家最終僅以傳播西洋繪畫知識和技巧為宮廷服務為己任,如耶穌會士郎世寧、王致誠、艾啟蒙和安泰的寫實油畫以及為清廷表記戰功的銅版畫,以及為圓明園設計奢華的西洋樓景觀,變成大水法專家的天文學家蔣友仁,他們往往被清帝視為“洋才”獲三、四品官位而享有俸祿,從根本上來說,他們的宗教心靈并不自由,即便是啟蒙主義的藝術審美情感也并不自覺,乃至背離了“榮神益人”的基督精神【2】。因此歷史的命運一再黯淡,普世的公義難能如江河滔滔,澆灌這個亙古匱乏神恩的“神州 ”。
中國基督教藝術本土化或“風土化”的成熟期,無疑是在20世紀三十、四十年代,畫家陳路加(1903-?)在1932年5月領洗入教后,出任北平輔仁大學藝術系主任 ,領導該系師生從事基督教藝術本土化的創作,并不斷舉辦圣藝術畫展,代表性畫家有徐志華(1912-1937)、王肅達(1911-?)陸鴻年(1914-),他們皆熟讀圣經,矢志于圣藝繪畫,風格特征兼工帶寫、精義傳神,為中國文人畫傳統賦予了新的精神內涵。輔仁大學藝術系具有代表性的圣藝術作品現在有幸多數保存在臺灣輔仁大學。比較而言,中國基督教藝術這一時期的發展,遠比亞洲其他地區和非洲更為明顯。關于何謂基督教和基督教藝術的本土化,陸鴻年的母親解釋得最為明澈透底。據陸自己早年的一段往事記載,當他看到歐洲明信片上所繪“耶穌降幅兒童”時,便問母親,畫中為何沒有中國兒童,母親回答:“耶穌也愛中國,只是這幅畫的作者是歐洲人,所以只畫了歐洲人的面孔。”陸氏說:“那時我想成為一個畫家,要畫耶穌降福中國兒童。”【3】
中國自門戶開放、西學和西畫東漸以來,對西方思想文化的認識有一個逐漸加深的過程,大抵經歷了五個階段:開初,覺得武器不如人,于是有洋務運動的發生,所謂“師夷之長以制夷”;到“五四”時期,才認識到更需要的是民主和科學,于是有啟蒙運動的發生;這一啟蒙不久就中斷了,一說是被救亡中斷,一說是被革命中斷。總之,由于十月革命成功,中國覺得還是革命解決問題,于是引進馬列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到了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很多人又覺得階級斗爭太過殘酷,扭曲人性,于是西方的人道主義、薩特的存在主義、人文主義成為熱門話題,隨即是一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登臺亮相;一直到世紀之交,才又有一部份學人通過奧斯維辛集中營、南京大屠殺、斯大林大清洗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全球生態危機的歷史反思,發現單靠西方的科學理性、人文主義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因為這些血醒邪惡事件的發生,都是在西方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現代化之后,都是把人的理性或威權領袖強調到至高無上的神圣地位之后,這就不能不使一些知識分子和藝術家轉向彼岸之思、轉向神性之維、轉向基督教尋找思想本源和靈命的根據,認識到人的罪性才是一切惡的總根源。這就是基督教圣藝術極力倡導上帝救贖之愛,并在當代中國復興的主要原由。
中國當代藝術界的突出癥候即犬儒主義,毋庸諱言,依傍藝術市場或官場而走紅的藝術家,大都患有深重的犬儒病。犬儒主義(Cynicism)從古希臘的狄奧根尼(Diogenes of Sinope)的理想主義犬儒,到今天的反理想主義犬儒。這一演變是憤世嫉俗向玩世不恭的轉變;而在今天,由于對所有大是大非皆持相對主義價值觀,犬儒派就從現存秩序的激進批評家、導演和前衛藝術家,變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種共犯合謀。中國的犬儒主義并沒有哲學上的思辯根據,而更多是一種生存策略。他們深諳“成功之道”就是與大大小小的世俗權力結緣。中國的犬儒主義包括兩個相輔相成的判斷:第一,別人所有的價值主張都是假的;第二、只有自己“唯物主義”和庸俗功利主義的目標、或者“利益最大化”目標才是真的。這種屬世的順民經驗主義也得到了東方兩種宗教思想的熏陶(實際上是互相熏陶),就是佛教和道教對世界的否定。這樣一來中國的犬儒主義不僅對信仰采取犬儒態度,它對犬儒主義也采取犬儒態度——它“深刻”地認識到,犬儒主義也是犬儒主義的。
愛因斯坦說:“使我遠離所謂無神論者的乃是一種面對和諧的宇宙深不可測,無法獲得的秘密的最謙恭的感情”。(What separates me from most so-called atheists is a feeling of utter humility toward the unattainable secrets of the harmony of the cosmos.)【4】 扼要地說,“犬儒病”真正的病根在于它的無神論本質,在于它的“無罪狀態”。它首先不相信存在一種超驗的普世絕對的價值。事實上在無神論世界,犬儒主義的價值觀是完全合乎“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邏輯的。如果人是上帝,每個個體就有自己一個價值準則,而且“自己”就是“自私的基因”并因此獲得個人和社會生存及擴張歷史的動力。在這種情況下,“我”成為最高價值,而這一最高價值必然將不同個體重疊的價值部分犬儒化,使這些理性主義的“普世價值”成為實現“我的價值”的工具。換言之,如果沒有超越“我”的更高價值的存在,所有的“我”互搏的唯一文化結果就是犬儒主義。
無神論自由主義者在批判犬儒主義的時候愿意相信:沒有上帝也行。他們深刻地看見了犬儒主義的問題就是因為他們沒有信仰。世俗自由主義者首先是人本主義者,然后是個人主義者,最后是經濟理性主義者。人本主義視人為神,但人不是神,這恰恰正是犬儒主義的邏輯起點。犬儒主義認為人是靠不住的,這點犬儒主義甚至比自由主義還要深刻。個人主義相信個人價值至上,這是對群體主義的反駁。但是,犬儒主義同樣是真正的個人主義者。至于經濟學理性所奉行的“個人利益最大化原則”,它既是當代自由主義的信條,也是犬儒主義的信條。這樣一來,自由主義只能通過道德說教來區別犬儒主義,而這一“道德理想國”的說教,恰恰是當代自由主義反省現代極權主義的主要學術成果。在這種困境中,當代自由主義和某些偽先鋒藝術家不得不把“自由民主”本身神化,作為一個不證自明的信仰前提,拒絕將這些價值放到分析領域。這也許是一種策略,回避這些概念可以避免向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道德理想國兩個極端求援。然而無論如何,無神論的的自由主義和犬儒主義最后的“動力機制”只能是達爾文主義的和道德主義的。但是,無論科學進展還是理性的進展都表明,達爾文主義和道德主義最多只能是一種社會科學的假說和心理學上的自負。
基于此,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和藝術家認識到,在21世紀,人類面臨比路德和加爾文的16世紀初期宗教信仰危機更大與更多的文明危機;這些文明危機,包括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犬儒化,包括人類道德的墮落與心靈的空虛、人類倫理與價值觀的混亂、無神論的個人主義思想橫行、人口過度的膨脹、貧富不均、能源與干凈水源的短缺、核子威脅與毀滅性的戰爭、恐怖主義、生態浩劫、全球性的傳染病盛行、過度的工業與城市化、環境污染、地球溫室效應、全球氣候的異常、自然與生物多樣性的逐年消失、地球資源的枯竭、地球可持續發展性等問題。 這些文明的危機,關涉人類的罪、懺悔與救贖等問題,也關涉于人類應該如何自我拯救的問題;作為“以拯救人類為目的”的基督教,它現在應該有更積極的行動與更正面的意義。在中國基督徒藝術家普遍認為,21世紀的基督宗教及其圣藝術,應該重新回歸基督的精神與理念,重新回歸基督信仰的目的與本質。上帝在神州大地作工,興起屬靈的圣藝術和有靈性的藝術家,正是對于這最深沉的心靈誓言和最深刻的藝術歷史使命的回應。
當此危機之際,我們有必要重申基督教精神,只有植根基督教精神,我們才會理解圣藝術的奧義、并繼續激勵、從事圣藝術的創作。耶穌給門徒有一條簡樸而高超的誡命:“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你們要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世人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5】耶穌這一誡命就成了我們判斷是否基督徒的一條簡單而可靠的標準,基督的品質就是愛,愛上帝、愛世人,就是基督徒。從圣經的經文,可以清楚了解,基督就是愛!這種愛,是來自于神界的愛,是超越人界的愛,是永不改變的愛,是永不妥協的愛,是永恒的愛,是無我無私的愛,是無邊無際的愛,是犧牲之愛,是舍己之愛,是愿意無條件背十字架之愛,是愿意做人類仆人之愛;凡是愿意認同與信仰這種愛的人,都是基督徒,他可以是人類任何一種宗教的信徒,也可以是一個沒有特別宗教信仰的人,但是他不可以是一位信仰絕對無神論、不尊重生命尊嚴或倡導仇恨意識的人。
一些人常說中國文化是樂感文化,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這說法似是而非。樂感文化和罪感文化是不同范疇的概念,不同范疇的東西不能放在一起對比。正確的說法是:中國文化是樂感文化,西方文化是愛感文化;或者說中國文化是德感文化,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劉小楓說:“如果把罪感對應于樂感的結構位置水平,明顯就搞錯了。罪感意向并不是基督教精神意向結構中的顯現狀態,而是引發另一種心理意向(按:愛感)的根據和基礎。在極為復雜多宗的基督教各派別中,沒有任何一派把罪感的精神狀態確立為個體精神所應企達的境界,而是個體精神被規定的在體性意向狀態。如果把罪感對應于樂感,等于說基督教精神倡言以罪感為個體生命的理想境界,罪感成了精神的目的性意向。事實上,罪感是被祈求超逾(得救)的意向狀態,這正是‘救贖’的意義。”【6】罪感即是對人自身中的自然欲望的自覺意識,是對人背離上帝的自覺意識。罪感的精神意向,必然引向愛感。由于愛感是在人的生命裂傷(罪)的在體上產生的,愛感生命力僅得自于超自然的神圣生命。神圣生命的救恩行動將真正超越性的愛帶給人,使罪的人在神圣生命的救恩中得到重生。這種愛感把人感覺狀態轉化為溫柔、感恩、承領、祝福的心意,人不再是漂泊于自然狀態中的孤身只影。說到底,愛不植根于人,人才植根于愛,這就是基督教精神的基本品質。
基督教精神還有一個基本品質,這就是自由。自由不僅是權利,還是恩典,沒有愛,便沒有自由,保羅說:“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被奴役的軛挾制。”【7】按基督教的原罪說,人的自由是一種罪性,人妄用自己的自由,偷吃了智慧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園。但也正是這種罪性,帶給人救贖的需要。經過耶穌救贖之愛的洗禮,自由就使人的精神位格稟有了神性的品質。新約中的上帝形象不是高高在上,而是降身為人,替人受難,直至犧牲,而后復活,為的是拯救每一顆破碎的心靈。耶穌基督不僅是愛的化身,也是自由的化身。十字架是上帝自由的象征,釘在十字架上的是人的自由,耶穌是為自由而死。耶穌基督給予人最大的贈禮,就是自由。劉小楓引用梅烈日科夫斯基的研究,認為舊約與新約的差異并非只是“公義的上帝”與“愛的上帝”之別,同樣,甚至更為重要的是:舊約偏重上帝的子民(人民),新約偏重“個體的神圣性”。什么是個體的神圣性?信仰從根本上說,是個體生命的事件,而個體生命的價值,只在與上帝的關系中才會得到確認。進入信仰之光,即是個體生命與上帝的摯愛同在,與上帝的自由同在,這就是個體的神圣性。有人說,近代個體自由主義的原祖就是耶穌基督的“我在”。二者確有親緣關系。基督教的“絕對主體性權利”,個體的“無限自由的身位”已經體現了個體自由主義的原則。
按基督信仰,人的自由同愛心一樣,不是出自自然本性,而是來自上帝的恩典,這是真正的天賦人權,是人經過上帝二次創生后所獲得的天賦人權。基督徒作家余杰在《朋霍費爾對中國自由主義的更新》論文中,通過梳理朋霍費爾在中國的接受歷史認識到:所謂基督教精神,除了最根本的愛上帝、愛世人之外,就是要高揚這種承受了上帝恩典的自由精神。不需要一套完美無缺的主義來解決問題,而需要每一個人在身體上和心靈上成為真正的“自由人”;以“光明之子”的形象去昭示出一條新的道路。正如朋霍費爾所指出的那樣:“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天才,不是玩世不恭者,不是憤世嫉俗者,不是機敏的策略家,而是真摯的,坦誠的人。要使我們能夠找到重返純樸與真誠的道路,我們的精神包容量足夠地充分,我們自身的正直足夠地問心無愧了嗎?”【8】毫無疑問,由于自由屬于先驗的存在,與神同在,自由就不屬于任何主義,更不屬于尼采的敵基督哲學的形上之“自由意志”,自由乃是生活和生命的價值本身,乃是屬靈藝術的本體所在。“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9】虛無主義以及犬儒主義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沒有被基督精神充滿的自由或前衛,僅僅是半吊子的自由主義,無論何其前衛,都是無根之浮萍,它必依附于世俗的虛妄和權利,也必毀于圣約翰在《啟示錄》所預見的那“紅龍”和“大淫婦”的惡毒捆綁。
借由上述基督精神的重申,我們可以認信,基督精神就是愛與自由,基督徒和屬靈的藝術家都是光和鹽,他/她們通過在世上作鹽作光,將天國的法則——愛與自由表現出來,當圣藝術從大地不斷涌現出來,當基督徒藝術家聚集在一起禱告、舉行展覽,就成了山上的一座城,成了一個燈塔,照亮所有能看見它的光的人,通往主耶穌之路。
中國的基督教圣藝術的特征還不是已經明顯成熟的本土化,本土化只是手段,不是其目的。其最本質的部分是,它應然隨著時代的審美變化而創造出豐富多樣的新視覺形式和風格,人們通過美的靈性感動進入神圣的意義領域。如果圣藝術的美是自足的,就必然具有基督的真理性和啟示性,因此也無法將其歸結為任何一種現實反應論、生物本能或心理意識。圣藝術絕不是指圣藝術的創作者乃是圣者,而是創作者將自己的生命和藝術才具向絕對敞開,作為上帝圣道的澄明無蔽之載體,極大地將上帝的圣道表征于世界。盡管圣藝術有其既定的部分,例如基督教藝術傳統和題材的規定性、優先性,但最終因其特殊的蘊含,因其必須承載的真理性和啟示性,也就必然要在傳統與題材、風格與形式、觀念與媒介的基礎上自我更新,開辟出新的意義空間和視覺樣式。圣藝術的審美創造尤其在新教教義中互為表里、融為一體。而世界基督教會歷史的一些光輝時刻,也正是保護并推動這種既在審美中超越又在教義之公義中融合的時刻。
在20世紀百年中國文化藝術歷史上,基督徒藝術家、作家還很稀少,盡管并沒有出現R.M里爾克、T.S艾略特、魯奧、夏加爾、梵高、薩瑟蘭乃至如當代俄羅斯圣藝畫家穆欣那樣影響廣泛的人物,但同樣值得敬慕和引以為榮的是,中國基督徒藝術家因信稱義,在曠野呼告,在暗夜追尋神跡,守護、培植著信仰的“一粒芥子”,使之茁壯生長。中國基督徒藝術家與廣大的基督徒、虔誠的教會同工一道,以使徒的使命感作出了有益的奠基,累積了豐盛的屬靈的奉獻。在新世紀,隨著基督教在中國城鄉的普遍復興,民間藝人、城市社區年輕的一代藝術工作者同時被上帝的恩典興起,他們應該更為有福,因而也必然經歷更艱險、更復雜的試煉。然而,無論我們怎樣看待上帝的計劃,中國的基督徒藝術家只能用沾滿他們家鄉泥土的鞋底把信仰、生活和藝術粘合在一起。在上帝的土地上,他們是沾滿泥土的孩子。中國基督教信仰及其圣藝術的前途何在,取決于它對中國社會肌體和精神震顫的感覺能力,取決于它們在泥濘大地上行走的能力。
而當角聲再度響起,圣靈臨到神州,基督的精兵就是藝術的先鋒。
2009-4-2,清華園
注釋
【1】《約翰福音》1:5。
【2】 參見柏萊德:《清宮洋畫家》,耿昇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1月版,序言,頁9-10,柏氏指出,歐洲被啟蒙時代的人士理想化了中國形象,與真實的中國形象有巨大差異,根據李約瑟的研究,中國在他們的發明中本來是超前西方數世紀,可是在18世紀卻在沉睡中。乾隆是一個歷史罪人。柏氏印證了一位耶穌會教父的話:“我們違心地犯了宗教罪孽,我的兒子和我,我們在時間上過分超前了,我們在時間上過分提前成了現代人。”另,有關耶穌會士在明清兩代的藝術創作和傳播、交流活動,可參見莫小也《十七—十八世紀傳教士與西畫東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1月版。
【3】 丹尼爾.約翰森.弗萊明(Daniel Johnson Fleming):《不同的表現手法,不同的藝術風格:20世紀初期亞洲及非洲的基督教繪畫》,王魯譯,成言藝術出版,頁89。
【4】 Albert Einstein to Joseph Lewis, Apr. 18, 1953
【5】 《約翰福音》13:34-35,另見15:12、17.基督教誡命“愛人如己”,既是舊約圣經的命令,也是耶穌和使徒們的命令。
【6】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7月第1版;頁145。
【7】 《加拉太書》5:1。
【8】 余杰:《白晝將近:基督信仰在中國》,晨鐘書局,2008年4月版,頁32。
【9】 《約翰福音》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