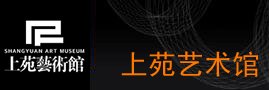|
��(d��ng)��Ԋ����Ҫһ��(ch��ng)˼���\(y��n)��(d��ng)(ʒ�_��)
[2009-4-21 17:15:11]
��(d��ng)��Ԋ����Ҫһ��(ch��ng)˼���\(y��n)��(d��ng)
�� / ���衢ʒ�_�ޡ����D����˪������
���裺ȥ��ʮ�·ݣ����ˑcף��W(xu��)Ժ���Ї�(gu��)����20���꣬�҂�?c��)��?j��ng)�e�k�˵�һ�θ��ɳ����Ո(q��ng)����һЩ���u(p��ng)�ҡ�ˇ�g(sh��)�ҡ�Ԋ�˵ȁ�ӑՓ�����u(p��ng)�Dz�����ʧ�ˡ��Ć��}�������Ǹ��ɳ���ĵڶ��λ��(d��ng)���҂��c�Ѻ��Ļ����������Ѻ��Ļ��͏d��ӑՓ���}Ŀ���P(gu��n)��Ԋ��ģ������҂�Ո(q��ng)������λԊ�ˣ�ʒ�_�ޡ����D����˪��������ӑՓ�����}�ǡ���(d��ng)��Ԋ����Ҫһ��(ch��ng)˼���\(y��n)��(d��ng)�������ȣ��҂���֪����ʲô�ӵĬF(xi��n)�(g��u)�����@�N��Ҫ��
����ʒ�_�ޣ������@��(g��)Ԓ�}Ҫ�����h(yu��n)һ�c(di��n)����?y��n)��҂��F(xi��n)�ڵ�Ԋ�����D��Ԋ���d�^һ���Ǐ�70���ĩ��80������_ʼ�ġ�80�����90������F(xi��n)�ڣ���һ�����B�m(x��)�ԣ��@��(g��)�B�m(x��)����Ҫ�����ģ�����һЩ��һֱ�ڌ������ǂ�(g��)�r(sh��)���_ʼ���F(xi��n)��һֱ�ڌ�Ԋ���@Щ�ˌ���Ԋ��?y��n)��@Щ�ˣ������������m(x��)�ԡ����⣬ÿһ��(g��)�A���в�ͬ�����ڌ�Ԋ���в�ͬ���˼����M(j��n)�����@Щ�¼����M(j��n)�����@Щ�˸�ԭ���ѽ�(j��ng)�ڌ�Ԋ�ģ��˺�Ԋ����һ����(li��n)ϵ�ԣ��@��(g��)(li��n)ϵ�Կ����Ƿ��������ơ���ͬ�⡢�����菽�����п��ܡ����F(xi��n)���п���Ҫ��һ��80�����
���������f�҂�ÿ��(g��)���u(p��ng)Փʲô���鶼���Լ��ĽǶȣ�����������ô���^�����Լ���80��������_ʼ��Ԋ�ģ���(du��)֮ǰ��Ԋ���ҿ���Ҳ��ͨ�^ij�N��ͬ��ĽǶ�ȥ���c�M(j��n)ȥ�ġ�ij�N���^�Ϳ��^��(li��n)ϵ�ԣ������@��Ҳ�܉�õ��w�F(xi��n)�����X�����X�����X�ؾ�ͬ�⣨��ͬ�⣩�ˡ�
����һ���҂��ġ���ˎ���β�����ʽ�ġ�������
�������裺80���Ԋ��Ļ���˼���YԴ��ʲô���㲻ͬ�����ʲô��
����ʒ�_�ޣ����Ҍ�Ԋ֮ǰ�ѽ�(j��ng)�е�����Ԋ���\(y��n)��(d��ng)�������Č�(du��)���ǡ����족�ɡ������족���҂����^��Ϥ��������һ��(g��)��(qi��ng)���ᘌ�(du��)�Č�(du��)�����������R(sh��)�ΑB(t��i)������ʮ���һֱ�ڳ��桢�������@��(g��)���R(sh��)�ΑB(t��i)�ǚvʷΨ�����x���ÚvʷΨ�����x���q�C���v�����Č�(du��)�����ǰ��������ı��w�еġ��҂��@��(g��)������ˣ���80������ЙC(j��)��(hu��)���|��������һЩ�µ���Փ��Ҳ��������������Փ�����nj�(du��)���҂����f���µ���Փ���҂��Ľ����^��Ҳ��ͦ��ֵġ������f�҂���һ��(g��)��Ȼ��ͬ�r(sh��)Ҳ���^�������y(t��ng)һ��ͯ�꣬��һ��(g��)���L(zh��ng)��(j��ng)�v�����ܴ��һ�ӣ����������r(n��ng)��߀���ڳ��У������Кg�����п����������҂����|���������x���ʹ������x���P(gu��n)���ČW(xu��)��Ʒ�������fС�f�����_�ص�С�f߀���ȃ�(n��i)˹��đĕr(sh��)�l(f��)�F(xi��n)�҂��п옷����������ͯ�꣬���^�����ij��L(zh��ng)��(j��ng)�v�����⣬�҂��]�з��ѵĸ��X���ǂ�(g��)�r(sh��)����X���ѡ�ʹ�����⣬�����҂��_ʼ�W(xu��)��(x��)��ͨ�^�������ČW(xu��)��Ʒ���M(j��n)һ��ͨ�^�@Щ��������Փ���W(xu��)��(x��)���ҷ��ѡ��W(xu��)��(x��)ʹ�࣬�W(xu��)��(x��)���^��������ʽ��ʹ�ࡣ�M���҂��]����ͬ�������������h(hu��n)���������]��ͬ�|(zh��)���Z�����@Щ�|���҂�߀�njW(xu��)��(hu��)�ˡ�
�����W(xu��)��(hu��)�˵��Ǜ]���k���ί����҂��]�����@�N����ˎ�������������˗l�������a(ch��n)���@�N�����@�N�^(q��)���@�ӵ�ˎ��@��(g��)ˎҲ�β����@�ӵIJ�����������һ��(g��)�����IJ����@��(g��)�����Ї�(gu��)���˾�׃�N�ˡ��҂�����ˎ�β����@�ӵIJ����ܵ���߅ȥ����?y��n)���IJ���׃�N��������ˎҲ�����á�����80������҂��ǂ�(g��)�r(sh��)����˼������һ�c(di��n)��֡��҂���(d��ng)�r(sh��)����˼��硢�����磬�����f���磬����һ��(g��)˼�����\(y��n)��(d��ng)���@��(g��)˼�����\(y��n)��(d��ng)�Ǹ���(g��)����ģ�Ԋ����@�l(f��)����(li��n)ϵ�����ߣ��ܻ����@��(g��)���еĵط�Ҫ����ʲô�|�����㌑һ��(g��)��ͬ��ʽ��߀�Dz�ͬ��(n��i)�ݵĖ|����Ҳ�܉�ż���õ��l(f��)������һЩ�ˏģ�˼���_�ŵģ���W(xu��)���I(y��)�ֵ�һЩ����C(j��)��(g��u)���������������������õĿ��g�l(f��)�������Ʒ��
���^��80�����˼�����\(y��n)��(d��ng)�mȻ�����ˎׂ�(g��)���棬����Ԋ������ķ���(y��ng)���䌍(sh��)�DZ��^��ġ������f˼�����\(y��n)��(d��ng)��������һ��(g��)�������x�đB(t��i)�ȣ�����Ԋ�����棬�䌍(sh��)���@֮ǰ��ʮ�꣬���_ʼ��һ��(g��)���ɕr(sh��)�ڡ��M���@��(g��)���ɵ����|(zh��)���ˑB(t��i)�����x�����������������ߣ�������ȡ�����ӑՓ���Dz�����Ć��ɣ������ǣ������80���˼���͌W(xu��)�g(sh��)��֪�R(sh��)���Ӹ�Ć���֮�g�Dz��������ȫ��ͬ���@�ǿ���ӑՓ�ġ����ǣ����Լ����X��80���˼���͌W(xu��)�g(sh��)�������ɵĆ����@��(g��)������Ԋ��硪�������ɼ������(q��)������������ˡ�
����80�����Ԋ���@�ײ������p��Ԋ�ˣ��������������ѽ�(j��ng)�|(zh��)׃����һ�N���飬���ČW(xu��)����Ԋ��׃���ČW(xu��)������(n��i)���@�Ǐ�(qi��ng)�ҵ���һ�N�����О顣�mȻ�������ČW(xu��)��Ŭ����������(g��)���Z����׃ʹ��������ijһЩ�����Ļ����dž�(g��)�Č����F(xi��n)���䌍(sh��)����ij�N�Y(ji��)��(g��u)�Ե�(li��n)ϵ����ij�Nȫ���ԵĽy(t��ng)һ�IJ��{(di��o)���ҹ�Ӌ(j��)��80�����Ԋ�ˣ��M���и��N�����ĸ�ʽ���\(y��n)��(d��ng)ʽ�ķ�ʽ��Ҳ�Л]���뵽�ģ��s�������˵IJ�ͬ�ģ��ط���80������ҹ�Ӌ(j��)�Ѓɂ�(g��)�����Ŭ����һ��(g��)�����DZ��^�������ڵ��S�㌑һ��������һ��(g��)�����DZ��^���ĵġ����^���ĵģ������܉�֔(j��n)���ģ�֪��Ԋ����һ��(g��)��KҪ��ɵ���ʽ���oՓ����ʲô�ӵ����(hu��)��������ǂ�(g��)�����룬��Ҫ���傀(g��)����־Ҳ�ã�߀��Ҫ��������Ҳ�ã�����Ҫͨ�^����������ʽ����ɵġ�������е��V��Ҫͨ�^������ց팍(sh��)�F(xi��n)���v������80���ͦ�S���������v���@�
�������裺90����أ��Л]�к�80�����ͬ��(g��u)�Ե�˼���YԴ��Ԋ�脓(chu��ng)��һЩ����(d��o)˼�롢������ˇ?y��n)�Փ�?/P>
����������80�����90���������׃�ø�������
��������������ӑՓ���}Ŀ�Ǯ�(d��ng)��Ԋ����Ҫһ��(ch��ng)˼���\(y��n)��(d��ng)����˼��Č���ӑՓԊ�膖�}���@��һ��(g��)������ĽǶȡ��@Щ��������ӑՓԊ��һ���(hu��)�Č����Ƕȡ��Z�ԽǶȡ���x�Ƕȵȵȣ������ٕ�(hu��)��˼��Ƕ�ȥ�ᆖ�������ܵ��X��Ԋ���˼���Dz�ͬ�I(l��ng)���ǃɂ�(g��)�Ю�(d��ng)���в�ͬ�ġ���Ҏ(gu��)����
���������_��һ��Ԓ��ӡ�������f������ͬ�⡱�đB(t��i)�Ȇ��}����������w�Ͽ����@��(g��)����ͬ�⡱ǡǡ�Ǯ�(d��ng)��Ԋ��������(d��ng)��ˇ�g(sh��)��������Ė|�����@�������uһ����Ҳ��������ĵ�����Ԋ�˂����@�N����ͬ�⡱��(g��u)����˼���ϵĚ��|(zh��)�ͽY(ji��)��(g��u)���ṩ��һ�N���w�Ժ��������������f��˼�����\(y��n)��(d��ng)��˼���ŵ�һ��(g��)���x����Ҫ����һ�N�µ����(hu��)�Y(ji��)��(g��u)�����ʽ���Ļ��w�ƣ�Ԋ�ˡ�ˇ�g(sh��)�ҵġ���ͬ�⡱�������@��һ��(g��)�^�̡�90����Ժ��Ї�(gu��)�����(hu��)���Ļ�Ҳ�Ĵ_���F(xi��n)�˽Y(ji��)��(g��u)�Ե�׃����Ԋ�˂�����ġ���ͬ�⡱��(sh��)�H����׃������ӵġ�ͬ�⡱�������fԊ�茑���������������µĽY(ji��)��(g��u)��Ĭ�J(r��n)�����������@�ӵ�׃����ɃɷN��ͬ��Ԋ����|(zh��)������f��80���Ԋ�����һ��(g��)��ͬ�w��Ԓ��90���֮���@��(g��)��ͬ�w�ƺ�׃�ø���(w��n)���ˣ�Ԋ�˵����ɸи����ˣ��]����ȥ�����㌑ʲô������ȥ��������(sh��)�H�Ϲ�ͬ�w�ĸ���׃�ø�ϡ���ˣ�����׃�ø������ˣ��������֮�g��(li��n)ϵ׃��Խ��Խ�٣���ͬ�⡱���ߡ���ͬ�⡱Ҳ�]̫��^(q��)�e��
���裺�����ᵽ�˼��ČW(xu��)�Ć��}�������f���L����Ҳ�г��������Ƿ����εģ�����������70���ĩ80������������s�ɞ�һ�N���ΑB(t��i)�ȡ�ͬ�ӣ������εġ����ČW(xu��)����ʽ��������Z���з����к�(qi��ng)�������ԡ����D(zhu��n)�������죬���ČW(xu��)������ʽ��߀����һ؞�������{(di��o)���ѽ�(j��ng)׃�ˣ��Л]���@�N���ܣ�
������������(du��)���҄����f���@�ɷN��B(t��i)��(sh��)�H���Dz�ͬ����(d��ng)��׃��һ��(g��)�ƶȡ�׃��һ��(g��)Ĭ�J(r��n)���w�Ƶĕr(sh��)���H�DZ���������ԣ�������Ą�(d��ng)��Ҳ׃�÷dz������ˡ�
������˪�����ČW(xu��)�@��(g��)���������ڮ�(d��ng)�r(sh��)���������Եġ��@��(g��)�����Բ���һ�㺬�x�ϵ������ԣ������f�������r����ᘌ�(du��)�ԡ������@��(g��)�l(f��)չ���^�����ѽ�(j��ng)����׃�÷����λ��ˣ�׃�ɺܷ�(w��n)���Ľ̗l��Ҳ���ʧȥ����ԭ�������x����ֹһ��(g��)�˱�¶�^�@�ӵĿ�������(d��ng)��Ԋ����������ĸ����g����70����ĵ����ČW(xu��)��˼����g���N(y��n)����������@��(g��)������80����õ��˱��l(f��)������90���֮����u�؆�ʧ���@��(g��)�f������ȥ����(du��)Ԋ���ڮ�(d��ng)��������o����һ��(g��)��ጣ����nj�(sh��)�H���@��(g��)����ǡ�þ�����?y��n)�����ᘌ?du��)�ԡ���80������oՓ�����ČW(xu��)��˼�롢�W(xu��)�g(sh��)���I(l��ng)���ڹ�ͬ��ij�N�����@�N�������պ�Ҳ��������ȫһ�µģ������@��(g��)ᘌ�(du��)�ԵĴ���ʹ�����@�����҂��������f����Ч�ԡ���90����ԁ����@�ӵ�һ�Nᘌ�(du��)�������ع̻���һЩ�µ�֪�R(sh��)��һЩ�̗l��
����������Ԋ��һ�N�����Ļ��������ʽ��
�������D���ұȽ�������˪��λ���gƫСһ�c(di��n)���ҽ���Ԋ����Ҫ�����ڷ��]�����z������һЩ�o���R(sh��)Ӱ푡��Ă�(g��)�˽�(j��ng)�v���f���cԊ�ƺ��l(f��)������ʲô�P(gu��n)(li��n)�����_ʼ�댑Ԋ���]���κ����ɡ�������ǰ�������]���x�^���VԊ��Ҳ����Ԋ������ʲô��Ψһ���Դ_�J(r��n)���ֲ�֪������������^����Ԋ�dz�ߵģ����҂�Ψһ��Ҫ��Ė|���������M(j��n)���W(xu��)���_ʼ�xԊ��Ȼ���_ʼ�������^�˽�Ԋ��Ҳ��Ҫ�����ڮ�(d��ng)�r(sh��)����Į�(d��ng)��Ԋ����Ʒ�Լ����(gu��)���g��Ʒ��Ҳ�����f�ı�����Ė|������KҲ�S���]��ȫ�x����������ģ�����X�����ǣ�Ԋ���ṩ�Ė|���c�Լ��������кܴ�ą^(q��)���ԡ��S�����������룬���X���܉��֡��҂���֪�����ഺ��Ԋ��һ����(li��n)ϵ����ֻҪ���p����Ѫ֧�ֵ��Z�ԡ����X���ԾS��һ�Εr(sh��)�g��������һ���r(sh��)�������и��ܵ��@��(du��)�҂�(g��)�ˁ��f�ǂ�(g��)�λ\�����X�e���֡�
���Լ����������R(sh��)�ϰl(f��)���P(gu��n)(li��n)��߀���x�������ġ���(d��ng)���Ї�(gu��)��˼���r�c�F(xi��n)���Ԇ��}����ƪ���¡���ƪ���·�����(d��ng)�����(hu��)�M(j��n)�̣�������Ҫ��Մ�r(n��ng)�冖�}����?y��n)����Լ��r(n��ng)������ģ�ÿ������������ѽ�(j��ng)���X���r(n��ng)���׃�����������X���@Щ�|�����䌑Ԋ�����c(di��n)���⣬��Ԋ����ҪƯ������⡢�F(xi��n)���ģ������r(n��ng)������e�۵���У��^��˽�ˡ���м����Ȼ�и��飬�����X�Ͼ��X�����⡢����һ�ȣ�������Ԋ�����Ǻ��żȻ�x��������ƪ���£������ĺÉě]�І��}������Ҫ�����|��(d��ng)���ң����^ȥ���顢�bѺ���̈�(zh��)�����Һ�Ȼ������˳���������һ�r(sh��)�g�J(r��n)�����Լ����y�����ضȡ����������ε����ҡ����^ȥ�ؼң��������^�ߣ����^�@Щ�������ĬF(xi��n)��ֻ���һ�ۣ�����(hu��)̫�P(gu��n)ע�@Щ�|�������Լ��c��֮�g��ʲô(li��n)ϵ������?y��n)�l(f��)��������߅��߀��(hu��)�������w�ϵ������㿂���ܷ��J(r��n)��Щ�l(f��)��������߅������@�N��w������ɢ���h�飬����(hu��)��ӳ������^����R(sh��)�ϣ���У�������Ҳ�Sҹ��r(sh��)��һ����߀��(hu��)����һ���������������Ϳ��������s�ߡ���(d��ng)�ҿ�����ƪ���º�ͻȻ����(d��ng)���ң�����?y��n)����^ȥ��ЩƯ���ģ�ɢ�����w�����ﱻ������һ�N���F(xi��n)�ڿ������@�N����Ҳ���^��(ji��n)ª������(d��ng)�r(sh��)��(du��)�ҁ��f����������Z��Q���������Ҵ_�J(r��n)�����Լ��Ĵ��ڡ��ɴ˳��l(f��)���ŕ�(hu��)�����R(sh��)�����˽�һЩ�|�������_����Ĵ��ڡ�
�ҬF(xi��n)���ڱ���һֱ�ԁ������Ќ�Ԋ�Ă��С���Щ����W(xu��)�ӣ�߀Ҫ��Ԋ��߀�ڌ�Ԋ�����80�����90������ڣ�Ԋ������˥�䣬��߀�Dz�ͣ�������p�˼��롣�����@��(g��)���룬�Ҹ��X���|(zh��)��һ�c(di��n)�c(di��n)׃�����@�N���|(zh��)���ܴ���һ�N���wڅ�����X�Ì�Ԋ�����_�ؾ���һ�N�I(y��)����(d��ng)�������ƹ�������ơ�Ԋ�����@����������ǽ��Q�P(gu��n)ϵ����Ҳ�S�����Լ����`�⡣
������������(d��ng)���˸��v�����ʽ����ԊҲ��һ�N�����Ļ��������ʽ��
����ʒ�_�ޣ����ѷ�ʽ��
�������裺�@�ڄe���I(l��ng)����ձ飬��DV�������C(j��)���L�����ռ�����
�����������ͮ�(d��ng)��Ԋ����ԣ�ǡǡ����(y��ng)ԓ���F(xi��n)�@�ӵĠ�r����?y��n)�?d��ng)��Ԋ���һ��(g��)��(n��i)��Ҫ���Ǿܽ^��Ԋ�讔(d��ng)��һ�NȤζ�����{(di��o)������������x�ϣ�����(y��ng)ԓ�ɞ�ˢ���Z�ԡ���׃��(j��ng)�(y��n)�Y(ji��)��(g��u)����(chu��ng)���r(ji��)ֵ��һ�N�������mȻ�����M(f��i)��Ԋ��Ҳ����Ҫ��Ԋ���܉�֏�(f��)�c��ͨ��������P(gu��n)ϵҲ����Ҫ�������X�ý���ӑՓ�����c(di��n)�����@��(g��)����
�������裺����˽���ĵĕr(sh��)��Ҳ�ᵽ80����������x��˼���YԴ��90��������ɡ������������x��һЩӑՓ��Ŀǰ�ゃ?c��)�Ԋ��?chu��ng)���^���У����w��ʲô�|���ゃ���X��Σ�C(j��)�У�������������Ҫһ��(ch��ng)˼����\(y��n)��(d��ng)��
�����ġ�Ԋ��׃��Խ��Խ?j��ng)]���u(p��ng)�r(ji��)��
����ʒ�_�ޣ��䌍(sh��)�҂������v�@��(g��)�ĕr(sh��)�����Ҳ�f����90����mȻ���@Щ˼���Ʉe�����_��һ��(g��)һ��(g��)Ȧ�ӣ�һ�Nһ�N����(ch��ng)����������h����(du��)���qՓ���Є�(sh��)���̈́�(sh��)���������F(xi��n)�����Ǹ�80�����һ�ӣ�80����ĕr(sh��)����Ҳ�S��ʲô���x���]��ʲô�P(gu��n)ϵ����������@Щ������Ҳ��������Ҳ��̫���⡣���nj�(sh��)�H��߀�����|(zh��)�غ�������P(gu��n)(li��n)����?y��n)��ǂ�(g��)�r(sh��)�����(hu��)���^�ۺ�Ԋ�裬�oԊ�˺ܶ�Č��ۡ�����90�����һЩ��
������һ��(g��)�F(xi��n)��90����mȻ�������ɡ����������x���Ϻ���һЩ�W(xu��)УҲ�������Σ�C(j��)��ӑՓ������Ԋ���mȻ֪���������80������ö�һ�c(di��n)������?y��n)?0���Ԋ�˵��I(y��)��90���Ԋ�˵��I(y��)��ͬ�ˣ�90�����Ԋ�˺ܶ��ѽ�(j��ng)�ڴ�W(xu��)����̕�����������?y��n)�ʲôԭ��ʲô�����������?hu��)ȥ���@��(g��)�|�����˽�ø��ࣻ80����˽�ò��ࣻ�����ܵ���ͨ�����܉���ʲô���ҹ�Ӌ(j��)��֪������?y��n)��҂��ij��L(zh��ng)��(j��ng)�v��࣬�҂��Ľ�(j��ng)��(j��)̎�������ε�λ��࣬�҂���֪�R(sh��)��ԴҲ����࣬�㿴ʲô����Ҳ��ʲô�����㿴��������Ҳ�����������ČW(xu��)��80����ǂ�(g��)�r(sh��)�����Ҫ����ʹ��˼����������Ҫ��һ��(g��);�������ČW(xu��)������90����ČW(xu��)��λ�ˣ��mȻ�W(xu��)�g(sh��)����һЩ�W(xu��)�ߺ͌W(xu��)��ӑՓ��˼�붷��(zh��ng)�dz����ң������@Щ��Ԋ���˿���ֻ�ǿ��ˣ���һ�c(di��n)���������
����90����γ��@�N���䵭�đT�ԣ��䌍(sh��)Ҳ����Ԋ�˛]���˅��c���ܶ�Ԋ�˸����ˡ������u(p��ng)�����ČW(xu��)�����׃�����e�ģ����W(xu��)�g(sh��)�����(hu��)�W(xu��)���ܶ��e�ġ��D(zhu��n)����(du��)�r(sh��)�����dȤ������Ԋ��o�Լ�����һ�K���ء���������˺ܶ��e�ģ�����ͦ�гɾͣ������f�����һ�c(di��n)�X���õ�һЩʲô���L(zh��ng)Ҋ�R(sh��)���U(ku��)��ҕҰ�ęC(j��)��(hu��)���������]����Ԋ���@������ʲô�����X�ú���һ�c(di��n)���]����ʲô���顣Ԋ���Dz��౻��(qi��ng)���ģ����Ҹ��X�������u(p��ng)�r(ji��)���C(j��)�ơ��@��(g��)�C(j��)���ںõ�һ�棬����һ�c(di��n)��(du��)�A���͕r(sh��)�ֵĵ������������õ�һ�棬ʹԊ��׃�ɱ��߸ߒ���Ė|�������@���õ�һ�棬Ԋ�˸��X������Ҫ�����Ŭ��������Ԋ��������˵�˼���˼��(li��n)ϵ������ij�Nֱ�ӵģ������f��l(f��)�r(sh��)�g�����(li��n)ϵ����(sh��)�H���@��(g��)(li��n)ϵԽ��Խ�١���?y��n)��������֪�R(sh��)��İl(f��)��(li��n)ϵ��һ������һЩ��ͬ��Ԓ�}�������҂���(du��)�@Щ��(g��)Ԓ�}���䵭�ġ��@��ʹ��Ԋ�豻�҂����O(sh��)�������x�ġ��@��(g��)���x�ǹ��ϵģ����������Ԟ�����Է�飬�����ǣ����ĵģ��e�˽o�O(sh��)���ġ���(du��)���ČW(xu��)���f��Ԋ��Î�һ�c(di��n)��̖(h��o)���ܣ��ش��˺�����ļm�𡣹ŵ��ČW(xu��)Ҳ�Г�(d��n)���@�ӵĹ��ܣ����ǹŵ�Ԋ�W(xu��)���S�oԊ�����Dz�Ը���^��Ԋ��Ҳ��(y��ng)ԓ�Г�(d��n)��Dz���ܣ�����Ԋ�裨���լF(xi��n)��Ҏ(gu��)����Խ��Խ?j��ng)]����Dz���dȤ�ˡ��絽�҂���ӑՓ�ρ��f��Ԋ��Խ��Խ׃�Û]���u(p��ng)�r(ji��)���F(xi��n)�ڣ���Ԋ�ˌ�Ԋ�������@ЩԊ�����u(p��ng)Փ�������������֪�R(sh��)���ӛ]�k���u(p��ng)�r(ji��)���B�����Լ�Ҳ�o���u(p��ng)�r(ji��)��
�������裺90����ĕr(sh��)�����^��֪�R(sh��)����Ԋ���͡����gԊ����ӑՓ�������ᵽ�ġ����ء���߅���І
�����������@��(g��)ӑՓ�ѽ�(j��ng)�^ȥʮ���ˣ���(d��ng)��Փ��(zh��n)�ı��l(f��)�������·ݣ���һ��Մ���@��(g��)���}��߀�ǰ�����(d��ng)��һ��(g��)���r(sh��)�¡���Մ���䌍(sh��)�������Ժ��Ї�(gu��)��(d��ng)��Ԋ��l(f��)���˺ܶ��׃�����ǂ�(g��)Փ��(zh��ng)�����mȻ�]�|��̫������Ć��}�������Կ�����һ��(g��)��ˮ�X����(d��ng)��Ԋ��Ľ������u(p��ng)�r(ji��)�����əC(j��)�������Ժ�Ĵ_�кܴ�׃����
�塢��Ԋ��һ�_ʼ��һֱ��̎��Σ�C(j��)�Ġ�B(t��i)��
������˪�����Լ���Ԋ�Ǐ�90������_ʼ����(d��ng)�r(sh��)��һ�N���X���X���Լ����յ��ˮ�(d��ng)��Ԋ�茑�����}�j(lu��)�����҅��c�M(j��n)ȥ������̎���d�^�Ġ�B(t��i)�����X����һЩ�µČ����^����R(sh��)���������������γ�һ��(g��)��ͬ�ķՇ������Ԯ�(d��ng)�r(sh��)�Ҍ��^һƪС���£�����������ڃ�(n��i)���҂�һЩ���ѹ�ͬ�k��һ��Ԋ�迯��ģ��������һ��(g��)�������(d��ng)��Ԋ�Ă��y(t��ng)���������J(r��n)�飬��(d��ng)��Ԋ��80����_ʼ�ѽ�(j��ng)�����Լ���һ��(g��)���y(t��ng)���ҬF(xi��n)�ڷ�ʡ����(d��ng)�r(sh��)����@��(g��)�J(r��n)�R(sh��)�ĕr(sh��)���䌍(sh��)����һ��(g��)�e(cu��)�X���ƺ���80�����90�������������Ԋ����^�����Ԋ�c������J(r��n)�R(sh��)����(du��)���Z�Ե��J(r��n)֪�����⣬���o�ļ��ɣ��@Щ�|�������ǿ�������һ��(g��)��(w��n)���Ļ��A(ch��)�����@����ȥ���Ϳ��ԣ��dz����^�����쿴�����Č�(du��)����(g��)��Ԋ��һ��(g��)���v��ĽǶȣ��Ұl(f��)�F(xi��n)��Ԋ��һ�_ʼ��һֱ��̎��Σ�C(j��)�Ġ�B(t��i)���@��(g��)Σ�C(j��)���H���f�������ڃ�(n��i)�ĬF(xi��n)���ČW(xu��)���Ї�(gu��)�ĬF(xi��n)�����^����Ҫ�Г�(d��n)�Ĺ��ܣ�������Ԋ��ô�J(r��n)�R(sh��)�Լ���Ҳһֱ����һ��(g��)��Σ�C(j��)�����^���У�����Ԋ�Ļ���Ҳ�����ڑ�(y��ng)��(du��)�@�NΣ�C(j��)���^���У���Σ�C(j��)���R(sh��)��ጷų����ġ�����횷dz����J�������Ҫ�{(di��o)���Լ������c(di��n)��ʹ�@��(g��)���c(di��n)���Լ���̎���Z������һ��(g��)���ϡ���80�����Ԋ��͆������x��˼��֮�g���P(gu��n)ϵ��Ҳ���Է����@��һ��(g��)Σ�C(j��)���}�j(lu��)��ȥ�J(r��n)�R(sh��)����ˣ����^�ٿ����ҽ������Ҫ�����ĵط����ǣ������(d��ng)��Ԋ���@��һ��(g��)���y(t��ng)���@��(g��)���y(t��ng)�Dz���،��Լ���������Σ�C(j��)�����R(sh��)֮�У�Ҳ�����f������ʼ�KҪ���������I(l��ng)��֮�g�a(ch��n)��һ�N��ͬ�С�
�������裺�����ᵽԊԽ��Խ�����u(p��ng)�r(ji��)�����ɱ��ˡ�ԭ����ʲô����Q������ʲô����?y��n)鮅���Á�һ��(g��)Ԋ�������Д�Ļ��A(ch��)��ʲô���ゃ߀�Ǖ�(hu��)�Ђ�(g��)��a���Дࡣ�ゃ�F(xi��n)���X�������ĺ�Ԋ�Ę�(bi��o)��(zh��n)��ʲô������@��(g��)��(bi��o)��(zh��n)߀Ƿȱ��Ԓ������(y��ng)ԓ��ʲô���ӵģ������@Ҳ���҂���ҪҪՄ�Ć��}��
ʒ�_�ޣ��䌍(sh��)ÿһ��(g��)�ˌ�(du��)ֵ�õĖ|������(hu��)�����Дࡣ������һЩ�Д࣬�����f�㌑��ʮ��߀��ʮ����Ԋ���㿴һ��(g��)ʲô�|��һ�۾�֪���@��(g��)�|����߀�ljģ������@��(g��)�Д�������һ��(g��)��(x��)�T��һ��(g��)���x�ӳ���(x��)�T���@��(g��)��(x��)�T������������Լ�����(x��)�T�У�ʹ����֪���Լ��@��(g��)�Д��䌍(sh��)��һ��(g��)�T�ԾS�o(h��)���S�o(h��)���o(h��)�Լ��������@��һ��(g��)Ȧ�ӡ��@��(g��)Ȧ���������ֻ����һ��(g��)�ˡ���S�o(h��)�@��(g��)߅�硣���ң������f�����f�@��(g��)�|���ã����X���@��(g��)�Ϻ��ҵ���(x��)�T���҂�ÿ��(g��)���γ�һ��(g��)��(x��)�T�����ף���(j��ng)�^�ܶ����˼������(sh��)�(y��n)����(sh��)�`��ͨ�^�ܶ���ķ�ʡ���ҬF(xi��n)��Ҫ����һ��(g��)�Ϻ����Լ��T�Ե��Дࡪ���@��(g��)�|��ͦ�õġ�������һ��(g��)�Ƕ��v����֪���Ϻ��T�Ե��������@�ӣ������@��(g��)�|�����ã����Ì�(du��)�������x����?y��n)����u(p��ng)һ����ᘌ�(du��)���u(p��ng)�Č�(du��)������һ���棬Ҫ�Լ����棬��������u(p��ng)���(d��ng)���㌍(sh��)�H�����ڼ�������J(r��n)�R(sh��)������Д���(d��ng)�����Լ���˼���������õ��Д���ܼ���҂�������ʲô����ԊҲ�ã����u(p��ng)ՓҲ�ã���Ҫ�����܉������@��(g��)����ĕr(sh��)����X���Լ��挍(sh��)�ش��ڡ�����һ��(g��)���u(p��ng)���(d��ng)����Ԋ�ĕr(sh��)��һģһ�ӡ������]�к�ij�N�܉�_ͻ�Ė|���l(f��)���_ͻ���X���Լ��@�N�r(ji��)ֵ�^���������R(sh��)�]�к�ʲô�|������һ��ĕr(sh��)��l(f��)���������@��(g��)���(d��ng)������ֵ�Ñ��ɵġ�Ҳ���nj�(du��)�Լ����ʡ������@��(g��)�|���Ұ��ՑT��Ҫ�f���ã����ǣ�����f��Ҫ�ļ����Լ���˼���ĽǶ��v��Ҫ��(du��)�Լ��������ҬF(xi��n)���f���ã�������˼����ȫһ�ӵġ�
�����ڱ��^�������r���f��߀�Dz��ö���һ�ӵġ��ڲ��õ���r�£����^��ƽ��̎�������Ǵ�Ҷ��ԶY��������l(f��)����Ġ�(zh��ng)Փ���������в�ͬ����Ҋ�������Լ��Ŀ������҂��l(f��)�����p��ʲô�Ľ��h������҂�?c��)��@�ӵ�һ��(g��)��(ch��ng)�ϣ����f�@��(g��)�|���ܺã��������f���ã��f�úͲ�����һ�ӵ���˼��߀��һ�N�����f�Ͳ��f��ͬ��һ��(g��)��˼���@����һ����һ��(g��)����Ҫ��ȱϯ��һ��(g��)Ƿȱ���҂��������@��(g��)�Д��һ��(g��)�Д���(d��ng)�ĽY(ji��)�����@��һ�N����˃�(n��i)�ݵġ�ҕ����Ҋ��ֱ�^�ķ���(y��ng)��
����������(d��ng)��Ԋ��Խ��Խ?j��ng)]��˼���������
�����������ҕ��r(sh��)���Բ������������㲻���ٹ�������Ҷ��ܰ��ģ��lҲ���韩�����Կ����Լ��ăr(ji��)ֵ�������}�Ǖr(sh��)�g�L(zh��ng)�ˣ����ص���Ҳ׃���IJ����ɣ��]���˺��l(w��i)�r(ji��)ֵ�Ē����^�̡����磬���fһ��(g��)�|���ã����^�������´_����(n��i)�����еăr(ji��)ֵ����Ҳ���f����Ҳ���f���@��(g��)�r(ji��)ֵ��׃���콛(j��ng)���x���r(sh��)�g�L(zh��ng)�ˣ��f�õ����X�Û]����˼���f���õ���Ҳ�X�Û]����˼����(du��)��Ԋ�����u(p��ng)���ԣ��F(xi��n)�چ��}����߀�������u(p��ng)�������Пo�����Ǵ���Л]����x���u(p��ng)�r(ji��)���dȤ����(d��ng)Ԋ��׃���@�ӵĖ|���������źܶ��˶���(hu��)��ʧ���J����ʧ��������(d��ng)���������ĕr(sh��)����ζ���@��(g��)�|���ұ���R��̎���������̎�팦(du��)�Ҙ�(g��u)��һ��(g��)�pʧ�������e(cu��)ʧһ��(g��)�����J(r��n)�R(sh��)�Լ��ęC(j��)��(hu��)�������҂��挦(du��)��һ�N�����ǣ���(d��ng)��Ԋ��Խ��Խ?j��ng)]��˼���������Ԋ���Д�׃��ͬ��Ͳ�ͬ�⣬ͬ��]���}����ͬ��Ҳ�]���P(gu��n)ϵ��ȱ��һ�N��(n��i)�ڵĒ������^�̣�����Ч�ġ�ͬ�⡱����ͬ�⡱��(y��ng)ԓ�DŽ�(chu��ng)��r(ji��)ֵ���^�̡��r(sh��)�g�L(zh��ng)�ˣ���Ҷ���Ȼ�oζ�ĕr(sh��)��Ԋ����Ȼ��(hu��)͑׃��һ�N���Ļ����ɞ���������c(di��n)�Y�������f�Ѻ��@�ӵ�һ��(g��)���g���н�(j��ng)��(j��)��(b��o)�����ʘ���(b��o)������(d��ng)ȻҲ���������Ļ��͏d���ڽ�(j��ng)��(j��)���ʘ������a(ch��n)֮�⣬����ҲՄ?w��)�Ԋ�裬�mȻ�@�c(di��n)���ʵ�һ�c(di��n)��
��˪����������һ��(g��)�dz���Ҫ�Ć��}�������Լ��Č�������x���^���У���(du��)��(d��ng)��Ԋ����u(p��ng)�r(ji��)��(bi��o)��(zh��n)�����ѽ�(j��ng)����һЩ���������ġ�֪�R(sh��)�������ǿ��Լ��Է����ͷ�ʡ��Ҳ���l(f��)��׃��(d��ng)�������^ȥ�ஔ(d��ng)һ�Εr(sh��)�g��@��(g��)��(bi��o)��(zh��n)���ܶ�����٠��B�������^��ͼ����ϵġ��r(sh��)�С�����һ��(g��)�ض��r(sh��)�ڵ��ČW(xu��)�Շ�����(d��ng)Ȼ��һЩ�µ���Ҫ����Ʒ�İl(f��)�F(xi��n)��Ҳ߀����?y��n)������ܺ��҂��?d��ng)�µĠ�r��������ij�N�P(gu��n)(li��n)�����Ǖ�(hu��)�кܶ��ˏ��н��bһЩ�µķ����ͼ��ɡ��@����(hu��)׃��һ��(g��)�r(sh��)�ڡ�һ��(g��)�A�εČ����Շ����@Ҳ��(hu��)��(g��u)�ɻ�Ӱ푵����c���õ��u(p��ng)�r(ji��)��(bi��o)��(zh��n)�����������D���f��������⡱��һ��(g��)��Ʒ����f�ã�����Ҳ�����@��(g��)��Ʒ�������^����⡱��һ�����������µij������@��(g��)��������ֻ��һ��(g��)С������(n��i)�Ĺ��R(sh��)����Ҳ�������x�ģ��������䌍(sh��)������һ��(g��)�^��(du��)�ăr(ji��)ֵ�������Ѓr(ji��)ֵ�Д�Ľ^��(du��)�ԡ����Խ������ʡ�����X�����@������u(p��ng)�r(ji��)��(bi��o)��(zh��n)Ҳ�ƺ���һЩ׃�����@��(g��)׃�������ҬF(xi��n)���Еr(sh��)��ϲ�g����һ��Ԋ��Ҳ�S������?y��n)����ļ��ɶ�ô���r��������?y��n)����@��Ԋ���ṩ����ij�N��ͬ��˼����Ȼ����R(sh��)��B(t��i)��������҂�����������ij�N����̎�����������������ṩ����һ�N�������R(sh��)���@�N���R(sh��)Ҳ�S��δ�õ���ֵط�ʡ�����������@��(g��)������Ŭ���������x�ĕr(sh��)��͕�(hu��)���X����̫һ�ӡ��@���g��һ��(g��)ì�ܣ������Еr(sh��)���@�NԊ��(hu��)�@�ñ��^�����⡱��������߀���X�����Ѓr(ji��)ֵ����ӛ��90�����ƪ���u(p��ng)���������@��һ��(g��)�^�c(di��n)����(du��)��(d��ng)���Ї�(gu��)Ԋ����f����Ҫ�IJ������������dz��졣�@��90�����һ��(g��)����Ҫ�����R(sh��)���������҂�������һЩ�����ϵĻ��X���ڌ�����������졣���ҬF(xi��n)�ڵ��u(p��ng)�r(ji��)��(bi��o)��(zh��n)���dz��죬�������£���������������ͻȻһ�����^����������_��һ��(g��)����������һ�N���r�՚⡣
�����ߡ����F(xi��n)��(sh��)����l(f��)���o��(li��n)ϵ��Ԋ��ǡǡ�c�F(xi��n)��(sh��)���P(gu��n)(li��n)��
���������������Ҳ���F(xi��n)�˺ܶ���F(xi��n)��(sh��)����l(f��)���o��(li��n)ϵ��Ԋ�裬����ȥ������ĕr(sh��)�ͮa(ch��n)���˺ܶ�Ԋ����Ʒ����Щ��Ӱ�߀�ܴ����҂�(g��)�˸��X��������Ʒ�mȻ�P(gu��n)ע�F(xi��n)��(sh��)����ǡǡȱ��һ�N�������������R(sh��)�̓r(ji��)ֵ���R(sh��)�����F(xi��n)����ǡǡ���c�F(xi��n)��(sh��)�IJ��P(gu��n)(li��n)�����죬�@��һ�N��͵�Ԋ������(du��)������Ԋ����������һ�c(di��n)�����@����������⣬���ǹ������⡣
�������D�����f�^�����Еr(sh��)�]���|�^ʲô�F(xi��n)��Ԋ������x��W(xu��)���_ʼ�x���ֵğoՓʲô�ĬF(xi��n)��Ԋ����?y��n)鹤�Ƴ��������ϐ��^�棬��Ҫ������יC(j��)�����һ�Ӹ�����Ԋ�赽������ô��(g��u)�ɵģ�����Ҫ�fʲô���x�˺ܶ�F(xi��n)��Ԋ����ÿ�F(xi��n)��Ԋ��ò����̫һ�ӣ��ܶ��r(sh��)��dz�ʹ�࣬�o���m�ġ��Еr(sh��)���Dz�̫�����ǾͰ�������̎�����Ͱ�����(d��ng)���ܸ��F��̎������߀�ǰ��Լ����v�þ�ƣ���ߣ��·���һЩ��������ʲôҲ�������@���Լ�Ҳ�_ʼ����ͬ�r(sh��)�^�m(x��)�xԊ��߅�x߅����Ҳ������һЩ��(bi��o)��(zh��n)������l(f��)�F(xi��n)�@Щ��(bi��o)��(zh��n)��̫�ɿ���������Ҫ�Ć��}�ǣ������f���ҬF(xi��n)���ЛQԊ�ĺÉĸ��Լ����P(gu��n)�������Լ�ʲô���P(gu��n)�أ�����@��(g��)�Լ���ʲô��(g��u)���أ��Լ�Ҳ�f��̫�塣�ҬF(xi��n)�ںܶ��r(sh��)������Ϸŗ��xԊ�ˡ���(d��ng)Ȼ�����Dz����ף����Ǻ��ٰl(f��)�F(xi��n)�Լ�����(d��ng)��Ԋ�ˡ������}����Ԋ�裬�������X�����Լ���ś]�б��^���������˼��ăr(ji��)ֵ�^���Լ�ֻ���^�DŽe�˵đ�(zh��n)��(ch��ng)����M�ˡ����W�c�}��(d��ng)�����ѡ��w�Y(ji��)�������Ć��}����(ji��n)�ζ������ף���(du��)����߀������������δ�ز��挍(sh��)����һ�θ�һ����ӑՓ���}�����X�ú�����Ҫ��Q����Ԋ��Ć��}���������}���o���W�����X���˵Ć��}Ҫ��Q�ã�Ҳ�S���ܽ�QԊ�膖�}���Ү�(d��ng)Ȼ֪�������}�����@ôһ�֞��������߀��Ҫͬ�r(sh��)�m�p����Q���߲���Q���Һ��ߵĿ����Ը����ҬF(xi��n)�ڻ��������@�ӣ���Щ͵�У���̫����(d��ng)ֱ�ӏ�Ԋ������@���YԴ����(d��ng)����
�������裺������˪�ᵽ�����������R(sh��)�ġ��r(ji��)ֵ�^��Ԋ�������S���������һ��(g��)�������е�Ԋ�mȻֱ���漰���Σ�����ǡ����ȱ�����η�˼�ġ��ƺ�ֱ���漰����r(ji��)ֵ�Ć��}������(du��)�������r(ji��)ֵ���ϵĖ|��Ҳ��ȱ��˼���ġ��_���ᵽ��Ԋ�脓(chu��ng)����Ҫ���µ�����r(ji��)ֵ�^����(j��)���˽⣬�DZ���ֱ�ӳʬF(xi��n)��Ԋ���еģ����ǿ����ԵĻ��A(ch��)���@��(g��)����ăr(ji��)ֵ�^����ԭ�t��ʲô��
������˪�������Һͽ�������˼�������෴�ġ������f��ȥ������֮��ĺܶ�Ԋ����(d��ng)Ȼ�����P(gu��n)�ѣ���Ҳ���^һЩ�����Dz����������f�����£��ܶ�Ԋ��Ȼ����һ��(g��)��·�ϡ��@������қ]���f�����
���� �ˡ�ˇ�g(sh��)�����R(sh��)�ΑB(t��i)�K�Y(ji��)֮������y��
����ʒ�_�ޣ�����Ψ�����x��һ��(g��)ǰ�ᣬ���������v���Ǹ��X�������X�Ć��}���҂���ע������ɢ��ע�������ܼ��У����������ۡ��҂�̎�ھ����㱵Ġ�B(t��i)�����|���п����Ǟ���һ��(g��)�y(t��ng)һ��ʹ�Լ���һ�Εr(sh��)�g������Q�@��(g��)ì�ܣ�ע�������^���еؽ�Qì�ܡ����@�ﱾ������һ��(g��)���ڵ�ì�ܡ��������u(p��ng)Ҳ�Ǟ���һ��(g��)�Լ��������X���ǽy(t��ng)һ�ġ�߉���f���^ȥ��������һƪ���¡��Ҳ������҂��@ô������һЩ�dz��õ����u(p��ng)�������@Щ���u(p��ng)������þ�����ʲô���Ҳ����J(r��n)���u(p��ng)ʷ����?y��n)�l(f��)���^Ӱ푵ģ����Ěvʷ���ñM�ܿ��������u(p��ng)��������������(g��u)�ɬF(xi��n)��(sh��)���Ҿ��ǬF(xi��n)��(sh��)����Ψ�����x���]���ģ�һ��(g��)���ČW(xu��)�У�Ԋ���I(l��ng)��ˇ�g(sh��)������������棬�҂���һ��(g��)���R(sh��)�ΑB(t��i)�ĽK�Y(ji��)֮������y���҄����f���@�N����oɢ��r��ע���������Ġ�r����Ӌ(j��)�����R(sh��)�ΑB(t��i)�K�Y(ji��)ֱ�����P(gu��n)���@��(g��)���R(sh��)�ΑB(t��i)�K�Y(ji��)��(d��ng)Ȼ�����Ї�(gu��)����r������ȫ�������r�������������(zh��n)�r(sh��)�ڌ�(du��)�O��(qu��n)���x�����У�֮�������R(sh��)�ΑB(t��i)�K�Y(ji��)����Փ�������҂��@߅���КvʷΨ�����x���q�C����һ�Εr(sh��)�g�DZ��^���\(y��n)�ĕr(sh��)�ڣ�����(du��)�����ˣ�Ҳ���ԏ�������(du��)�Č�(du��)��@���Լ��ăr(ji��)ֵ�^���@���Լ������R(sh��)�ΑB(t��i)�������Ե����R(sh��)�ΑB(t��i)����������߀�Ǜ]������h����(du��)�����R(sh��)�ΑB(t��i)��һ��(g��)�Ё�Դ������(ch��ng)����������?y��n)鷴�?du��)���@�Õ��r(sh��)������(ch��ng)���M���@��(g��)����(ch��ng)��Ҫ���ܱ��^�ɿ������u(p��ng)���M�ܕ��r(sh��)�Եijɹ��ǿ�������ġ�
����������(ch��ng)���Ё�Դ�������u(p��ng)�ij��l(f��)�c(di��n)�����u(p��ng)�Ϳ��������ȡ��@���nj�(du��)Ԋ������u(p��ng)������Ԋ��������������u(p��ng)������ˇ�g(sh��)��Ʒ������Ҫ���������u(p��ng)���F(xi��n)��ˇ�g(sh��)�^�ɵ���(d��ng)��ˇ�g(sh��)������Ҫ��һ��(g��)׃�����ǣ���(d��ng)��ˇ�g(sh��)���������һ�N���u(p��ng)������(ch��ng)����(d��ng)��ˇ�g(sh��)��(qi��ng)�{(di��o)ˇ�g(sh��)�������(hu��)��һ��(g��)�ɆT�����Г�(d��n)�����f��(y��ng)ԓ�Г�(d��n)����������һ��(g��)�ɆT���c�������������P(gu��n)ϵ������Ҫ�O(sh��)������@��(g��)���(hu��)�P(gu��n)ϵ�ķ������҂���������P(gu��n)ϵһֱ��Ҫ���ơ�
�����҂�?c��)�ë�ɖ|�r(sh��)����һ��(g��)�y(t��ng)һ�ģ���ҟoՓ���Ă�(g��)�Ƕȡ����̶Ƚ��ܵ�Ψ�����x���ҽ����ˣ������f�қ]����ô���ѵؽ����ˣ����������˺������ĚvʷΨ�����x�đB(t��i)�ȣ���(du��)���Լ������(hu��)�����ıO(ji��n)���B(t��i)�ȡ�����҂�����һ��(g��)�A�Σ����һ��(g��)�vʷ��(ji��)�࣬���Еr(sh��)�������һ��(g��)����Ěvʷ��(ji��)�࣬���Ǵ�����������vʷ�Ĺ�(ji��)�ࡣ�҂�����80��������ܰ�؈��؈��ץס����ͺã��ŗ������R(sh��)�ΑB(t��i)�Ĺ̈�(zh��)���҂��M(j��n)����һ��(g��)ץסʲô�|���ĕr(sh��)�����@��(g��)ץס�����ǽ�(j��ng)��(j��)�I(l��ng)��Ҳ�����ǹو�(ch��ng)�ϣ�����Ҳ������һ��(g��)����Ҏ(gu��)���������f��Ҫ�M(j��n)ʲô�W(xu��)У����һ��(g��)ʲô�ط��������@�ӵęC(j��)��(hu��)Ҫץס�����������(hu��)�����w�F(xi��n)�ñ�С�f��Ԋ������߀Ҫ��֣��҂�����Ҫץסʲô���Ҍ��^һ��Ԋ�С�ץס������w�����@��(g��)��Դ�ҹ�Ӌ(j��)߀����ֱ�Ӂ�Դ��߀����80������R(sh��)�ΑB(t��i)�_ʼ���F(xi��n)�հķ���(y��ng)��һ��(g��)������Ȼ�ķ���(y��ng)���ҹ�Ӌ(j��)������(gu��)Ԋ��Ӱ푡�����(gu��)Ԋ���濂�Ǐ�(qi��ng)�{(di��o)Ҫץסʲô���Ҍ�Ԋ������(gu��)Ԋ�ܴ��Ӱ푡�ه�،��ģ����f���������T���ڕ�Ұ������һ�c(di��n)���F����һЩ�R߀��ţ���F�����[���F(xi��n)��ͻȻ�����F�����X˯��(m��ng)���Ƅ�(d��ng)��ɢ�_�������X��һ�N��ŵ����������f�����@��(g��)�r(sh��)���ҿ���Ó���ҵ��|��������͕�(hu��)ŭ���绨���@��Ԋ��(d��ng)�r(sh��)�o�ҽ�ŵĸ��X�������ҽoץס�ˣ�������(gu��)Ԋ��(j��ng)���ᵽҪ��ʲôץס������������˼��һ�ӵġ�ץסһ��(g��)��ŵęC(j��)��(hu��)�����X�ñ�����ץס��(sh��)�ڵĖ|�����Ǹ���һ�ӵ�ץס����˼���ڽ�š����l(f��)�����x�ϣ���ץס�C(j��)��(hu��)����˼��
�š���(d��ng)��Ԋ����Ҫһ��(ch��ng)˼���\(y��n)��(d��ng)��
�����@������һ���ĕr(sh��)��90��������Ј�(ch��ng)�Ժ��Ї�(gu��)���˼������罛(j��ng)��(j��)һ�w���C(j��)�����҂�ץס�@��(g��)�C(j��)��֮����һ��(g��)ʹ��ĽY(ji��)�����F(xi��n)���҂��ѽ�(j��ng)ץס��һ�У�������l(f��)�F(xi��n)ʲôҲ�]��ץס�����磬�҂�������ô��Ԋ�������ѽ�(j��ng)ץס�˺ܶ��˼�룬��˼�������x����ijһ��(g��)ȡ���^���@Щ�|�������x�̓��F(xi��n)���sʹ�����@����˵�ģ��ɿɡ������أ��͕�(hu��)���]һ��(g��)���}���҂������ѽ�(j��ng)�W(xu��)��(hu��)�����顪�������f����(gu��)������M�ɵć�(gu��)�҆ᣬ����(gu��)�˿��nj���y(t��ng)һ���W�����ǽy(t��ng)һ�ģ��e���˿��³��F(xi��n)�ԺW����һ��(g��)��(g��)�w�M�����w�ĵط�������?y��u)��ˏ?qi��ng)�{(di��o)��(g��)�ԣ����ˏ�(qi��ng)�{(di��o)�����(d��)�����e(cu��)λ�ĕr(sh��)�������������飻����(gu��)��Դ���顢���Խy(t��ng)һ����ͬ��Դ����ͬ���塢��ͬ�wɫ���ˣ������J(r��n)ͬһ��(g��)�y(t��ng)һ�ԣ��@��(g��)�y(t��ng)һ�������ǵġ�����80������҂��������ˣ��ĸ�]�б�����Ė|����������������@�˵�˼�뷽ʽ���c�£��҂����Լ������ˡ��ɹ���ʹ�Լ�����ɞ���Ƭ���@��(g��)��Ƭ������ճ�ϵĕr(sh��)�����Ҳ����ݺ����]�Џ�(qi��ng)�������ݺ����҂���Ҫ���Լ������Ե�߀ԭ��һ��(g��)�y(t��ng)һ���ˣ��y(t��ng)һ�����w���y(t��ng)һ��˼�������ĕr(sh��)�]���@�N�ݺ����ҹ�Ӌ(j��)�҂���ͬ�к�폊(qi��ng)�{(di��o)���w����Ҫ�ԣ�90����Ժܶ��ˏ�(qi��ng)�{(di��o)���w����Ҫ�ԣ���(qi��ng)�{(di��o)֪�R(sh��)���ӣ���(qi��ng)�{(di��o)���g����(qi��ng)�{(di��o)���w������һģһ�ӵģ����Ǐ�(qi��ng)�{(di��o)���w����Ҫ�ġ����g��(qi��ng)�{(di��o)���w��ֻ���^���g�X���������ؽy(t��ng)һһЩ������һ��(g��)���o(h��)�ӵ��£�����̎��һ��(g��)�����ڽy(t��ng)һ�ĵ�λ��֪�R(sh��)������߅����������������ĵط������Ǐ�(qi��ng)�{(di��o)ij�N�������Ҫ�ԣ�����չ���Զ����Ǹ���(j��)�ԡ�������ĽǶȣ�����(j��)ʲô���ҵ�ʲô�y(t��ng)һ�������ҵ�ʲô�y(t��ng)һ��Ҳ�����ҵ�ʲô��(w��n)��������(ch��ng)��Ҳ���܌���ʲô�нy(t��ng)һ��־��Ԋ�裬Ҳ���܌�(du��)ʲô�|���l(f��)����������Ҋ�������o�Ǿ���߉�����������ĽǶ���ô��(sh��)�F(xi��n)�����أ�
�����҂�ÿһ��(g��)�˶���һģһ�ӵġ��҂�ÿ��(g��)�����@��(g��)���w�Ļ��A(ch��)�������҂�ֻ�ǿ������w�����߰��҂���˼����Ը���ij��l(f��)�c(di��n)ͣ�������w�@һ��ĕr(sh��)��(sh��)��Ҫ��һ��(g��)�����Ե��ݺ����]�С��҂��Һ���һ��(g��)�e�Ė|����ʹ�҂��܉����R(sh��)���҂������R(sh��)���������Һ����@��(g��)�|���ڣ����������Ƭ���������ĸ���(j��)���@��(g��)�ط�����ʹ���zˮ�ĵط�������ʹ�������ԵĖ|�������R(sh��)�ΑB(t��i)�ĽK�Y(ji��)�����������v�ģ�߀���҂��v�����R(sh��)�ΑB(t��i)�Ŀհף��҂��]�����f������̎���@�ӵĿհ��A�Σ��҂����ԏ��@��(g��)�ط��_ʼ�������҂������R(sh��)�ΑB(t��i)��Ԋ����Ҫһ��(ch��ng)˼���\(y��n)��(d��ng)��������Ԋ�裬������Ҫ����Ԋ�裬��Ҫ�Ǟ�������(du��)���õĹ�ͬ�����ô���γ�һ��(g��)���������^��(g��)�w������r(ji��)ֵ�^֧�����^��(g��)�w���γɡ��]���@��(g��)�����^��(g��)�w�o���γɡ��҂�?n��i)���v���w�������v�Ŀ��^��(g��)�w�����ǿ��^��(g��)�w�����������R(sh��)����ô����������(d��ng)�����R(sh��)����ô����������(d��ng)��˼������ô�����Ъ�(d��)�����ДࣿҲ�����f��������ܘ�(g��u)��һ��(g��)���^�����@Щ�����ԵĿ��^��̫���ܷ�ֳʲô�ČW(xu��)ˇ�g(sh��)�Ŀ��^���ČW(xu��)ˇ�g(sh��)�Ǐ����^���Ė|�������^�ڄ�(d��ng)�����^Ŭ���ĽY(ji��)�����ČW(xu��)ˇ�g(sh��)��Ʒ�Ŀ��^�����������������^���܇���
�������裺���Dz����f����̫���܌��ҵ��������zˮ����Ҫ��һ��(g��)�ζ��ϵ��zˮ��������֮�»���֮����zˮ��
����ʒ�_�ޣ��zˮ�����á�˼���ķ���������һЩ�r(sh��)����ҪһЩ�zˮ�����γ����^��(g��)�w�ĕr(sh��)�����X����߉���á�Ҫ��߉�������v�п��{(di��o)Dz�ĸ������@Щ�|���������^��(g��)�w�������γɺ����ɵģ�Ҳ����һ���Ե��γɵģ��Dz�����γɵġ����γ����^��(g��)�w���^���У�һ����(hu��)�ܶ�ĕr(sh��)������ì�ܣ��ܶ�����ҷ��ܶ�đ��ɣ��ܶ��ͣ�����������^·�����ˡ��˿�����?y��n)�����ʲô��������������(y��n)�������������(y��n)��Լ�ij�N����?xi��ng)l��������׃�����l(f��)����(n��i)�ڵĪqԥ���������������µ����ҷ��ѡ�����һ��(g��)�r(sh��)�ڕ��r(sh��)�ҵ�������(du��)�������������R(sh��)������˼�������DZ�һ��(g��)����IJ��ɱ���đ��ɴ��飬���ҵ����ٴ��飬���ҵ��@��һ��(g��)�����ԣ��@��һ�N�µĿ��ܡ��v��Ψ�����x�������f��һ��(g��)�dz���(w��n)��������r(ji��)ֵ�^�܉�һ�����ҳ��������ǂ�(g��)�ط����h(yu��n)���á������@��(g��)���҂���һ��(g��)�γ�����r(ji��)ֵ�^��Ψһ��ԭ�t����ʲô�vΨһ��ԭ�t����?y��n)�r(ji��)ֵ�^�S�r(sh��)�S��ÿ��(g��)�˶��Ѓr(ji��)ֵ�^�������Ǹ���(j��)�@��(g��)�r(ji��)ֵ�^���ֳ�Ĭ������߀��˯���X��߀�����������Ԛ�߀�DZ�����Ū�����҂�ÿһ��(g��)�˶���(hu��)��?y��n)��@Щ��(sh��)�Ãr(ji��)ֵ�^�����Լ����x��ͷ���(y��ng)��������(du��)ʲô���������R�r(sh��)�����ӣ������@�ӵăr(ji��)ֵ�^֧�������Մ������߄�(chu��ng)�졣ֻ�г�������֧�䌍(sh��)�Ãr(ji��)ֵ�^������r(ji��)ֵ�^֧����˼�����Є�(d��ng)���Z�ԣ��ſ���������ġ����O(sh��)�Եăr(ji��)ֵ���F(xi��n)������r(ji��)ֵ�^������(sh��)�Ãr(ji��)ֵ�^�������γ�����Ψһԭ�t���ڽ̡��܌W(xu��)������ͨ�^�ČW(xu��)��˼��������Ŭ�����ˣ������������������ˣ������ѽ�(j��ng)�ṩ��������������܉���ԭ�t���������ɗ��Ą�(chu��ng)�¡����������nj�(du��)��������Ŭ������(du��)���^�͵ȵķ���Ҳ��������ô����(chu��ng)�º͍��¡�����(j��)�����ṩ�o�҂��Ľ�(j��ng)�(y��n)���҂�?c��)ٷ�ʡһ�¡��γ�����r(ji��)ֵ�^ֻ��һ��(g��)ԭ�t���@��(g��)Ψһ��ԭ�t�ֳɃɂ�(g��)��͡�һ��(g��)��ͣ���(qi��ng)�{(di��o)���(y��n)�ԡ���(qi��ng)�{(di��o)һ��(g��)���Ƚ�(j��ng)�^˼��ͬ��ĵ�������ԭ�t���������¡�߀�ǡ�����һ��(g��)��͡����҂��ȷŗ�һ�С������Ϳ������ʲô�|������һ��(g��)��(j��ng)�(y��n)��������(j��)�@Щ��(j��ng)�(y��n)�ٿ��Y(ji��)��һ��(g��)���������Y(ji��)��һ��(g��)�������ָ��(d��o)��Ҋ��ȥ���¡������ϵ�ָ��(d��o)ԭ�t�o���@�ɂ�(g��)���҂��ķ���Ҳ�����@��(g��)�ط������綼��һ��(g��)�W(xu��)��(x��)���������DŽe�ġ�����Ҫ��Ψһ�ġ����ƵĖ|�����@��(g��)��Ψһ�����@���治��һ��(g��)�����������ǰl(f��)����
�������裺����뷨���뵽�˃ɷN��ͬ�Ă����ΑB(t��i)��һ�N��Ҏ(gu��)���Եģ����(y��n)Ҏ(gu��)���ģ�߀��һ�N�ǽ�(j��ng)�(y��n)�γɵ������Եġ����ᵽ��Ψһ������r(ji��)ֵ�^��Ψһ������ʲô����߀�X�ò�������@��(g��)����r(ji��)ֵ�^��ԭ�t������ʲô�������f�����С�����������ʩ���ˡ������°����ԭ�t���T���������ƏV�������ˣ��ܲ����ټ�(x��)��һ�£�
����ʒ�_�ޣ��Ȳ��fΨһ��һ�����^��(g��)�w�������γ���һ��(g��)Ψһ�ĽY(ji��)�֡�����˽�ĽǶȣ��ȏ����ҵĽǶȣ��@��Ψһ��ԭ�t���@���˺̈́e�˴���һ��(g��)�����������҂��f���^���Ҫ�Ƿe�O��Ԓ��һ����Ҫ���]����(y��ng)ԓ��һ��(g��)���������^��(g��)�w�����������^��(g��)�w�܉����ĭh(hu��n)������ͬ���õ�����@��һ��(g��)���(hu��)���@��(g��)���(hu��)��(y��ng)ԓ���������ԁ��O(ji��n)��ǰ��Ė|�������^�����^��(g��)�w��ʹ�����Ǟ��˹�ͬ���õ������γɡ���?y��n)����^��(g��)�wҲ�����Dz��ܿ��Ƶġ�
�������_�ބ����P(gu��n)������r(ji��)ֵ�^�IJ���չ�_�ķdz���֡������a(b��)��һ�c(di��n)���������v���ġ�ץס�����@��(g��)�~������˼�����Ǐ�(qi��ng)�����ģ�ָ�������ض��ĕr(sh��)����Ҫ��ijЩ˲�g���@��ȫ�µĸ��X���ǂ�(g��)˲�g�������Eһ�ӡ������҂��벻�������E���䌍(sh��)�ڮ�(d��ng)��Ԋ�������(d��ng)��ˇ�g(sh��)�У��@��(g��)���E��˲�g��ץס��˲�g��������ˇ�g(sh��)��ǰ�ᣬ�����@�ӵ�˲�gҪ����Įa(ch��n)�������ܘ�(g��u)��һ��(g��)��(chu��ng)���О����ɡ��ڮ�(d��ng)��Ԋ������һ��(g��)��Ҋ���f�����Ǿ����҂�Ҫ�����Z�ԵĿ����ԡ����^�Z�ԵĿ��������Z�Բ����ץס˲�g�������ጷš�����ظ��£��䌍(sh��)�Z��Ҳ��һ�N���^��Ҳ�����|(zh��)�ԡ������Ե�һ�N���ӡ���(du��)�Z�Կ����ԡ���(du��)���w�����Ե����Σ�����ij�Nͬ��(g��u)�ԣ�Ԋ�����������w���Z���а������o�F�����E�Ŀ��ܣ��Q��Ԓ�f��Ԋ�˰��Լ����o�˿��^�ԣ��������S�r(sh��)ӭ�����E�����@��������һ�N���ԡ�����(d��ng)����?y��n)��Ұ��Լ����o���ǂ�(g��)˲�g�����o���ǂ�(g��)ץס���^�̡����@��(g��)�^���У��ҵ����^���������˸�����(ch��ng)���r(ji��)ֵ����(ch��ng)���D��������ʧ�ˣ����ĽY(ji��)���Ǯ�(d��ng)�^���˲�g�ѷeһ���҂�����ץס�Ė|����һ�ӵġ���(d��ng)��Ԋ�ˌ����@ô���Ԋ�裬��(du��)�˵ĸ��N�����r������˶�ı��_(d��)���������еĕr(sh��)���҂�߀�Ǹ��X�@Щ��(j��ng)�(y��n)�ijʬF(xi��n)Ȼ�Ǻܜ\¶�ġ�����ͻ��ģ��P(gu��n)�I�����҂�?n��i)�ʧ��һ��(g��)��(qi��ng)���������^�y(t��ng)�z�����ԣ���ô��Ó���w���Z�ԵĿ��^�ԣ��@�����Ǹ���Ҫ�ġ�
��˪���_������ġ���Ψ�����x�������B�����ܶ��|���������f��Ψ�ġ��@��(g��)�~�������Ї�(gu��)���y(t��ng)���е��Z�R��(du��)�����܌W(xu��)�еĸ�����Է��g����ô���͎������Ї�(gu��)˼����y(t��ng)�е�һЩ�|�����f��Ψ�����x����(du��)�ڬF(xi��n)��Ԋ����f���䌍(sh��)Ҳ���˷dz���̵�Ӱ푣������(gu��)�����ɺ�Ψ�����x�\(y��n)��(d��ng)֮�g���P(gu��n)ϵ�������҂���(du��)Ԋ�����������S�У���Ȼ߀�܉��@�NӰ푵ĺ��E�����@��(g��)���A(ch��)�ϣ��ҷdz�ͬ�ℂ���_�Ľ�ጡ��ҿ��ܛ]�н����������ô����X�ÏĂ�(g��)�w��(j��ng)�(y��n)�ρ��f��Ҳ�Ĵ_�܉���X���@Щ���}�Ĵ��ڡ��҂��^ȥ�ŷ�ĚvʷΨ�����x�ѽ�(j��ng)���҂������R(sh��)�ΑB(t��i)�нK�Y(ji��)������ֻʣ�������w��׃���ˡ�Ψ���w���x�������oՓ��������߀���Ї�(gu��)����(du��)���˵Ķ��x����Ҫ�������w�Ĵ��ڵģ���t���c�ݫF�͛]ʲô��һ���ˡ���������f�ČW(xu��)߀�����������c���˘�(g��u)�ɵ����(hu��)�и��õĴ��ڣ��Ĵ_Ҫ���@֮����һ��(g��)����һЩ�����c(di��n)��
�������������v�����w���x���ҵ�����Q��Ԓ�f���ǙC(j��)��(hu��)���x����ij�N�֜\�����ϡ�ͨ�^׃����˲�g��ͨ�^�������ͨ������ķ�̖(h��o)׃�ήa(ch��n)������Ŀ�У��������ʧ��ij�N�Y(ji��)��(g��u)�Ե��������@�ӿ�б���Ҳ�Ǜ]���f�����ģ������dž��{(di��o)�ġ��@�ӵęC(j��)��(hu��)���x�����H���F(xi��n)����ˇ�I(l��ng)���ڮ�(d��ng)���Ľ�(j��ng)��(j��)�I(l��ng)�������I(l��ng)��˼���I(l��ng)������Ƶ�߉��
�������D�����Ž����c��˪��λ�f�ĺ��ء����҂�(g��)�ˁ��f�������a(b��)��һ��(g��)���P(gu��n)ע�����ġ��Ҹ����P(gu��n)ע��(g��)�����w�Ć��}��Ҳ���������Ă�(g��)�����w��ν��������P(gu��n)ϵ�Ć��}����ǰ���X���Լ�Ŭ����Ŀ��(bi��o)�����DZM���Լ������w����(d��)һ�o�����c����ͬ��������X���������ܑ{��(g��)�˽�(j��ng)�(y��n)�����@��(g��)��(d��)���ԡ��B�Լ��Dz���һ��(g��)���w���Dz���һ��(g��)���������w������M���ɡ��F(xi��n)�ڵ��X�Â�(g��)�����w������ǡ���Ǻͽ������������Ĺ����P(gu��n)ϵ�Ǿo��(li��n)ϵ��һ��ġ��҂��^ȥ�����Ĺª�(d��)��(g��)�w���䌍(sh��)Ҳ������һ�N�����P(gu��n)ϵ�������@Щ�����P(gu��n)ϵ����(sh��)�H���ǽ��������҅^(q��)���ģ��@��(g��)���Ĺ����P(gu��n)ϵ��(sh��)�H���������҂������w���������@Щ���ԵĹ����P(gu��n)ϵ�������҂��M�⡣����뽨��һ��(g��)�����Ă�(g��)�w�����ܸ��ƬF(xi��n)�ڹ����P(gu��n)ϵ�����|(zh��)���ǘӪ�(d��)�������Ƶ��������w�ſ��ܸ��õĽ������������Ľ��������P(gu��n)ϵ�����(hu��)���ȁ������������ƵĹ����P(gu��n)ϵ��(sh��)�H����ԇ�D�����ˡ���׃?n��i)��c��֮�g���P(gu��n)ϵ���������c������P(gu��n)ϵ���Ķ�Ҳ�ܸ�׃�҂������(hu��)��ʹ�҂��ܳ���һ��(g��)���õ����(hu��)Ŭ����
�������裺�����������ᵽ����Ψ�����x�\(y��n)��(d��ng)һЩ���ܵā�Դ����������҂�����һ�¡����ā�Դ���Ї�(gu��)���y(t��ng)���f�ϡ����졢�����߀�ǵ�(gu��)�ŵ�Ψ�����x��߀���^�кͺ���(y��ng)����Ψ�����x�Ă��y(t��ng)��
����ʒ�_�ޣ����ā�v�ǬF(xi��n)����R(sh��)�ΑB(t��i)�K�Y(ji��)�����ĬF(xi��n)��ڶ���(g��)��ֱ�ӵ��P(gu��n)(li��n)����Ψ�����x����?y��n)�Ψ�����x��һ��(g��)�y(t��ng)��һ��(g��)�A�������˵����R(sh��)�Ė|�������X���ڿ��]���}�ĕr(sh��)��һ������ؿ��]������߃r(ji��)ֵ������׃�ο�����һ���ӑՓ��˼�������ԣ���һ�ǬF(xi��n)��ڶ���Ψ�����x�����ĬF(xi��n)������YԴ���@��(g��)�YԴ�ҷdz���Ҫ���F(xi��n)�ںܶ����ڿ��]�Ї�(gu��)���y(t��ng)����D�֏�(f��)�Ї�(gu��)���y(t��ng)������(y��n)�������f��ô�^��(ji��)����ô���·�����ô��һЩ�ش�ăxʽ����?y��n)��҂�������ʲô�?ch��ng)���fʲô�ӵ�Ԓ���О��eֹ���@Щ���Ƿdz��o�ȵģ���?y��n)��҂���IJ�֪����ʲô�?ch��ng)��ԓ�fʲôԒ����(du��)��ĸʲô����һ��(g��)��ǡ��(d��ng)?sh��)ķ�ʽ�������@Щ�|���������γɃr(ji��)ֵ�^��ԭ�t���ø������҂���(d��ng)Ȼ���γɃr(ji��)ֵ�^��ԭ�t�����Ǐ��@�ӵĽǶȲſ��]�҂��Ă��y(t��ng)����t���μ�ӑՓ�҂��Ă��y(t��ng)��Դ�����J(r��n)�������c(di��n)����(w��n)��
�������裺������y(t��ng)�еĶY���������������҂�����(g��)���ճ�����Y(ji��)�ϵ÷dz��o�������ڽ�Ҳ����ˣ������ṩ�ăr(ji��)ֵ�^�����γ��˃xʽ���ƶȡ������������r(ji��)ֵ�^����������r(sh��)��˼���\(y��n)��(d��ng)�������������ă���߀�����փH�H��һ��(g��)���И��w��
����ʮ�������߲��Ǹ����(w��)�I(y��)�����Ǟ��������� �X�����X��
����ʒ�_�ޣ��������v���������@�ӵ�Ŭ�������X�����@�ӵ�Ŭ���п����ڛ]�����^�Д�����˼����������r�£���������һЩ����(w��)�I(y��)�����ǰ��҂��^ȥ�Ă��y(t��ng)�Ļ��еĺ��˲����ؕ�I(xi��n)׃�������ó��������f���y(t��ng)�YԴ�ĕr(sh��)���Һܻرܰт��y(t��ng)�YԴ׃�����ס���һ����Ҫ���c��˼�������c���˵Ē����͌����Ё����@��(g��)�r(sh��)���������ˣ���Č�(du��)�˸������Լ��Ĵ��������á��@��(g��)�r(sh��)���@��(g��)���y(t��ng)���á���t��Ԓ����׃������һ��(g��)�����(xi��ng)Ŀ������⡣����Ұ��@��(g��)�����ˣ��ҾͿ����v���҂��v��Ψ�����x���^ȥ���YԴ���п��ܼ��뵽�҂����ڵ����R(sh��)�Ё����ҿ��ܕ�(hu��)�����{(di��o)��(d��ng)���e��Ҳ�����{(di��o)��(d��ng)�e���YԴ���ҿ��^һ�c(di��n)�ŵ��܌W(xu��)�������D������赵ؿ��]���}������(y��ng)���]���������������ѽ�(j��ng)�ѷ��Ҳ�C�ϵ�������ˣ���̵�ϵ�y(t��ng)�ԣ��ܾC�ϣ��F(xi��n)��IJ�����C�Ͽ��¡���(gu��)�����^Ψ�����x���䌍(sh��)Ҳ����ʲô���r�����飬����֮�g�п��ԽY(ji��)�ϵĵط����Y(ji��)�������ͳ��ˬF(xi��n)���ij��ɶ��졣���ҿ�������(gu��)�ŵ�Ψ�����x���ӏ�(qi��ng)�{(di��o)���^�����������҂��������ԁ����Ă��y(t��ng)���ӏ�(qi��ng)�{(di��o)���^���S�M���������S�M�Ǻܲ�һ�ӵ��O(sh��)Ӌ(j��)�����Լ��䌍(sh��)�]�п��]��ô�����һ��(g��)�K�OĿ��(bi��o)���Ҳ�ȥ���@��(g��)��
������Ұ����҂���Ԋ߀����ˇ�g(sh��)���Ǟ��˞�o�˽���һ��(g��)���ĵ�����̎���@��(g��)�Ҳ��룬���P(gu��n)�ĵ����@��(g��)������һ��(g��)�ˣ������R(sh��)�����Լ����F(xi��n)�������@����������������߲��Ǹ����(w��)�I(y��)�����Ǟ��������� �X�����X���x���܉����������õ������ķ���(w��)�ǣ��@��(g��)���������ҡ����l(f��)�ң����s��ע����Լ����@���˲���ģ����п��������ķ���(w��)�����������Եģ�Ԋ�˲��Ǹ��@��(g��)�����@��(g��)�Ƕ��v���Ҹ��dȤ�ģ���ʲô�v��Ψ�����x�������ѹŵ�Ψ�����x���^�����������ČW(xu��)������W(xu��)������Ҹɵó�ɫ̫���ˡ��ұ��^ע��ľ��ǣ������njW(xu��)�����ģ����njW(xu��)���ģ����njW(xu��)���t(y��)�ģ��ǘ��،�(sh��)�W(xu��)�Ė|�������P(gu��n)�ăr(ji��)ֵϵ�y(t��ng)��һ��(g��)��ĥ�p�Ŀ��g�����һ��(g��)�r(ji��)ֵ�^�]��һ��(g��)��ĥ�p�Ŀ��g�����͛]��ʹ�õĿ����ԡ��κ�ʹ�ö���ĥ�p���Ұ������Ľ���Σ�C(j��)����һ��(g��)�r(ji��)ֵϵ�y(t��ng)�����ÿ��g��ĥ�p���˘O�ޣ�������Ҫ�{(di��o)����������߸��ƣ���Ψ�����x�����R(sh��)�ΑB(t��i)�dz���ߣ�������ô���һ��(g��)���y(t��ng)�����������ġ����Ї�(gu��)���ģ�������Փ��Ҳ�ã����dҲ�á���ʲô������ë�ɖ|�r(sh��)���Y(ji��)�����Y(ji��)�������J(r��n)�����������ÿ��g�ѽ�(j��ng)�����ˡ���Ҳ�S����չ�����«@�����ã���һ��(g��)�r(ji��)ֵ�����ÿ��g��Ҫ��(ch��)���ஔ(d��ng)?sh��)����������������ī@����Ҫ�ܴ�����ģ���Ҫ�ܶ����(y��n)�C���ĽY(ji��)��(g��u)������ע������ö������档���ԣ��҂��v�F(xi��n)�ڼ�Ȼ��һ��(g��)���R(sh��)�ΑB(t��i)�Ŀհ��ڣ����҂��ČW(xu��)ˇ�g(sh��)�ļ�����ҕ�����|(zh��)������������ҿ�������Ψһ��������������e�O���ɵ�ֻ����Ψ�����x������ǰ���f���ģ��������P(gu��n)ϵ���@��(g��)�P(gu��n)ϵ�dž��l(f��)�Ե��P(gu��n)ϵ���������^�е��P(gu��n)ϵ�����P(gu��n)�ĵ����γɣ���ͬ�������ء���Ҳ�S��������ء����γ�һ��(g��)�����ÿ��g�����(hu��)���@��һ��(g��)���^�D�y���x��
�������裺��ˇ�g(sh��)���棬�����ЈA���@�����f��798�������л����ĕr(sh��)���������γ��ƶȵĕr(sh��)��(d��ng)���ˇ�g(sh��)�Ј�(ch��ng)�ѽ�(j��ng)��Ʒ�����@�N�̶ȣ������ڬF(xi��n)�ɵ��ƶ����ƏV��F(xi��n)���ѽ�(j��ng)��һ��(g��)���|(zh��)���x��Û��ˇ�g(sh��)�h(hu��n)�����Ļ��������S��S��Ū���ėl���£������(du��)�ƶȌ���]��һ��(g��)���죬ͨ�^�ׂ�(g��)ˇ�g(sh��)չ���㌍(sh��)�F(xi��n)Ψһ����r(ji��)ֵ�^�п��܆
ʒ�_�ޣ��@���놖�}�����������ǷN�ƶȵ����(hu��)���h(yu��n)����Ҳ�����O(sh��)�룬�����O(sh��)��һЩ�����A(ch��)�����顣�����f�҂�һֱ��ˇ�g(sh��)���W(xu��)�g(sh��)����һ��(g��)���҂����ܰl(f��)���P(gu��n)ϵ�ĸ�̎���@��(g��)λ���Ƿdz�����������O(sh��)Ӌ(j��)�������҂�һֱ��ӑՓ���ǣ���(du��)�@��(g��)�O(sh��)Ӌ(j��)���M�⡣�҂���ҪԊ�衢ˇ�g(sh��)���W(xu��)�g(sh��)���(d��ng)������һ���Ŭ�����@��һЩ�˵�Ŭ���܉����һ��(g��)��ͨ�ĭh(hu��n)�����棬��(d��ng)��һЩ��ͨ������팦(du��)������(d��ng)������(j��ng)�팦(du��)�����������Ҍ�Ԋ�Ǟ������Z�������һ�B�������^�����^����ijһ��(g��)�F(xi��n)����ô�@ô�����ǣ�������Ҫ���@Щ�ط������˺��ˡ���˼��������������ķ��棬������ͨ���P(gu��n)�ԡ��@��һ��(g��)���A(ch��)���]���@��(g��)���A(ch��)���O(sh��)��һ��(g��)��Խ�@��(g��)���A(ch��)������Ŀ��������ƶȣ���(sh��)�H��̫���ܡ������ǿ��ܣ�����Ԍ������������a(ch��n)���Ї@֮��Č�(sh��)�H���x��
�������裺��߀��һ��(g��)���}�����ᵽ�˽������^���ҵĆ��}���@��(g��)�����c90����_ʼʢ�еĂ�(g��)�����x��ʲô��e��
����ʒ�_�ޣ��f�����^��(g��)�w���^��һ�c(di��n)��
�������裺����(j��)�ҵ����⣬�������r(ji��)ֵ�^��������Ҍ�(du��)���˵�؟(z��)�Σ������˹����ĺ��x���@�(g��)�w��Ⱥ�w֮�g���B���������γɵģ�
����ʒ�_�ޣ����Ү�(d��ng)Ȼ����Û�ġ����������v�������Ć��}�������҂��ě]�з�������ʲô�����������кܶ࣬������Û�@�N���������^��(g��)�w���x�����������ƥ��ġ���ʲô����Ҳһ�ӣ��҂������٣��ҹ�Ӌ(j��)��˪Ҳ��һ�c(di��n)������Ҳ��һ�c(di��n)���ҽ�(j��ng)���]���x����������?y��n)�C(j��)��(hu��)�����������ɂ�(g��)�������ĕr(sh��)�Ϳ����Լ�׃��ū�`����Ը���������О��ū�`���@��(g��)���^��(g��)�w����܉�������ҹ�Ӌ(j��)�����г���ĺ�����
���裺�㲻�X���ڽ̵�;��������������ֹ���ڽ�һֱ���ṩ����r(ji��)ֵ���YԴ����һ��(g��)�������(hu��)����������������(hu��)�����µăr(ji��)ֵ�^�
����ʒ�_�ޣ����Ǿ�������h(yu��n)֮�Ă��y(t��ng)����ġ���]���@��(g��)���\(y��n)ȥ����ij�N�ڽ̵�ϴ�Y���]�������C(j��)�������Ҫ�ڂ������(hu��)���ҵ�;��������@��(g��)������Щ�C(j��)��(hu��)���ǿ������������\(y��n)���]���@�ӵ����\(y��n)������Ҫ���Լ���·��
�������D���ҿ��^�����ص�һƪ���£�����Մ���˻���������Ŀ����ԡ����ՌW(xu��)���R����ą^(q��)�֣����꣬�����،�(sh��)�H�����R(sh��)������һ��(g��)���������磬�]�ж��Ŀ����ԣ��������_ʼ�D(zhu��n)�����ؽ���Ӣ��(gu��)˼����Դ�h(yu��n)���L(zh��ng)�ġ��ЙC(j��)�Ļ����Ŀ����ԡ����@һ�c(di��n)��������D�����u(p��ng)�������[���ڰ������O(sh��)����Ļ����(hu��)�еĕ���̎�����ˣ��������O(sh��)������@��һ��(g��)���(hu��)����һ�����(hu��)��Ӣ���ṩ���r(ji��)ֵ��ԭ�t�@Щ�|������ͨ�^������A��(j��)���ܣ��@Щ���r(ji��)ֵ��ԭ�t���o��e���f������ȥ����(d��ng)Ȼ���f��;���ǣ��@Щ����ʿ�ゃ����Ҫ���ף�ֻ�����B(y��ng)�ゃ����(x��)�T�����ˡ������D�@Ȼ�J(r��n)�飬��(d��ng)���һ�N�����D(zhu��n)�Ƶ���һ�A�ӣ����Ǖ�(hu��)�l(f��)��׃�����������ǰ��������O(sh��)����ǷN�ص�ͬһ��
�������裺�����D߀���R��˼���x�ߣ�߀��(qi��ng)�{(di��o)��������Ⱥ�����w�ԣ���(qi��ng)�{(di��o)�������܄�(d��ng)�ԡ�
�������D����(d��ng)Ȼ�����D߀�ǽ��������ώ�����•����˹�Ć��l(f��)����������˹���O(sh��)Ӌ(j��)������������һ�N���Ļ����܉���ݵ����w���ʽ���������@�N���ʽ�ą����ߣ����������A�ӣ���ȻҲ�����������ğo�a(ch��n)�A��(j��)��ֻ���@�ӣ��@�Nȫ������Ļ����Ÿ����S�����кܶ��ӴΣ����֘�(g��u)��һ�N���w�����^�����D�J(r��n)�飬����˹���O(sh��)Ӌ(j��)�c�����ص�һ�ӣ�Ҳ�в����A(y��)�y(c��)�IJ��֡��������f�����A(y��)�y(c��)���ǣ����B(y��ng)����(x��)�T�������ȥ��֪����������˹���O(sh��)Ӌ(j��)Ҫ��ȫ���c�����Y(ji��)���o���A(y��)�y(c��)��
������˪����������һ��(g��)���⣬�_������ġ���Ψ�����x���ѽ�(j��ng)��(n��i)����һ��(g��)ǰ�ᣬ�����@��(g��)�����^��(g��)�w���ǰ��������ˣ��������f��Ψ�����x���������x����ӑՓ�Č�(du��)���䌍(sh��)��һ��(g��)���x�е��ˣ�ֻ���������@��(g��)���������^��(g��)�w�ģ��Y��
����ʒ�_�ޣ����X�ð�Ԋ�衢������Ą�(chu��ng)���܉����һ��(g��)��ͨ�ĵ�λ���nj�(du��)Ԋ�衢ˇ�g(sh��)���������ء�
�����������@�䌍(sh��)������(j��ng)�¡������b��Ū�������顣
����ʒ�_�ޣ���������ӛ�T������һ�ӣ������f����ĸ����f�����@��(g��)�£��@����ı��¡��㌑��Ҳ�Ǵ��֣�������Ŀ��������ǓQһ��(g��)�h(hu��n)����������nj�(du��)������Ů�����f�@����ͦ��ŵġ���ŵ���˼���������������
�����������������Լ�Ҫ������(d��ng)������(j��ng)�¡��e���J(r��n)�錑Ԋ������(j��ng)����(du��)Ԋ��đB(t��i)����ȫ��������������ȫ�]���P(gu��n)ϵ��
����ʒ�_�ޣ����J(r��n)ͬԊ�˾���һ��(g��)��ţ���Ҫ?ji��ng)?chu��ng)��һ�B�����Z�����^����͕�(hu��)ȥ���@��(g��)����ͮ��ܶ�Ư���ĈD������һЩ��(g��)����Ū�����ϡ�
�������裺�F(xi��n)�ڸ���(g��)�I(l��ng)���ж��Ќ�(du��)���^ƫ��(zh��)����
������������(d��ng)���^׃��Ψһ��ԭ�t�����Լ�Ҫ������(d��ng)����(j��ng)�£��������������(j��ng)���P(gu��n)�ѡ�����㌑Ԋ�c�������˵������������(hu��)���P(gu��n)����ô���(hu��)�挦(du��)���w�����������(hu��)��Ҫ�P(gu��n)�ĵĆ��}������Ҫ̎�����P(gu��n)ϵ���@��ζ����Ԋ�������Л]�л����(qu��n)��
�������裺Ҫ���½���һ��(g��)�c���(hu��)���c�ճ����P(gu��n)���Z����
����ʒ�_�ޣ����ǣ���Ԋ���˲���һ��(g��)�ؙ�(qu��n)�A�ӣ����ǵ�����Ů�ڸ�����������e��һ�ӣ���һȺŤ��(d��ng)�������y�������ߐu�еĿɑz�x��ƽ���^�š�
�������裺�҂��ĸ��ɳ�����˽Y(ji��)�����x�x��ң�
�鿴6092��
|